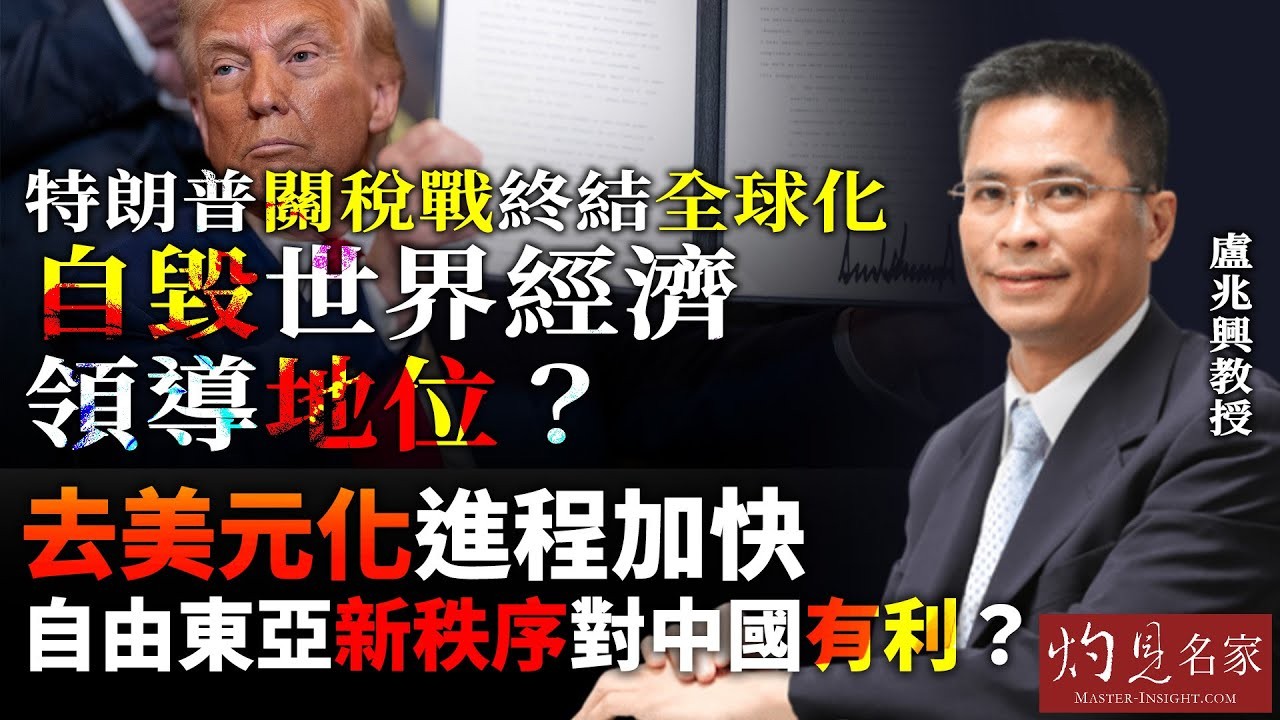國際局勢風起雲湧,香港又遇發展方向與步伐快慢的爭議。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親自南下,落實習近平主席的澳門講話精神,旨在敦促香港要快馬加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其中一個演繹跟過去比較,顯示有新精神:誰的辦法管用,就用誰的辦法。這個比喻形同鄧公的「黑貓白貓」理論,無人會爭議。但將「辦法」上升到「制度」,性質就改變了。雖然制度創新應該無邊界,但也應考慮到變化的時間及可能引起的士氣問題。

據媒體引述,去年12月中大(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肖耿在前海論壇發表講話,相信主題是深化深港金融合作,但後面又講到關於超越金融合作的建議。他認為香港應該有一個「超級特區」,其理據是當年深圳特區的試驗是從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而當今香港同樣可承擔一個國家大局的試驗,把中國外循環與內循環銜接;而且正值香港規劃發展北都,有條件在北都其中一個片區做試驗。具體建議是:在「北都大河套片區」,將深圳河的海關與邊檢分界線向香港境內南移幾公里,形成一個「香港境內關外──深圳境外關內」的兩地深度合作超級特區,使之既可以用深圳的水電氣、人財物、產業/市場/基礎設施等硬實力,還能同時叠加香港法律、監管、城市管理等軟實力,降低片區建設合作成本,為推進深港科創樞紐奠定基礎。
「超級特區」關鍵在「關外」
這個簡稱「海關南撤」的超級特區建議,立意非常好:使用深圳水電氣可大幅降低成本,對吸引內地企業在港境內設置機構,十分有利。這個建議最關鍵部分在於「關外」,即「海關與邊檢管轄範圍以外」。
內地有「飛地」的做法。深圳在汕尾市有一塊468 平方公里的「深汕特別合作區」,由深圳主導管理,有責任將深圳工業溢出部分疏導到合作區,部分稅收歸深圳,產值屬廣東省。但這個飛地同屬廣東省管轄範圍,並不涉及海關與邊檢。

香港也曾與飛地擦肩而過。2014年時任特首梁振英獲中央首肯,在南沙撥出一塊地給香港。但在特首率領相關局長到南沙考察可如何利用這塊地的前幾天,有關消息被泄漏到媒體,而且解讀為一國兩制邊界被模糊。整個計劃胎死腹中。
當年若香港在內地獲得一塊飛地,從發展空間來說有所擴大;從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方面是早着先機;從制度創新的角度看,也是試驗特區。不恰當的比喻是香港「北上攻城掠地」,若然實現,也反映當時香港仍處於「氣勢如虹」勢頭。而今肖耿教授提出的香港「海關南撤」建議,先不說制度與邊界等問題,單從氣勢角度看,倘實現,同樣是不恰當的比喻,香港被「掠地」而形同捱打局面。
回到制度創新問題。評論員屠海鳴有一篇文章,引述夏寶龍主任2月7至10日在橫琴、前海、河套等大灣區合作平台調研考察時的一些講話與精神。文章提到,夏寶龍此次調研河套「一區兩園」,從現場可看出深港「兩園」的巨大反差:在深圳園區,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已有大量企業入駐;在香港園區,目之所及,還是一片荒蕪,最先建成的3 棟大廈最快今年才能推出。這個陳述是客觀現實,也是香港特區政府「錯要認,打要企定」的根據與大背景。

另一個論述,與討論「海關南撤」的建議相關:「大灣區涉及的制度創新,是為了更好地推進經濟發展,並不會觸及一國兩制的根本,不必擔心憂慮。再次,制度創新應遵循「優者選用」原則。誰的辦法管用,就用誰的辦法;如果粵港澳三地現行辦法都不好用,那就大家合作尋找一種新辦法解決問題。總之,格局要大、思路要活,不能拘泥於細枝末節。」(但是否直接引述夏主任的話並不清晰)
這個優者選用原則,與鄧小平當年提出的「黑貓白貓」論異曲同工。但應用在香港的具體制度,比如「海關南撤」,是否會觸及一國兩制,則值得討論。
為制度創新而模糊區別 或得不償失
海關的功能與職責並不僅限於稅收。若只是稅收,香港讓出一塊地招商引資,並放棄一些稅收,確實不會觸及一國兩制根本。但海關還有規範知識產權、產品安全標準、商品說明當中對虛假與誤導陳述的界線等。雖然都不是大原則問題,唯都需用法例作為根據。由深圳來管理這塊飛地,都採用香港法律嗎?最大問題是關稅區──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對外聯繫,可以跟別的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議;這些協議都要加括弧聲明香港境內某些地區不適用嗎?現在美國將香港納入制裁中國的範圍,所謂的理由就是香港與內地界線不清晰。當然這些都是托詞,但香港的辯詞則說香港是單獨關稅區,以後辯詞也要加括號嗎?
其實,「海關南撤」也並非完全不可能。但要等國際局勢有利時刻,以及香港與內地的規範標準和做法相近的時候。為了制度創新而刻意去模糊區別,可能是得不償失的做法。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