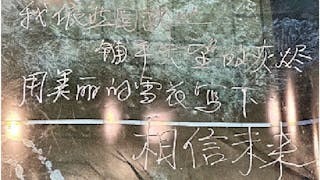認識岑偉宗(岑爺),自然是從音樂作品開始。他自90年代開始填寫歌詞,1994年的《城寨風情》至近年的《四川好人》、《頂頭鎚》、《一屋寶貝》、《情話紫釵》、《奮青樂與路》……作品無數。
跟岑爺面對面聊天,是在2019年底,在扶輪社主辦的第一屆香港青少年微小說創作比賽「回憶。禮」中,我和他都是評判,大家一起開會時,共同討論評審標準。
當時,已有計劃訪問他,可是風雲變幻,疫情蔓延,一直未能結緣……直到最近,由於音樂劇《大狀王》上演,他剛好跟太太淑嫻回到香港,我們相約在西九的戲曲中心,暢談了4個多小時。
岑偉宗很健談,我們從小時候開始聊起,說到舞台劇、音樂劇……還有填詞心得、語感層次,以及未來計劃。

初中一,緣結舞台劇之始
岑偉宗祖籍廣東順德,出生於廣州,他是獨生子,5歲時移居香港,「當時,我跟母親坐火車來香港,從尖沙咀火車站走出來,印象很深刻,鐘樓好漂亮……」父親幾年後才來港團聚。
為了謀生,父母忙於工作,無暇照料他,小學四年級至六年級,將他送往調景嶺的鳴遠學校念書寄宿,「那幾年的寄宿生活,是人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日子,主要是因為有『同伴』……」他學會與人融洽相處,結交朋友。
「那時,晚上60個學生一起睡大通鋪,有上下兩層,熄燈後門就鎖起來……住在學校,兩星期回家一次,不回家的週末,跟老師去爬山,又跟同學會去游泳,鍛鍊體魄,我覺得好快樂。」宿舍有聖誕聯歡會,也有歌唱比賽,他好享受在台上表演這種感覺。
那些年,像其他的男孩子一樣,他最愛看漫畫,例如黃玉郎的《龍虎門》。「我喜歡在練習簿上,畫漫畫寫故事,在班上傳閱……還改寫歌詞。」他第一次改寫的,就是區瑞強的《陌上歸人》。
升上中學後,他不再看漫畫,「我戒看《龍虎門》,有一段時間,最喜歡閱讀《好時代》雜誌。」他愛聽日本歌,自小就迷上澤田研二,「他的performance非常好看,眼睛好迷人……退而求其次,才是西城秀樹。」
從中一開始,岑偉宗就加入學校的劇社。「在劇社,我找到了個人的identity,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感覺。」1981年,他第一次踏台板,就在藝術中心的壽臣劇院,他還記得,「學校劇社參加聯校戲劇比賽,劇本是師兄寫的,我演一個偵探。」當時劇社的導師是張任兒弟老師,正是當今音樂劇演員張國穎的母親,「張太很好,無為而治,放手讓我們去搞活動」。

他是劇社的活躍份子,至中二,已代表學校參加聯校戲劇活動的籌委會,認識了不少來自其他學校的朋友。「我的成長,建立於聯校的友誼中,我很適應這種社交模式。我們的友情,一直維繫至今時今日。想不到聯校活動,給予我一個很好的『歸宿』。」中四那年,他還寫了一個劇本《虛榮醉》,「係咪好老土?!」他笑着說。
中五會考後,1985年,他投考香港演藝學院(HKAPA)的戲劇學院,豈料對手太強,「我如何與黃秋生、姚潤敏等猛人競爭?不獲取錄是意料中事,唯有『死死地氣』走去讀中六。」由於原校沒開文科班,他以1B4C的成績轉往九龍工業學校念預科,亦加入了劇社,導師是鄧偉明老師,「當年參加聯校戲劇比賽,劇本是師弟寫的,我還拿了最佳導演獎。」他繼續說下去。
「念中六時,要讀Principe of Accounting、地理、經濟……我完全跟不上。」一年後,他再報考HKAPA,結果又名落孫山。「那兩年,我幾乎想死,戲劇是我的『歸宿』!」
預科時,岑偉宗已開始在香港話劇團做兼職,「我擔任舞台助理,在後台工作,搬布景板……也認識了不少話劇團的演員,這也是identity!
AL成績,考得最好的是中文科,他進了浸會念中國語言文學系,順理成章地加入浸會劇社。他開始嘗試寫劇評,曾投稿《年青人周報》,誰知一投就獲取用。為了免費門劵,他單刀直入,致電《信報》文化版編輯,問對方可否在報章上寫劇評,而且用報館的名義索取傳媒票看演出,編輯說取了票就要交稿。如此這般,他在大二時,以張近平為筆名,開始在《信報》撰寫劇評。
「每周看戲、寫劇評,迫使我認真去看戲劇,然後透過思考、構思,將觀後感寫出來,這是很好的訓練。」他的文章散見於《信報》、《越界》及《經濟日報》等報刊,亦曾是《文匯報》戲劇評論專欄的作者之一。

音樂劇,邁向心靈的歸宿
1991年畢業後,岑偉宗當上了中文老師,「初時,我不懂教書,完全是摸着石頭過河……」到第二年,他跑到HKU讀教育文憑,遇上了謝錫金博士,「他為我開拓了全新的教育視野,從他的身上,我學到了什麼是教育!」他認識了認知心理學,還應用在教學中,「在課堂上,我學會了寓學習於遊戲,不再硬生生的要學生聽我講書,我跟他們溝通,激發他們的想像、聯想……學生開心到不得了!」
1995年,他毅然辭去教職,跟隨謝博士念哲學碩士,靠自己的積蓄和在大學做研究助理維持生計。其論文題目為《香港專業舞台劇作家寫作思維過程模式研究:構思及衍生意念》。
「我覺得謝博士的理論,好適用於劇場,教育不是自說自話,戲劇也如是,需要溝通,觀眾的反應好重要。」岑偉宗強調教育經驗奠定了他日後「心靈的歸宿」。
另一方面,他仍然對戲劇念念不忘,修讀了浸大校外進修部的「戲劇文學」證書課程。「盧偉力剛從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回來,搞了這個一年制課程,導師眾多,有張秉權、陳捷文、洛楓、陳守仁……讓我可以系統地學習。我沒有受過HKAPA的洗禮,可以藉此建構自己對戲劇的認識。當時,我還寫了一篇論文〈論老舍《龍鬚溝》的戲劇結構〉,曾投稿內地的戲劇期刊,並獲得刊登。」其勇於嘗試,於此可見一斑。
他也曾「膽粗粗」地毛遂自薦,致電著名編劇杜國威,主動要求杜Sir給他機會,協助音樂劇《城寨風情》的填詞,那是1994年。《城寨風情》的成績很亮麗,在舞台填詞界,岑偉宗找到了方向。
2001年,他為《聊齋新誌》填詞,出色的表現,吸引了毛俊輝找他為《還魂香》(2002年)填詞,令他的填詞事業,又更上一層樓,連大師級的填詞人黃霑也稱讚他:「中文根柢好,詞寫得好,寫詞而又有這樣中文根柢的,現在很少了。」

在HKU念完碩士後,岑偉宗轉職成人敎育機構,並於專上教育機構兼職導師,如HKAPA戲劇學院、香港公開大學的語文及教育學院。在明愛專業及成人教育中心任教時,學生楊偉倫(阿卵)等替他改了個綽號──岑爺,因為當時亞視的高層有位沈野先生之故。本來這只是個暱稱,後來口耳相傳,新相識的朋友,人人都這樣稱呼他。
多年來,他一直參與業餘戲劇社(如丁劇坊、湛青劇社等)的演出活動,從導演到燈光,台前幕後,什麼都做。到2002年,他不再參加業餘劇社,專心填詞的工作。
2003年,岑偉宗跟做時裝生意的女朋友結婚,至2006年,在太太的支持和鼓勵下,他全職填詞,自此,走上了專業填詞人的不歸路。
「歌詞在戲劇中,並無獨立的生命,它只依附着戲劇生存。」當岑偉宗開始愛上填詞時,曾有研究戲劇的學者如此說。在當時的劇壇,填詞一直不獲重視。香港戲劇協會主辦的香港舞台劇獎,到了第21屆才設立最佳原創曲詞獎,由「一屋寶貝」奪得;再去到第29屆才設立最佳填詞獎。
「流行曲歌詞是什麼?它反映了作者在一時一地的看法。」岑偉宗每一首作品,都反映了他對人生的思考,以及對這個世界的看法。換了是音樂劇歌詞,重點則是展現戲劇、故事和人物,作者本身的想法就退居次席。他認為,「縱使觀眾沒有看過戲劇作品,也明白歌詞想表達的內涵,有所共鳴,這才是成功的作品。」這也是他對作品追求的高度。

林夕曾說過:「用廣東話填詞,不是人玩的遊戲。」
岑偉宗指出,「用英文填詞,即使旋律改動一點,仍是那個字,但用廣東話填詞,旋律改少少,因為Pitch(音高)的關係,就會變成另外一個字,例如『笑』,變成了『蕭』。」相對來說,廣東話比較「縛手縛腳」,自由度比較少。
「粵語本身很有音樂感,其實很適合用來寫音樂劇,正因為語音要求精準,構成廣東話句子的音樂質感好強烈,即使無音樂伴唱,如果台詞寫得好,純說台詞,也有音樂感……困難與否,視乎你追求art piece還是easy job。如果歌詞寫得好,必定需要相當的語文工夫。」他認真地說。
寫劇本,改編《穿KENZO的女人》
談到音樂劇創作,岑偉宗指出,「音樂劇有三種元素:音樂、故事和歌詞,我的強項只是第三部分。音樂劇有另一難度,便是要藏有大量information,因為音樂劇用歌曲來說故事,歌詞自然要介紹人物、地名、背景、時空、行動等;歌詞絕不單純是『寄意』,其實它是複雜的對白。」
他強調,「曲詞本質是輔助一首歌,而歌曲無可避免地是一件『半商品』,因為它需要聽眾,故此,不要太曲高和寡,好的曲詞必須雅俗共賞。」
2021年11月,音樂劇《穿KENZO的女人》於葵青劇院上演。此劇改編自鄧小宇的同名原著,他負責撰寫劇本與歌詞,與作曲家高世章聯手創作這個音樂劇。

岑偉宗與高世章(Leon)第一次合作,是2003年首演的《四川好人》,而2009年的《一屋寶貝》,兩人再度與「演戲家族」合作。2010年,他開始萌生編寫劇本的念頭。
「當時剛剛看完《穿KENZO的女人》,我好喜歡。徵得鄧小宇同意後,便動手改編,雖然好難,也硬着頭皮開始……」作品完成後,由「演戲家族」於2013年,公開圍讀。8年後,此劇終於由中英劇團完整地搬上舞台。
《穿KENZO的女人》本是連載小說,想當年,它在《號外》連載時,筆者已是讀者,被書中形象鮮明的人物、抵死的對白、妙趣橫生的場景所吸引。
小說中大部分的角色都寫得生動傳神,「這些角色又確實是有趣兼且有點惹人羨慕的一群……」鄧小宇也曾說過,他也不盡認同自己塑造的角色,包括他們的心態、生活方式,希望引起讀者反思。讀者大抵也能感受到文字中的反諷,對其筆下的人物既愛且恨。
香港在上世紀70、80年代,經濟起飛,新中產階級崛起,這部小說成功地描畫出人們如何建構自我,譜寫了香港人身份認同重要的一章。
「我在劇中加入很多我自己的童年記憶、生活經驗,我覺得戲劇的功能,就是將現實已經看不到的東西,重新呈現出來。」他希望以歌舞說故事,共創作了20首歌曲,藉此將香港70、80年代的時代氣息、往日的情懷帶給觀眾。
筆者觀劇的當日,亦感受到台前幕後整體的全程投入,各演員傾力演出,又唱又跳,為整個演出帶來無比的能量和動力,實在是難能可貴。

《大狀王》,就是這樣煉成的
近日在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公演的粵語音樂劇《大狀王》,故事的主角是「廣東四大狀師」之一的方唐鏡,寫的是公堂審案。
「《大狀王》,絕對是個嶄新的嘗試。題目是我們自己定的,跟以往接受委託製作的音樂劇完全不同,它是個清裝的公堂戲,好難寫。」岑偉宗認為,此劇對高世章和他來說,是極大的考驗。
「我和高世章合作多年,讓我更深入音樂劇世界,對自己的要求也提高了,我希望歌詞可以融入多種音樂的質感,面對古典西洋曲,歌詞要有古典西洋味;面對元代故事,文字就要有元曲的味道。」

何以衍生創作公堂戲這個意念?岑偉宗說:「第一,公堂戲在香港影視文化,是個重要的類型;第二,近年華語音樂劇經常提及IP(Intellectual Property),公堂戲就是一個IP,方唐鏡與陳夢吉、劉華東、何淡如並稱,是香港人比較熟悉的狀師,就是方唐鏡,我們可以發展這個IP,讓這齣戲有長遠的演出潛力……」談起背後的理念,他滔滔不絕地說起來。
早在十多年前,高世章已想寫一個清朝的音樂劇,「2015年初,我和Leon到上海看《上海灘》,有一天,在Starbucks喝咖啡聊天,忽然我說不如改編《審死官》吧……」
然後,在2015年的10月31日,一班朋友,到新加坡看宮澤理惠主演《海邊的卡夫卡》,也是在喝咖啡之時,跟茹國烈談到這個公堂戲……回港後,他們相約Leon一起再談,結果,西九文化區接納了這個作品的概念。

「Leon希望這個製作要分階段進行,先試做一個workshop……」如何去發展一齣音樂劇?西九也期望做一個model出來。
「workshop之後,辦preview……希望有時間refine這個作品,不用趕deadline,有足夠的時間將作品布局、剪裁、沉澱……對我們來說,好珍貴!」
身為填詞人,岑偉宗有意識地去尋找各類型知音,從選材開始去構思,什麼可以雅俗共賞,選取一個廣東人熟悉的題材,是他們考慮的重點。
「張飛帆先寫劇本,由Leon決定何時唱歌,他作曲,然後我填詞,大家互動。」三人三年同步創作。曲詞劇本於2017年準備就緒,團隊先後邀請香港話劇團為合作伙伴、方俊杰擔任導演,以及遴選演員,經過兩年的準備和排練,《大狀王》於2019年的5月預演,是香港前所未有的實驗性演出。預演後,他們以不同形式收集意見,期望在正式公演前,再加琢磨,讓作品更臻完善。
從醞釀意念起歷時多年,這齣音樂劇終於在2022年9月正式公演,《大狀王》就是這樣煉成的!

「音樂劇以審案為題材,作詞的難度頗高,公堂戲的歌詞,既要交代案情的細節、控辯的理據,還要道出時、地、人,說明殺了誰。但願歌詞出來的效果,有『清代味』和『審案味』吧!」岑偉宗如是說。
以歌唱的形式交代連場公堂戲的複雜案情,推進劇情發展之餘,又要蘊含哲理,實在不容易。面對這個作品,難怪岑偉宗感到非常自豪。
談填詞,說語感6個層次
岑偉宗創作多年,在其著作《音樂劇場‧事筆宜詞》(2012)中,他曾提出粵語音樂劇歌詞具有5個語感層次──「雅、妙、趣、俗、鄙」。談及填詞境界,在這次訪問中,他還加上了「文」,變成「文、雅、妙、趣、俗、鄙」六個語感層次。
「記得在2008年,有一次,我和Leon去澳門演講,在船上聊到粵語雅俗問題……」談到最後,結論就是廣東話可分成「雅、妙、趣、俗、鄙」5個語感層次。
而「文」的靈感,則來自加拿大UBC的音樂系教授羅倩欣,「她很喜歡我寫的歌詞,是她inspire了我,在5個語感層次的基礎上,多加了『文』。」岑偉宗透露,在近十年的創作中,他常常思考語言學的問題,結果發現了歌詞是否動聽、悅耳,與「語感」有莫大的關係。
關於填詞,如何達到文情俱備,雅俗得當?岑偉宗表示,「音樂劇的歌詞要配合角色,角色人物的成長背景,社會地位,都會反映在語言上。恰當就是美,不自然就不美。如何在遣詞造句上做到自然效果,能讓角色更鮮明立體?這涉及人物身份、動機、處境……」他的說法,令我聯想起老舍的文章〈連人帶話一齊來〉。

頓了一頓,他開始解說:「『文』,即是文飾。如林夕的『俗塵渺渺 天意茫茫 將你共我分開 斷腸字點點 風雨聲連連 似是故人來』;而『雅』者,正也,亦即恰當的、斯文的語言,人畜無害。例如人們說『去鞠躬』,即表示參加喪禮。」
他接着說:「『妙』,即係有『嘢』想講,背後有訊息,如許冠傑/黎彼得寫的『點解要擺酒 亂咁嘥錢冇理由 人人為飲一杯酒 累到夫妻一世憂』;而『趣』則如『童年就八歲多歡趣 見等狗仔起勢追 爺話我最興嗲幾句 買包花生遳遳脆 跳下飛機 街邊玩下水 爺爺重教我講呢一句 有酒應該今朝醉』。」
說完妙和趣,他笑着說:「『俗』,即通俗,而『鄙』,即粗俗。」他舉自己的作品為例,如「呀咿呀 我莫如做隻狗 正乞兒 我累人生花柳」就是俗;而鄙則如「仆街 仆街 遇到你我就仆街」。
接着,他補充:「例如在《大狀王》中的〈福臨門〉,有幾句歌詞『激死老竇 愧疚淚流 壯志未酬 率先折壽 冇嘢當就去偷 卒之揸住個兜 沒法呀辭其咎 萬惡呀淫為首』就遊走於妙、趣、雅、俗之間。」
講到填詞的竅門,他繼續說下去,「《大狀王》中的〈道德經〉,我要滲入老子的道家哲學,從有到無,所謂『無為而無不為』……我所寫的第一個版本,好深,於是改為較淺的版本。」他採用「嵌字法」,將「道德經」三個字嵌入歌詞中,如「無道德 經書撕爛 唯《道德經》可師範」。
在創作上,「布局的構思比較花時間,寫詞其實很快,例如在〈福臨門〉中,歌女唱「山伯臨終」。當我知道要寫「仙伯臨終」,沿着旋律,首先找出可以嵌進粵曲《山伯臨終》的經典唱詞的樂句;接着以哭起句,然後寫到尾才嵌進『山伯』和『英台』的名字,以便不懂粵曲的觀眾知道發生什麼事。全段歌詞『我借哭問天意 淚似簾外雨 盡惹愁呀絲 今世若緣盡到此 燕分飛斷腸事 碎心伴秋意 盼兄哥你知 山伯與英台同心事 化蝶同林相與』就是如此衍生出來的。」岑偉宗細細道來,詳加解說。

此外,他亦提到「替代」,即是以類近的詞,取代原本的字詞,二者意思相通。在《大狀王》預演後,他將歌詞中,所有「的」字刪去,如「留在你的墓誌銘」改為「前事記於墓誌銘」;「想歸家的引路有燈影」改為「知否歸家引路有燈影」等。
「又如有一場寫『打更佬』有夜盲症,因為無一個音可以寫到『夜盲』,於是我就寫『天咁黑佢點會望到人』……這就是整個意念的『替代』。」岑偉宗鍥而不捨,在創作的過程中,精益求精,不斷改進的精神,實在教人佩服。長年致力粵語音樂劇,岑偉宗對粵語入詞自有心得,我想,「字字珠璣」,恐怕是所有填詞人的挑戰。
盼未來,推動華語音樂劇
岑偉宗已是舞台填詞界的中堅分子,他有個心願,「我想更進一步磨利自己的刀,與大家同心協力,推動華語音樂劇,繼續創作具價值的作品,把音樂劇再推上層樓。」
他與伍卓賢合作的音樂劇《阿飛正轉》,2018年在台灣首演。「我一開始想寫機場候機室的來來去去,後來變成講述兩個年輕人在異地工作的故事,以鳥喻人,劇中的每隻喜鵲名字都有個『飛』字,像『王飛』、『孟飛』等,那些飛來飛去無處落地的角色,賣命的『菜鳥』,以至背後遙控的大人,都是華人社會常見的世代處境。」期待觀眾在笑聲淚影中喚起心中熱血和浪漫,甚至帶點傻勁的阿飛精神。
由香港小交響樂團聯同「一舖清唱」及人力飛行劇團,集合了港台兩地的創作人演員,合力打造的交響音樂劇《阿飛正轉》,於去年12月初,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上演。岑偉宗坦言,「《阿飛正轉》最終可以在台灣和香港兩地輪番上演,身為原著編劇及作填詞人,我深感欣慰。」
第50屆香港藝術節的重點節目《日新》,是他與金培達合作的音樂劇,此劇還原了孫中山在青年時期的心路歷程,重塑他的激情歲月,演期原定於今年3月,因疫情延期,可能在明年初才上演。
此外,他已完成了一個新作品,主題講生死,由鍾氏兄弟作曲,尚未正式命名。
移居台灣近兩年,岑偉宗看了不少台灣的音樂劇,他說:「無論是題材、風格,甚至marketing,都有新意,尤其是市場學,他們的營運模式,令我感到好impressive!」


談到未來計劃,他透露:「除了香港的工作,也希望能把一些之前在香港創作的作品,換個方式呈現,有些項目已經與台灣的編劇合作開發;有些項目則是把粵語音樂劇變成普通話版本,目前已經完成中文文本,待疫情過後,再找適當的機會搬上舞台,展現在觀眾眼前。」
他繼而指出,歌詞是要從聽覺中創造畫面,「粵語有九聲,易有變化,但也難寫,因為聲調差一點,意思就差很多;普通話因為只有四聲加一個輕聲,同音字很多,也容易混淆,我希望這兩套系統可以在我手中融合,為華語音樂劇創造更多可能。」
岑偉宗期待在填詞方面,創作不輟,而且有所突破。「我和高世章,不時都在尋找新的題材,我也在構思與伍卓賢合寫一個音樂劇……」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信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