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香港科技創新聯盟由一群來自香港產、學、研的科創業界代表發起,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副院長盧煜明教授出任創會主席,多家大學14位專家擔任顧問,多個國家級科研平台及科創公營機構負責人等15位人士擔任理事,陣容鼎盛。香港科技創新聯盟的成立宗旨是促進聯盟會員之間的跨學科交流與創新合作,發掘合作研發項目;探討與香港科技創新發展相關的政策、協同香港政府部門、產業界、學界、研究機構等,推動大灣區科技創新合作與發展,以及增加大眾對科技的認識及興趣。本社編輯部月前曾在科學園訪問盧煜明教授,請他分享早年在英國留學的經驗、1997年從英國學成歸來從事研究、創科25年的心路歷程,以及對香港科研發展的看法。本文先回顧他赴英國的求學研究之路。

文:文灼非;盧:盧煜明
文:你出生於醫學世家,是否從小立志從醫?
盧:我自小對生物學十分感興趣,爸爸(盧懷海醫生)固然對我有一定的影響。小時候,他常常參加學術會議,有時候會在家中我和弟弟面前預演,我也會幫爸爸忙製作簡報。因為我很喜歡攝影,所以也會幫爸爸拍攝。他曾經告訴我:”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所以他也鼓勵我學習繪畫和攝影。我擁有的第一部相機也是爸爸1958年剛從醫科畢業時買的錦囊牌(Canon舊稱)的Rangefinder相機,性能頗好的。那時候,沖曬照片需要在黑房進行,其實與做實驗是差不多的,需要預先計劃、小心控制溫度等。科學與攝影一樣,都是一種藝術。所謂藝術,就是將一種虛無的概念轉化成實在的東西。
最近有一幅我和一位畫家一起創作的作品被學術雜誌刊登在封面,充分證明了爸爸的話是對的。看完這幅畫對文章的領會,比花幾個小時讀整篇文章更深和更立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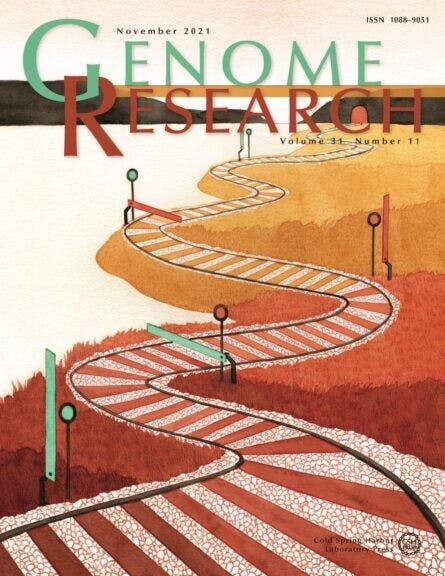
記得中學時有一本書Biology: A Functional Approach,裏面有許多傑出科學家的照片,包括發現DNA結構的科學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劍橋大學拍攝的照片,令我感受到劍橋大學在締造科學歷史上的關鍵角色。但當時仍未決志念醫科。當時香港的大學入讀率低,所以英美的大學都有報讀,甚至選過史丹福大學的工程學,為自己提供更多的選擇,直到中七,因為劍橋的歷史決意到劍橋大學念醫。
文:DSE成績高的學生大都選擇進入兩大醫學院,令醫學院的門檻很高,當年有沒有這個現象?當時你的學校多數選擇什麼學科?有沒有影響你?
盧:那個時代double E(電機工程)都是很具挑戰性的,很多人追求的,醫科一直都是大學最top的學科之一。當時學校有3班,一班是文科,兩班是理科,包括數學和生物學,因為我感覺到自己在數學上不是有太高的天分,所以選擇生物學,不少同學的志願都是當醫生,那一年聖若瑟書院的成績不錯,有3位同學成功進入劍橋大學,兩位進入醫科,一位念工程。

文:你在劍橋大學有什麼得着?
盧:劍橋是一所很特別的大學,從中體會甚多。我入讀的是劍橋大學以馬內利學院(Emmanuel College),哈佛大學的捐贈者約翰·哈佛(John Harvard)也是以馬內利學院的學生。當時,一位老師帶着兩、三名學生上supervision(香港的tutorial),老師曾經問過一條問題,我依書直說固然沒錯,但老師則質疑為什麼要這樣回答,背後的意思是追問憑什麼認為書本提出的數據是對的?令我難以忘懷,時刻都會探求實驗數據的來源。所以,現在我也會教導學生凡事都要探源。

劍橋也出產許多諾貝爾獎得主,甚至在吃飯、研討會中都不乏他們的身影,這種耳濡目染的氛圍是很重要的。以爬山為例,你會先看到山峰,雖然未必能夠爬上去,但起碼看到目標。
文:後來為什麼考慮前往牛津大學?
盧:很有趣,牛津與劍橋大學的歷史相約,但劍橋大學醫學院一直以來只提供3年教育,後來是在1976年才多加3年的。我是1983年才就讀劍橋,所以那時仍是一所很新的臨床醫學院,而牛津的臨床教學歷史比較久,當時成績較為優異的學生都選擇在牛津或倫敦繼續餘下3年的學習,變成一種傳統。

文:研究的題目靈感是怎樣來的?
盧:在劍橋的最後一年,我開始接觸DNA研究。那一年有一個final year project,抽籤時,我是最後一名,抽到一個很難開展的研究項目,將血吸蟲的其中一個基因複製(克隆,clone)出來,如果無法克隆出來便沒有數據,那一年便會十分辛苦,但令我學習到不少有關DNA的技術。因此,我在牛津大學十分渴望繼續DNA研究。在課餘時間便去繼續這些研究。
文:在陌生的地方,面對全球各地人才的競爭,那個壓力大嗎?
盧:我覺得劍橋和牛津大學的氛圍是十分不同的,前者的壓力大很多,每個學期都有數次口試,後者的考試比較少,合格率高,因此我們有能力在課餘時間做研究。當年牛津大學後3年有100個名額,40個劍橋,60個牛津,老師上課問問題時,有些只是讓牛津大學的學生回答,因為劍橋大學的學生可能已經讀過,反映這兩所大學在頭3年課程深淺的不同。

文:為什麼在醫學、哲學上均修讀了一個博士?
盧:許多醫生都是考取醫學博士(MD),或者DM(牛津叫法,同時兼顧研究與工作)。但我在英國讀書時,有些老師則認為這樣會「學師不足」,需要用3-4年全職考取一個PhD,或者DPhil(牛津叫法)。我是醫科生時曾經做過一個研究,尋找母親血液中嬰兒的細胞,在畢業那一年在著名的醫學期刊《刺針》(The Lancet)發表了一篇文章,做houseman時對這個研究念念不忘,是否需要完成它?那時候掙扎了好一段時間,和爸爸談論,他擔心這樣有可能會浪費了之前的學習成果,加上學費很貴,那時候需要依靠4個獎學金才能夠繳交學費,需要的決心很大。尤其我的博士導師只保證我頭3個月的薪水,之後的要自己籌措,的確有破釜沉舟的感覺。慶幸贏得牛津一間書院的初級研究院士席(Junior Research Fellowship)承包了我的電腦與租金,我只須安排生活費。
文:這是一條比較崎嶇的道路,研究的成果不可預見,當時有沒有想過一定會成功?
盧:沒有的,我沒有期待什麼結果,只是享受那個過程。即使現時無創性產前檢測有許多人使用,但當時若能達到80%準確,在科學上已經十分厲害了,更加沒想到我可以做到97%準確。當時沒有保證一定會成功的,而且那研究相當困難,甚至第二年兼職做糖尿病相關的研究。

文:為什麼會回流香港?
盧:我在DPhil口試的同一個星期申請了在牛津大學擔任講師一職,後來受聘。從1994年開始,便在牛津大學有一份tenure-track教席。但我和太太都是香港人,一直念念不忘香港的環境。1997年正值移民潮,不少學者離開,港大和中大都有聘請我那個領域的學者。
太太是修讀物理的,在修讀博士時認識,1994年7月在同一個ceremony畢業的。我倆都決定回來。我太太和我都曾經接受過裘槎基金會的資助,現時我是裘槎基金會的董事,有時真的是命運驅使。
太太十分喜歡教書,因此回來後在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任教,數年前退休。
專訪盧煜明教授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