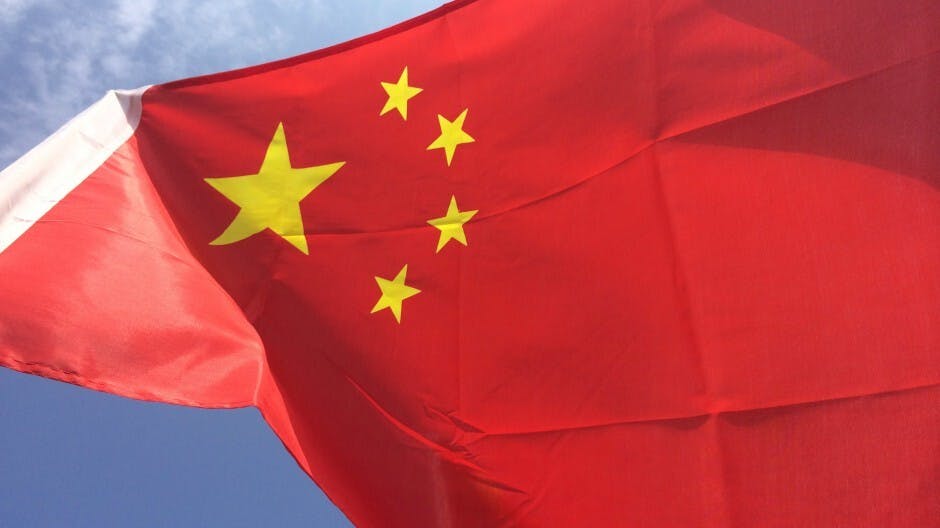近來,在西方世界,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或者制度化失敗(failur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正在成為在學術界和政策圈流行的新概念,藉此形容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內政治生活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儘管這個概念有不同解釋,但大多都指向黨內集權和權力結構重組、頂層設計、反腐敗、中國模式的明確化等變化;同時他們擔憂這些變化對中國政治的長遠影響。
為什麼西方學者會認為這些變化是去制度化或者制度化的失敗呢?這就要看另外一個相關的概念,即「制度化」,也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黨內生活的制度化,因為所謂的失敗是和十八大之前,中共黨內政治生活制度化狀況相比較而言的。
在西方,中國精英政治的制度化,一般是指鄧小平生前確立起來的一系列重要政治機制,包括任期限制、年齡限制、精英選拔制度和集體領導等制度。
第一是領導職位任期限任制。限任制至為關鍵。一般來說,包括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和其他重要職位(所有政治局常委)在內的領導人,最多可以在任兩屆,也就是10年。這與很多西方國家的總統制並無太大區別。對於防止在毛澤東時代普遍存在的個人專制,限任制是有效的制度工具。當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統治一個國家數十年,政治體制就不可避免會傾向營私舞弊、濫用職權,為社會所不容。很多國家發生顏色革命,其中一個主要因素就是領導人長期的專制統治。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年輕人很不願意看到一個特定領導人在政治舞台上表現數十年。
確保快速自我更新
第二,年齡限制同樣非常重要。它為高齡政治領導人和官僚提供了退休制度。在其他政治體制,退休制度適用於公務員。但在中國,退休制度適用於所有黨政官員,包括政治領導人、公務員、人大代表、社會組織負責人以及所有其他重要的政府和準政府組織。不同的級別有不同的年齡限制,西方最為關心的乃是政治局常委。在這一級別,到十八大為止實行的是「七上八下」的制度,即68歲及以上的官員必須退休,67歲及以下的官員則可以留任。
限任制和年齡限制使中國的政治精英能夠以極快的速度自我更新,因而可以有效地反映代際變化和利益變化。與許多其他政治體制相比,中國的政治體制有利於迅速地、大規模地更換政府官員。中國每年有數以萬計的官員離職,又有同等數量的官員接替。這種迅速的流動儘管有其弊端,但卻無可辯駁地體現着時代的變化。
第三項制度是無情的精英選拔體制(meritocracy)。在很多政治體制尤其是民主政治,要想獲得政治權力,就必須獲得足夠的選票。中國也在開始實行黨內票決制,在考察一位潛在的領導人在其同事以及民眾之間受歡迎程度時,票決制也很重要。然而,在票決之前,還存在一個額外的選拔程序。這個被考察對象必須滿足諸如教育、工作經驗(在不同地區以及不同級別上任職),和很多其他考核指標的所有要求。在中國政壇,不可能產生在其他政治體制內所發生的「黑馬」現象,即使有所謂的「黑馬」,他已經處於體制內,並且已經滿足了級別的要求。中國有幾千年的賢能政治歷史。今天,中共在人才錄用方面愈來愈傾向於從其中吸取有用的東西。
第四項制度是中國所說的「集體領導」或「黨內民主」,主要指的是政治局常委成員的集體政治領導。這個體制以內部多元主義為特徵,在中共的最高領導層,成員之間有着相當的制約與平衡。政治局常委會作為最高權力決策機構,往往被外界視為權威主義的象徵。然而,相當長的時間裏,各個成員之間擁有幾乎是同等的權力,各自負責一個領域的決策,並在該領域有着最大的發言權和決策權。一些中國學者將這個體制稱為「集體總統制」,因為主要國家決策是由集體做出的。
西方所擔心的是什麼呢?第一,這些制度是否還會繼續生存和發展下去?第二,權力交接會否順利進行?這始終是中共領導層所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都沒有處理好這個問題,導致了嚴重的權力鬥爭和政治不穩定。在後鄧小平時代,因為有了上述幾個方面的制度建設,權力交接問題處理得比較好,從江澤民到胡錦濤,從胡錦濤到習近平,中共已經實現了兩次和平的權力交接。十八大之後所引入的諸多變化,是否可以使得權力交接繼續和平穩定呢?現在離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只有約兩年的時間,西方對中共高層政治的穩定性愈來愈關注。第三,是否還存在着江澤民時代和胡錦濤時代開始的黨內民主?如果現在有變化了,新的制度又是怎樣的?是否有可能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的個人集權呢?
這些流行於西方的擔憂還可以理解,但去制度化和制度化失敗卻是毫無經驗根據的。十八大以來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導致人們對中國政治未來不確定,但從經驗層面看,這些巨大的變化中間更隱含着再制度化和更制度化的努力,而不是去制度化,更不是制度化的失敗。制度化是一個複雜的進程,其中一些制度因為根據原先的方式很難再繼續制度化,需要調整,使之走上更為有效的方向;而另一些制度則需要更加制度化。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理解今天中國政治生活的制度化。
第一,限任制會更加制度化。鄧小平之後,中國實行的是「三合一」制度,即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由同一個人擔任。這一制度的理性在於,像中國那樣的大國,必須具有促成足夠權力集中的制度。沒有「三合一」制度,如何能夠進行像十八大以來那樣的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從其他國家(包括越南)的經驗看,沒有這樣的權力集中,更有可能走向寡頭政治。現行憲法規定,國家主席是兩個任期,即十年。儘管沒有明文規定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的所有重要職務,過去的實踐都是兩屆。如果要改變限任制度,不僅要修改憲法,也會導致其他各個方面的重大變化。因為限任制所帶來的政治更新和穩定效應,這一制度不會更改,而是會更加制度化。
第二,年齡限制即人們關注的「七上八下」制度的變化仍然有待觀察。現在的年齡限制並不是完全固定的。這個實踐從江澤民時代開始,當時只是為了高層領導的年輕化考量和政治上的方便。這個制度如果堅持下去,就自然被視為是制度化;但如果出現一些變化,也很難說是制度化的失敗。人們既不能消除更年輕化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取消這個「年齡歧視」的可能。實際上,在存在限任制(即在一個職位上不能超過兩屆)的情況下,這個「年齡歧視」有可能在將來被改變。
集體責任導致無人負責
第三,集體領導黨內民主方面,十八大以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這些變化是為了通過調整而取得更大的制度化。十八大之前,政治局常委過於分散。由於政治局常委的每個成員,只負責各自的領域並在該領域享有最大發言權,政治局常委內部的分工體制,是趨向分散化發展的,有效的協調並不存在。因此,人們所說的集體總統制經常導致沒有總統,集體決策導致無人決策,集體負責導致無人負責的局面。這種體制類似於頂層「分封制」。
正是這種制度特徵,才造成今天人們所看到的「周永康現象」,即政治學上所說的寡頭政治現象。令計劃現象與軍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現象也屬於這個類型。黨內「團團伙夥」的形成使得頂層權力不再正常運作。這正是胡錦濤那一屆領導層所發生的情況。他們在開始時也有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但最終因為無窮的阻力而沒能成功實施。更嚴重的是,黨內「團團伙夥」的形成直接威脅到了執政黨的生存和發展。這種威脅遠遠超出了經濟腐敗行徑所能帶來的威脅。
十八大之後才改變了這個局面,主要是新成立了幾個領導機構,即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和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權力集中化。不過,這種集中化是對之前權力過於分散的回應。除了軍事改革領導小組,習近平是這些小組的組長,李克強是副組長,其他的幾個常委被安排在不同的小組,這就克服了從前的頂層「分封制」,避免各自為政,協調功能大大強化。這些小組的運作方式也和以往的不同,那就是正式化。從前也有不同的領導小組,但不公開,社會並不知道它們在做什麼;與此不同,現在的這些小組公開,活動公開透明。正式化應當被理解成「更加制度化」(greater institutionalization)而非去制度化。
第四,執政黨的黨建能力大大提升。這不僅表現在反腐敗運動上,更反應在各項制度建設上。十八大之前儘管「黨內民主」有了發展,但「黨內民主」不應當成為黨內腐敗合理化的藉口。如果黨內的「團團伙夥」互相制約,以黨內民主的名義來運作政治,執政黨的生存就是一個大問題了。互相制衡的結果必然是最後連反腐敗都沒有能力了。十八大之前就出現這種情況,當時盛行所謂的「刑不上大夫」的意識,即常委犯錯不會得到懲罰。十八大以來徹底改變了這種情況。更重要的是,一套新的以廣義法治為核心的黨內紀律道德制度,和以中紀委為主導的反腐敗體制正在形成。
第五,執政黨更具行動能力。十八大以來經過頂層設計,由三中和四中全會推出了一共500多項改革方案,五中全會推出今後五年的行動綱領,最近又開始了聲勢浩大的軍事改革。因此有人說,在今天的世界很難再找得到一個像中共那樣具有行動能力的政黨了。
所有這些都指向了中國的再制度化和更加制度化。當然,這些變化並不是說中共黨內政治生活制度化已經完成。中共是中國唯一的執政主體,也是改革和發展的主體,黨內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決定了黨的生存和發展。在黨內民主、權力交接、政治退出、政治錄用制度等很多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制度化空間。所有這些方面的建設並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不斷試錯的過程。但只要方向明確,執政黨領導層具有堅強的政治意志力和具體的行動綱領,就會實現最終的制度化。
原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亞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