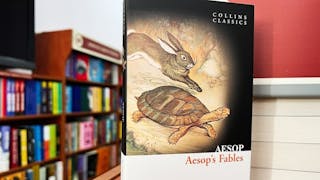(承上篇:為什麼荀子值得研究?——荀子的富國論(一))
〈儒效篇〉中,荀子對人性有很清晰的說明:
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
(北京中華書局王先謙《荀子集解》頁143-144,後均引據此書)
先天之「性」不分善惡
荀子把人性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先天的「性」,與生俱來,人人無別。〈性惡篇〉說:「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頁435)又說:「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與小人,其性一也。」(頁441)界定得非常清楚,是指人性中本能部分,賢聖如堯、舜,淫奸若桀、跖,秉賦相同,故在其原生狀態中,並無道德上的善、惡之辨。〈榮辱篇〉對「性」作進一步解說:
凡人有所同一: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黑白美惡,耳辨聲音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按:「養」同「癢」),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頁63)
「性」作為各種本能,是賢聖與淫奸同具的。那是人作為一種生物的感受與反應,包括各種生存欲望與生理官能,本無道德上的是與非的問題。但「性」雖天賦,卻可以「化」:因後天環境或人為因素的積習而產生變化、或加以轉化:
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埶注錯習俗之所積耳。(同上篇)
性化而為情
「性」雖同一,因後天習染不同,其「性」產生的變化有別,形成不同的人格取向。這種有後天因素所成的人格取向,便是人性的第二部分——「情」。但「情」是由「性」發展而來,是經人為過程變化或轉化了的「性」。「情」按前引所述,是後天人為的,不是與生俱來的。因為是人為的,難免與其他人或社會發生關係,故由「性」到「情」的發展,從道德判斷上便可以有好有壞:
師法者,人之大寶也……而師法者,所得乎情……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也。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
(〈儒效篇〉頁143-144)
當「性」為「注錯習俗」所「化」時,由於經歷取向的積累不同而形成為不同的「情」,在道德判斷上便可有好壞之分,在人格形成上有「君子」、「小人」之別。好壞不同的「情」取決於對「性」的放縱或節制: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祟。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由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性惡篇〉頁434-435)
就是說:「性」中的欲望部分,具有惡的潛能或基因,若加以放縱,便可變為一種引起紛亂爭奪之「情」,其結果在道德判斷上自可稱為「惡」。但這種「惡」是可以轉化的,以禮義之道化之,使歸於「治」——合乎社會的治理原則,也就是某歷史階段中,某種社會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規範(在荀子就是儒家所提倡的「禮義」),合乎這種規範,便是「善」。化性、情之「惡」為「善」,正如縱性、情中之欲為惡,都是後天人為的「積習」,荀子稱為「偽」。
孟、荀相較 荀近實際
歷代論者,都會把荀子的「性惡論」拿來和孟子的「性善說」比較。從近代觀點看來,荀子對人性的觀察和探討,無疑是更符合現實和較全面的。孟子完全從道德的角度來界定人性,把後天在人類社會中形成的意識形態,硬變為先驗性的東西,認為人之有「四端」——仁、義、禮、智四種道德動機,如其有「四體」(四肢),否則便不成其為「人」。 (參看楊伯峻《孟子譯著》頁78-80〈公孫丑章句上〉)這是把儒家提倡的四種道德規範,硬說成是與生俱來的。難怪荀子批評他說:「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性惡篇〉)
孟子的缺失是完全不理會人性中的本能部分(忘記了或否定了人的生物性或動物性的特點),看不到這個部分和人性中後天形成部分的關係。荀子則非常重視這個部分。他認為這個部分雖只是個體生存的欲望,本無賢愚善惡之別,卻可以「化」,可被後天習染轉化為「惡」或「善」。這種被轉化後的「性」,荀子稱之為「情」。如果無節制地放縱「性」的欲望部分,轉化後所形成的「情」,才會是「惡」的。所以荀子說的「性惡」,並不像孟子說的「性善」那樣,是先天的或先驗的,所謂善、惡也並非不可逆轉的道德判斷。荀子的觀察無疑更有「辨合符驗」,更靠近人性的實際,更具有近代意義。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