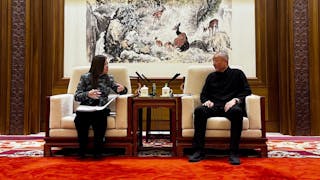香港作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一直與全球先進國家和大都會並肩同行,金融中心地位多年來與紐約和倫敦並稱「紐倫港」,擁有卓越的國際航運航空中心地位(3年疫情除外)等,政府和社會都一直引以為傲。但在另一方面,當有報道提到香港堅尼系數、快樂指數、新聞自由排名等方面,表現不理想時,政府就會退避三舍,視而不見。
談到香港的經濟成就,不少人都會侃侃而談,現時香港從政者更肩負了「說好香港故事」的任務。但如果撫心自問,香港基層市民在多恣多彩的上層經濟建築下,究竟過着怎樣的生活?香港作為一個富裕的開放文明社會,這問題我們是不能迴避的。
最低工資連通脹都追不上
就此,筆者今日與大家分析一個與民生相關的重大議題,這就是最低工資。筆者在90年代中以民協成員身份參政,當時已積極倡導最低工資立法,多年來仍有關注其執行情況。

上圖顯示最低工資自2011年以來的執行情況,由開始的28港元調整至現在的37.5港元,只上升了約34%;同期通脹率總增幅約是46%(這是具有複式累積效應),如果以全港的名義工資指數增加率計算,其總增幅約是58%(同具複式累積效應)。現時最低工資的水平較2011年28元的調整增幅,以通脹率計算,竟是少了12%(即平均每年少了約1%);如以名義工資指數增加率計算,是少了24%(即平均每年少了約2%)。
政府在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建議下,最近已批准把最低工資調整至40元,並將於2023年5月1日執行。以這水平計算,最低工資自2011年將增加了43%,這仍比同期的通脹率總增幅約少了3%;在到下次調整前,這差距極可能再擴大到約8%。依賴最低工資生活的基層市民,其實自2011年實施以來,其調整水平的總增幅就連通脹也追不上,與一般僱員工資增幅的差距也愈拉愈大,更遑論他們的生活是否因最低工資而得到實質的改善!
在另一方面,經濟學術界幾十年來都有個迷思,推論最低工資會引至失業率上升(尤其是年輕人和低技術僱員),以及打擊中小企經營,因此不少經濟學者是反對最低工資立法的。但近年很多實證硏究中,有關最低工資的反效果證實並未存在。在202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獎的3位經濟學者(David Card, Joshua Angrist和Guido Imbens)中,David Card就因有關硏究成果而獲獎。
在香港方面,據悉在政府的追蹤硏究中,亦未發現最低工資導致失業率上升和中小企倒閉的情況。
最低工資是否有客觀標準?
香港最低工資是偏髙還是偏低?這是否有客觀依據的標準?我們從下圖清楚知悉:香港最低工資是在所有先進經濟體系中是最低的,這不是略低,是大大偏低。

以香港現時最低工資37.5元計算,假定每天工作8小時,每月工作22天,則每月總收入為6600元,這只等於香港每月平均個人國民生產值約20%;這是否足夠一個勤奮勞工有尊嚴的生活(只是劏房的租金就超過2000元)。若以同一公式計算澳洲接受最低工資僱員的收入,其每月總收入為3480澳元(約19000港元),這等於澳洲每月平均個人國民生產值約50%,大大高於香港。
至於比香港平均個人國民生產值低的英國和法國,其最低工資則是超過香港的兩倍,我們可以怎樣理解?我們必須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在各個經濟發展水平大致相約的先進資本主義地區中,香港最低工資的水平是大大偏低的?基層市民在最低工資的大環境下,面臨生活的苦況,最近已有兩位嶺南大學學者(梁仕池及黃雅文)就其調查硏究及文章中有詳細論述,政府和最低工資委員會必須参考。
再者,加拿大去年吸納了40多萬新移民,澳洲也吸納了20多萬,如果加拿大和澳洲極高的最低工資真是會帶來高失業率,其政府也不可能長期執行這樣寬鬆的移民政策。
最低工資應檢討什麼?
可喜的是,行政長官李家超於2022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由最低工資委員會研究如何優化最低工資的檢討機制,包括檢討周期、如何提升效率、以及在最低工資水平和維持經濟發展等元素取得平衡。
在今次檢討中,筆者認為問題其實只有一個:最低工資的訂立如何能夠實質地改善基層僱員的生活。在最低工資每年定期調整時,要達至實質改善僱員生活這目標,可行的方法可包括:
- 每年的調整是上一年的通脹率,再加上1至2%;或
- 每年的調整是上一年一般僱員名義工資的增長率,再加上1至2%。
調整機制可直接引入公式,情況就如現在地鐵調整票價的「可加可減」機制一樣,以代替委員會內一些可能以立場先行的爭論。委員會在新機制下主要的工作則是確認該機制的落實,以及考慮一些次要的輔加因素,對最終的調整幅度作一些合理的微調;這公式則可每10年檢討一次。
筆者期望社會能多關注和監督這次委員會進行的檢討,不能掉以輕心。最低工資在這十多年的演變,極可能已偏離立法原意和社會期望,政府必須正視及作出正確的指示。習主席強調的「共同富裕」發展目標,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要如何落實?筆者認為最低工資可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最低工資的客觀標準其實很簡單,就是要讓受惠者過有尊嚴的生活,現在我們做得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