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掬水》是古箏編曲,加上三個字,就成了《掬水月在手》,那是葉嘉瑩先生的紀錄片。看了Trailer,80、90歲的葉先生,談過去,70、80年前的往事歷歷在目。
《掬水》
紀錄片有了,出版社把錄音梳理成書,遂有同名著作《掬水月在手》。說的是葉先生一生與詩詞的緣份、感情。一眾文化人、作家都在說他/她們眼中的前輩、他/她們的啟蒙老師。
看《掬水月在手》,也在看《知人論詩──葉嘉瑩帶你讀唐詩》。想起幾年前送給朋友孩子的生日禮物,葉嘉瑩的《給孩子的古詩詞》。朋友與孩子一起閱讀,開始愛上唐詩宋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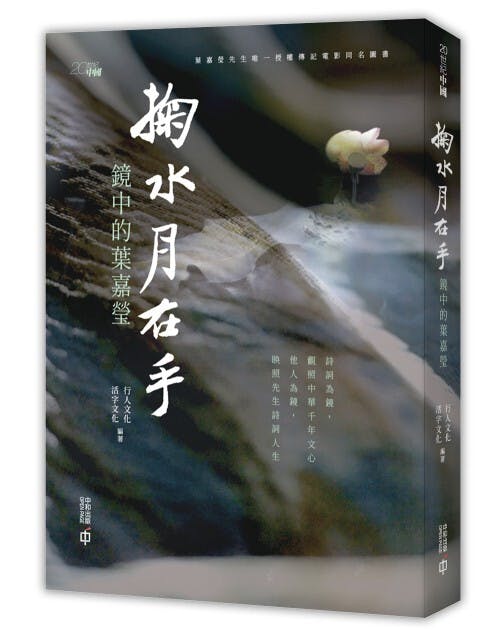
回憶從前,葉先生年幼時寫下第一首七言詩《秋蝶》,最後兩句「三秋一覺莊生夢,滿地新霜月乍寒」,前一句「幾度驚飛欲起難」,那「飛不起來的蝴蝶,是不是夢醒了的莊周呢」?葉先生說不知道,小時候他「對草木昆蟲充滿了關懷」。
15歲那年,寫了《詠蓮》,葉先生「從小就目睹了太多的痛和災難」,遂有「如來原是幻,何以度蒼生」。
多年後,葉先生在台大授課,很受歡迎。其中一位旁聽生(他唸外文系),說「葉先生是引導我進入中國古典詩詞殿堂的人」。葉先生「不光講詩本身,還把背後的社會變遷、詩人襟懷一一道來」。
葉先生講杜甫的《秋興八首》,精采極了。杜詩至此「句法突破傳統,意象超越現實」。道出杜甫「有能力繼承、破壞,進而變化出之」,詩聖當之無愧。
當年聽葉先生課的大學生,叫白先勇。把刊登在《現代文學》的《玉卿嫂》讓先生看了,先生沒有排斥「現代主義」,對小說點頭稱讚。
一起吃糭子
瘂弦也來寫葉嘉瑩,說「葉嘉瑩是研究傳統詩詞的,與我們寫新詩的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1951年,27歲的葉嘉瑩填了一首寄調《蝶戀花》,開首幾句:「倚竹誰憐衫袖薄。鬥草尋春,芳事都閒卻。莫問新來哀與樂……」
1964年,32歲的瘂弦寫下《如歌的行板》,詩的第一段:「溫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
新詩好,還是舊體詩詞好?在上世紀60年代,據瘂弦的觀察,寫新詩的與寫舊詩的不會來往。到了端午節(台灣的詩人節),「兩派詩人是不在一起吃糭子的」,皆因他們對屈原的解讀不同。
瘂弦那時編《幼獅文藝》,葉嘉瑩在那裏發表的第一篇文章,談王國維《人間詞話》的三種境界。作品中作鮮明真切的表現,讓讀者有真切感受,才是「有境界」作品。另一篇談李義山的詩,他的詩像謎語,倒讓葉嘉瑩解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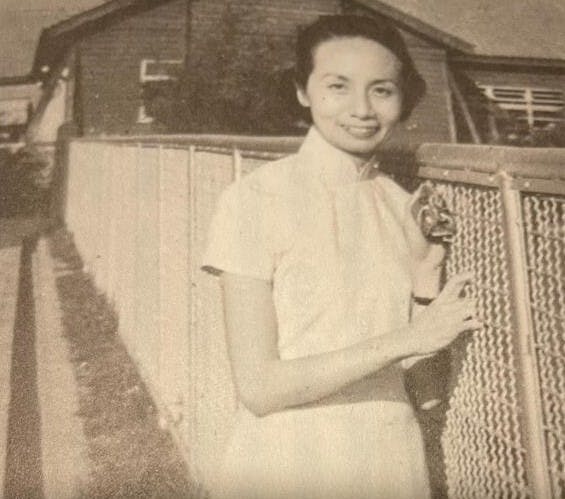
瘂弦說葉嘉瑩是「穿裙子的士」(她的先生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因「思想問題」被關了起來):「以儒家的標準來說,是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她都做到了。」
1952年,葉嘉瑩的先生出獄,不過再沒有工作。葉嘉瑩得打幾份工,去大學兼課、到電台講《大學國文》。最後,到外國講學,「都是被生活迫出來的。」
因為葉嘉瑩,瘂弦說「新詩人跟舊詩人開始在一個桌子上吃糭子了」。
葉嘉瑩解讀杜甫的一句「香稻啄餘鸚鵡粒」,不會如胡適所講,該寫成「鸚鵡啄餘香稻粒」。新詩的顛倒句法,杜甫也懂。
寫新詩一族,接受葉嘉瑩,葉先生可是同路人來的呢。
豪麗見真淳
《知人論詩》來到最後一章,葉嘉瑩談的不再是杜甫、李白,也不是柳宗元、韓退之、李商隱、白居易,而是杜牧。
先生起了一個看似自相矛盾的題目:《豪麗之中見真淳的杜牧詩》。杜牧「在豪放之中帶着一種華麗的風格,是豪放而且華麗的」。
這位風流浪漫詩人,在離開揚州時,寫下「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對杜牧來說,離開揚州,他就要「落拓江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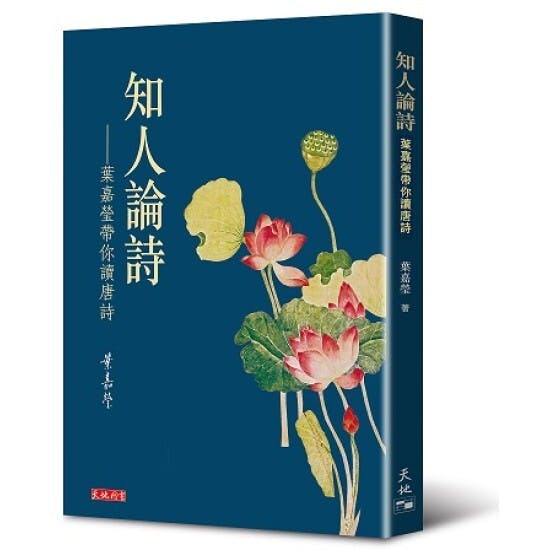
來到長安,杜牧當上監察御史,掌管法紀。應邀出席李司徒宴會,席上指明要見歌妓紫雲。甚至對主人家說「宜相惠」(把紫雲送給他),讓其他陪酒女子都笑了起來。
杜牧隨即揮筆,寫了《兵部尚書席上作》:「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偶發狂言驚滿坐,三重粉面一時回。」詩成。沒一點造作。
杜牧「風流瀟灑」,這一類詩,「並沒有很高深的思想可言。」
但先生說杜牧「品格不卑下」,他的七言絕句「寫得最好,因為是近體詩,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有氣勢,即興,不造作。
先生的導讀,讓我們看到像口語的「華堂今日綺筵開」,「非常自然」,「非常好」。
來到南宋,姜夔《琵琶仙》詞中「十里揚州,三生杜牧」,是向唐詩人杜牧致意。
杜牧也是明白歷史盛衰道理的,他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很流行,傳誦眾口,因為它辭藻華麗,聲調響亮。」杜牧生在清平時代,遂有沒作為可言之苦。他的「清時有味是無能,閒愛孤雲靜愛僧」,有感而發,可不是無病呻吟來的。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綜合轉載,題為編輯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