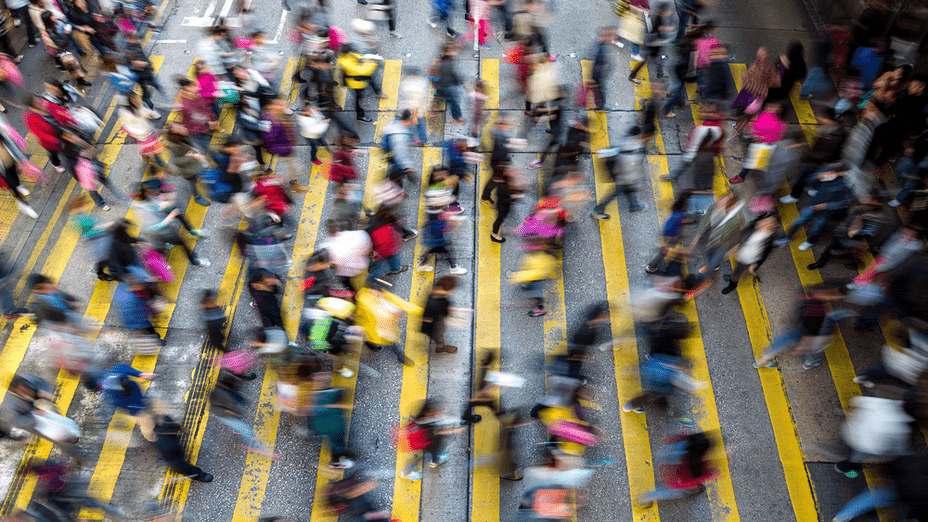「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
(劉邵,《人物志》)
「我寫的乃是人類的普遍現象……我用的倒是審美的視角。因此,描述的主要不是人性之惡,而是人性之醜。我以自己審醜的結果,奉獻給乾淨的孩子們和尚未被社會污染的純潔心靈,願他們與種種病態人格保持精神距離,讓自己的人生具有別一種境界。」
(劉再復,《人論二十五種》)
「錢鍾書80歲生日當天,家中電話響翻了天。機關團體,親朋好友,紛紛要給他賀壽。錢鍾書所在的社科院也準備為他開一個學術研討會慶祝。對此,錢鍾書一律謝絕。他說:『不必花這些不明不白的錢,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說些不痛不癢的話。』」
(李異鳴,《非常人》)
「大輪明王原是我佛門弟子,精研佛法,記誦析理,當世無雙,但如不存慈悲布施、普渡眾生之念,雖然典籍淹通,妙辯無礙,終不能消解修習這些上乘武功時所種的戾氣。」
(金庸,《天龍八部》)
「養生,是中國人獨有的觀念。養,是人為地調理育化、讓它歸於正途之意。不過,養這種治理調育,又不是剛性的、強力而為;乃是如風雨潤物般,令其得以生長。至於生,是有內涵的。儒家強調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生生不息,故人亦應如天地運化般,充滿了四時之生意。養生之養,即重在涵養這種生意、生機;養生之生,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生命年壽,而是指這種內在蘊含着無窮生命力的生命。」
(龔鵬程,《仁者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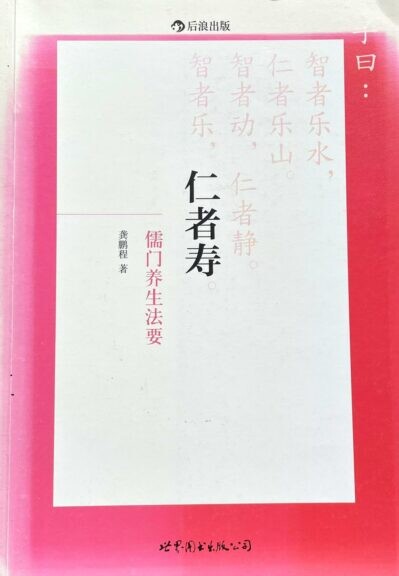
生命之道
春分了,紅棉開了。
春天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不但近了而已是春滿人間。
疫襲兩年多,苦了人間,但四時依舊不改次序,應約來去,這便是生命。70、80年代提倡「抗衡文化」的俗世清流雜誌《突破》出的一幅畫報,一朵潤濕欲滴的紅棉,襯着一段我至今不忘的文字 ──
「我不知道這是一個美好的時代,還是磨人的年頭;
我只知道,到時候,紅花總會開的。」
人類追求功器之利,放縱私慾,不知節制,引致天氣暖化,生態逆變,因求一時之利、滿足一時之慾,造成陸續而來的惡果。這疫襲或亦是天地對人類的警告,肉眼看不見微塵般的病毒卻能癱瘓了全球經濟。21世紀本是人類力量無比強大的時代,卻不堪微塵的一擊,且不分貧富高低,一視同仁地感染,可說是另類的平等。
然而,上天有好生之德,這病毒為了生存,卻選擇了自我演變,望與人類共存而變弱了,變得更近似人類的細胞,或可戲稱之為「由高壓變懷柔」。
這便是「道」──生命之道。
人心難測
這兩年,除了體悟生命之道,我們亦見到不少世情世態,而形成這世情世態的,便是各式各樣的人,各式各樣的言行。這疫情中的眾生相,令人百感交集,或悲傷,或感激,或讚賞,或唏噓,或憤怒,或鄙視,或怒極反笑(苦笑、苦中幽默,蘇聯高壓時期的波蘭人便是以冷峻的幽默作為最後的抗爭手段)。
難道果真是「天道可通,人心難測」!其實,生態危難之形成及應付的背後,仍是那千奇百怪的人心;生態研究固之然迫切,但「人心」的研究更重要。奈何,縱觀全世界的大學可有開辦「人學」的學系學院呢?
幸而,雖成不了堂皇的學院派,卻也有不少資料和見解分散於中外古今的著作之中。隨手拈來的例子如三國劉邵的《人物志》、清代曾國藩的《冰鑑》、歐洲榮格(Jung)有關希臘神話的研究(以希臘諸神作為人類的各式原型)。至於掌相之學、西方星座、中國生肖等玄學又怎不是「人學」的綜合探討。
在此我向讀者推薦兩本當代的著作──劉再復的《人論二十五種》和李異鳴的《非常人──1840-2000中國人的另類臉譜》,前者讀之紓解鬱悶,後者則收振奮精神之效。不過,李氏選的,多是清末民初的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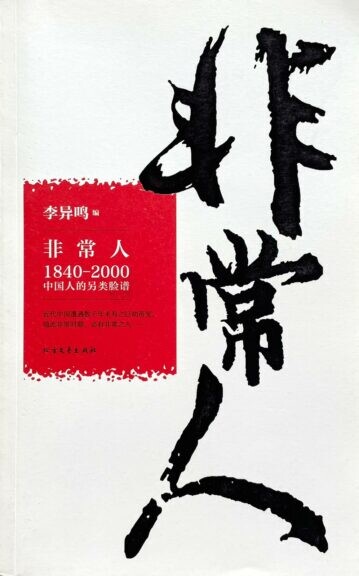
劉氏論人 反言求正
劉再復是當代讀書人,亦即有別於「專業學者」(亦即以做學問謀權位或巴結吹棒、搖旗吶喊的所謂學者),中華文化傳統的讀書人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有心人。劉氏是當代人,他寫的「人論」亦是他當代眼見耳聞的。
他筆下的25種人分別為:「傀儡人、套中人、犬儒人、點頭人、媚俗人、肉人、猛人、末人、輕人、酸人、閹人、忍人、倀人、妄人、陰人、巧人、屠人、畜人、饞人、儉人、分裂人、隙縫人」。以上都是負面點相、冷筆諷刺的。
他筆下正面的,只有「痴人、怪人、逸人」3種,但似乎皆心有持守,亂世求存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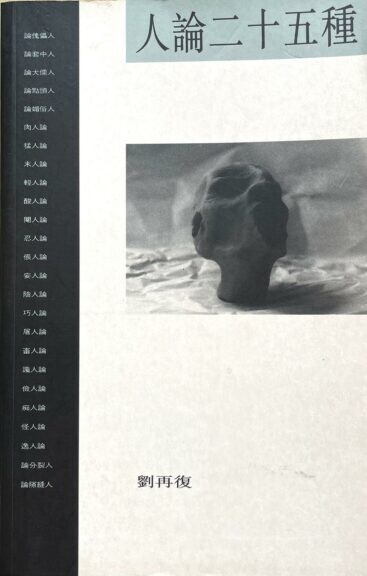
負面的22種不大需要說明了,單瀏覽名目,已可心有所感於內,或未能言之於外。劉氏在自序說明──
雖然《人論二十五種》寫的主要是人的荒謬和人的病態,對人開始絕望,但我仍然在反抗荒謬,反抗絕望,我確信人生的意義正存在於反抗荒謬與反抗絕望之中。我寫『末人』,自然是希望教育機構不要再制造末人;我寫『肉人』,是希望社會不要再淘空人的精神,或要求心靈的國有化;我寫『傀儡人』,更是為社會呼喚新鮮的,活潑的,屬於自己的靈魂。
可見劉氏實在傷心人別有懷抱,他的冷筆諷刺是為了刮骨去毒,他的筆是外科手術刀,他的文字是反言求正的。不過,他寫的幾個「正面人」,卻更令人掩卷長嘆,欲哭無淚。劉氏就此說明──
我還特別寫了怪人論、痴人論、逸人論和論隙縫人等,為這些人辯護,為人的個性辯論,為人的執着辯論,為人的自由權利辯護,並呼籲給人的自由意志以存身之所。倘若不允許「怪人」存在,一有個性就加以撲滅,有點持異的思想,就勞師動眾地加以批判,一點隙縫也不給,連隱逸之所、避難之所也都搗毀,政治烏雲籠罩一切,那還能有人才的孕育之地嗎?
俠者以命 奪回本性
劉再復的慨嘆請命或不易在現實中求,但卻可在金庸的小說中得到安身立命。其實,「俠以武犯禁」──能以人格和才能的力量突破專橫的禁制,為生命奪回本性生活的空間,才是「俠」的真義。
金庸筆下的「逸人、怪人、痴人」不少,我最心儀的,乃是洪七公、黃藥師;介乎隱與顯、逸與義之間,則是張三丰、莫大先生、定閒師太;至於風清揚的氣度則不及黃藥師。當然,我偏賞的,仍是黃蓉、任盈盈,但黃蓉的老子是黃藥師(最有型的逸人),她是順道成長的,而任盈盈的老子是任我行,她可需要絕大的魄力和智慧才能明心見性,活出真我。
說到任我行,則頗符合劉再復「猛人」的定義,但猛人可不易長壽,且看任猛人的下場──
陽光照射在任我行臉上、身上,這日月神教教主威風凜凜,宛若天神。任我行哈哈大笑,說道:『但願千秋萬載,永如今……』說到那『今』字,突然聲音啞了。他一運氣,要將下面那個『日』字說了出來,只覺胸口抽搐,那『日』字無論如何說不出口。他右手按胸,要將一股湧上喉頭的熱血壓將下去,只覺頭腦暈眩,陽光耀眼……忽然從朝陽峰上摔了下來……過得片刻,便即斷了氣。
估計這個猛人猝死之時,大概60多吧,卻因私慾過猛而死。觀乎其他「逸人」,似皆長壽,並且老當益壯,如張三豐、黃藥師。不過最長壽者,卻是另一隱士──《天龍八部》的無名老僧,可能年過百歲了,卻武功深不可測,但他之所以長壽,乃因佛法悟透──
佛門子弟學武,乃在強身健體,護法伏魔。修習任何武功之時,務須心存慈悲仁善之念。倘若不以佛學為基,則練武之時,必定傷及自身。功夫練得愈深,自身受傷愈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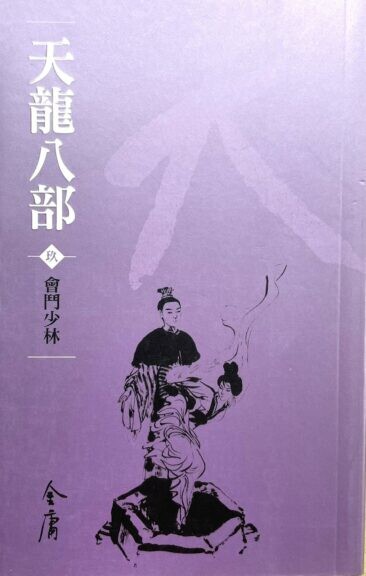
心存仁念 首在虛己
這道理又豈限於武功,學問才能以及事業成就,亦皆如此。具備大才能、大魄力的人士,若心無仁念,最後只會害人害己。手中刀愈大愈利,若不用之於伏魔降妖,為萬世開太平的話,只會為禍越烈。最後,報應己身,縱使不是折壽,也生不如死,內心煎熬,舉目無親(可信任之人),天天活在修羅場,睡不安寢。
仁者壽。只要仁厚為懷,隱逸也好,日理萬機也好,仍能壽──自然的壽,不是藥物支撐的壽。日本的稻盛和夫是一個好例子:60多歲患上胃癌,但勤而忘老,工作不斷至今90過外。他之能「一生懸命」仍能安,便是因為活在佛法之中。真正的學佛,不在講求佛學,而在身心浸淫其中,相忘於佛法。要能如此,首在「虛己」,自以為了不起的「猛人」,或免不了「猛死」。

最後,以劉再復的一句語重心長結尾──
「把人才變成奴才之後,奴才便變成人才了!」
說得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