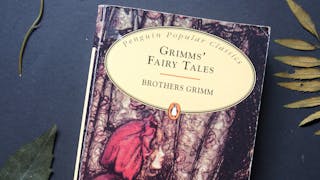電話打通了,我興高采烈一迭聲地說:「宗璞大師姐,是您嗎?您在家嗎?我現在就在北大東門啊,我現在進去找您好不好?」電話那頭親切地說:「張惠呀,好的,但是我現在不在燕園,搬到昌平了。」 我大吃一驚,說:「我看您的文章,還有曼菱師姐的文章,不是都寫您在燕園嗎?所以我就直接奔北大來了。」原來2012年,北大要籌建馮友蘭先生故居,因此宗璞大師姐搬離了久負盛名的燕南園57號三松堂。
隱居世外仙境的高人
我到了宗璞大師姐的新居,入門也是一個大園子。正是四月草長鶯飛,一路桃花迎春海棠!那高柳細葉新裁,果然是「菀菀黃柳絲,濛濛雜花垂」。中間臨水而立的「百歲堂」,頗類具體而微的天壇。而且地面非常潔凈,真有點像《紅樓夢》裏說的「但見朱欄白石,綠樹清溪,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
宗璞大師姐那天頭暈,一發作起來十幾二十天也好不了。但她居然還是見了我,並且要起來到客廳裏和我說話。我急忙說:「大師姐您別起來了,就靠在床上跟我說話就行了。」宗璞大師姐看着我,微微愣了一下,說:「妳多大了啊?」我忍俊不禁,這才猛然醒悟宗璞大師姐是1928年生人,比我大幾十歲,我怎麼敢一口一個大師姐呢?
可是我覺得有些人是有「文化形象」的。「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的杜甫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七十老叟,而「俱懷逸興壯思飛,可上青天攬明月」的李白無論如何還是30歲的壯年模樣——即使實際上李白比杜甫大11歲!在我的心目中,宗璞大師姐永遠都是《紫藤蘿瀑布》裏面的她,受過挫折卻還是對未來飽含希望的年輕女郎!
紅樓結緣成三人 自立為業顯志氣
宗璞大師姐也問起我們紅社的事兒,因為這是她、曼菱師姐和我聯合發起的。她也很關心紅社,只是首先自謙說年紀大了,就希望我們能做起來,她在旁邊敲敲邊鼓。其次希望我們這個紅社,大家都能發言才好,你一言我一語的,各抒己見。
我就跟她說:「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微信群,這個群裏面的每個人都可以說話,還可以發上去自己的書法,或者繪畫、攝影作品等等。」我還給她稍微展示了一下別的微信群的情況,她也笑着首肯。
宗璞大師姐現在聽力不太行,所以雙耳要帶上助聽器才能聽我說話,我也就靠在她耳朵邊,然後稍微提高聲音跟她交流。她當時首先就問我最喜歡哪個紅樓人物。我說其實我做講座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問我這個問題。我跟他們講,我已經不專門喜歡某一個人了,而是像孔子說「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也都有自己的缺點,我想如果單獨愛某一個人過深,固然她的優點可以學習,可是她的缺點也會影響到我,所以我現在希望能夠對她們保持審美的距離。
宗璞大師姐說她最喜歡的紅樓人物是探春。我有些訝然,因為宗璞大師姐不是多次寫過史湘雲嗎?還特別舉例辯稱史湘雲不是有些紅學家所贊同的脂硯齋,而且并沒有和寶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而是嫁了才貌仙郎衛若蘭。不過轉念一想,探春曾經說過:「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宗璞大師姐欣賞她,應該是探春能夠自立一番事業的志氣吧!
點亮黑夜的人生燈塔
我問她,您知道您父親的《中國哲學史》對韓國前總統朴槿惠影響有多深嗎?我靠在她耳邊,說起朴槿惠在母親遇刺之後陪在父親身邊,女代母職履行第一夫人的外交事務。萬萬沒有想到幾年後父親也遇刺,剛剛得知這一噩耗,就在瓢潑大雨中,被士兵監管着勒令立即搬出總統府。

渾身濕透的朴槿惠抱着紙箱等電梯,財政部長看到她,那個在她父親生前一直諂媚地追着她家口口聲聲要兒子和朴槿惠結親的財政部長,這時冷漠地把頭轉到一邊假裝沒有看到她。後來,在身體和精神雙重打擊下的朴槿惠生了病,正當芳年卻莫名其妙地臉上、身上長滿了黑斑。
而她僅有的親人,她的弟弟、妹妹當時也不理解她,甚至也對她大加指責,她曾經變得孤僻、易怒、悲觀,幾乎瀕臨崩潰的邊緣。偶然地,她接觸到了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回顧往事,她說:「我找到了人生的燈塔。」在每一個夜不能寐、孤燈挑盡的時分,在每一個萬箭穿心、嚎啕大哭的時刻,都是《中國哲學史》陪伴她,走過無盡的黑暗和無邊的絕望。
宗璞大師姐靜靜地聽我說,沒有打斷我。只是在我說完,深深地看着我,輕輕地說:「我知道的,我知道的。」
歲月帶不走的年華光彩
我們說了一會話,宗璞大師姐想起來送我她的三卷本《野葫蘆引》。過了一會兒,又說:「把我的那本散文集《雲在青天》也送給張惠一本。」而且,在汗牛充棟的藏書中她歷歷不爽地記得自己著作的藏身之處!真是讓我驚嘆,她的記憶力真是非常非常好,簡直我們年輕人都比不上她。
臨走的時候,宗璞大師姐還給我出了一個題目,她說:「妳看古詩裏面經常把在外的遊子比喻成王孫,比如說『芳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等等,他們未必都是王孫,那為什麼要把他們說成是王孫呢?」我首先跳到腦海裏的想法:是不是提高了他們的地位?但是我也不敢確定,所以回答說回去好好查閱一下。

曼菱師姐告訴我,宗璞大師姐來雲南田野調查的時候,一點也沒有名門之女的驕嬌二氣,而是事必躬親,親力親為。
我想起宗璞大師姐《雲在青天》的記載,她曾經去北大校醫院看望自己的老師:一位美國教授。那個教授想出去走走,一個護士說:「外面下着雨呢,不能出去」;另外一個護士說:「就是外面不下雨,也不能出去」,因為那個時候她的老師已經100歲了。
可是那個老師就用英語說:「哎呀,讓我出去。」宗璞大師姐可能看到了老師眼睛裏面的那種非常充滿了希望的光芒,我覺得當時這對她也是一種震撼吧!所以她到雲南的時候,她也堅持自己親自去考察。
宗璞大師姐的精氣神也給了我很大的震撼,你看一下照片中她的眼睛多亮呀!就跟我的眼睛那麼亮似的。要知道,宗璞大師姐做過三次視網膜脫落的手術,可是她的眼睛沒有老年人那種渾濁,還是那麼閃閃發光的感覺,我感到心裏特別高興。
記得剛見面宗璞大師姐劈頭就說:「妳的《紅樓夢研究在美國》我看過了,寫得不錯,很下工夫,讓我瞭解了很多現在國外對《紅樓夢》的研究情況。」我當時楞住了,因為知道宗璞大師姐現在眼睛不太好,無法閱讀,怎麼看的呢?原來她竟然是讓人一字一句的念給她聽,聽完了絕大部分。要知道我那本書可是三十多萬字啊!驚訝和感動一時全涌上心頭,卻不知說什麼好。
銀杏生紅豆 紫花盛轉衰
在拿書的間隙,我看到書桌的玻璃板底下壓着幾片銀杏葉。我問宗璞大師姐是不是從燕園帶過來的?她卻說不是,他們河南老家也有銀杏樹,是老家人送來的。可能是同鄉的緣故吧,我陡然對這幾片銀杏葉更多了幾分親切。書桌左邊牆上懸着宗璞大師姐最喜歡的一片大理石,使我想起文天祥的「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可是那個著名的紅豆呢?那個裝在「小小的有象牙托子的黑絲絨盒子」裏,「鑲在一個銀絲編成的指環上,沒有耀眼的光芒,但是色澤十分勻凈而且鮮亮」的「血點兒似的兩粒紅豆」呢?我知道這是小說的虛構,但因它那樣親切那樣實在,簡直覺得是實有其物了。
我們都是從她那篇優美得像詩一樣的小說《紅豆》對這兩顆紅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作者本人卻為此吃盡苦頭。短篇小說《紅豆》宗璞大師姐創作於1956年12月,並於1957年在《人民文學》「革新特號」上刊載出來。文章發表以後當即引起讀者的喜愛,同時也引起了文學界的不少爭論。
在「反右」鬥爭開始後,《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文藝月報》等先後登載了批判《紅豆》的文章。宗璞大師姐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焦慮和悲痛一直壓在她心頭,後來弟弟又身患絕症。宗璞大師姐於悲痛徘徊之際,見一樹盛開的紫藤蘿,由花兒自衰到盛,睹物釋懷,感悟到人生的美好和生命的永恆。

就像她在《紫藤蘿瀑布》裏面說的:
花和人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長河是無止境的。我撫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艙,那裡滿裝生命的酒釀,它張滿了帆,在這閃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萬花中的一朵,也正是一朵朵花,組成了萬花燦爛的流動的瀑布。在這淺紫色的光輝和淺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覺加快了腳步。
往事黑暗 生命仍薪盡火傳
宗璞大師姐的父親馮友蘭先生在多次住院、雙目幾乎完全失明的情況下,95歲高齡時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如今,也是雙目幾乎完全失明的宗璞大師姐每天上午依然堅持寫作,繼續撰寫曾獲得「矛盾文學獎」的《野葫蘆引》的最後一卷,這種以生命弘道的文化基因可謂薪盡火傳。
宗璞大師姐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遭受這樣無理嚴厲又無情的批判,飽受重重打擊,卻不放棄不絕望,終生獻身文化事業,如今雙目難視依然筆耕不輟,真是「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她的文化執着就是她的生命線啊!
我想,傳統文化的踐履者,不但在其腹笥積厚,口吐煙霞,亦要懷有「當年蓬矢桑弧意,豈為功名始讀書」之毅士精神!
原刊於「夢影紅樓」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