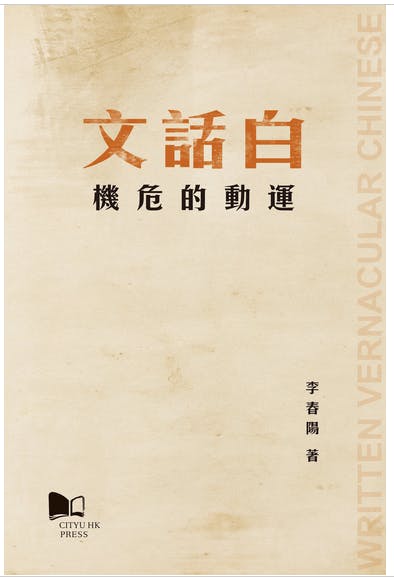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為現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重要分水嶺,尤其在學術思想史、文學及學生運動上,更是重要的課題。每於五四運動的周年紀念,更有很多追憶、紀念及研究文章,不斷表述五四運動在不同層面的歷史意義,此成為從事研究歷史學、現代文學的學者,及文學創作者的精神符號。
2019年為五四運動100周年的重要紀念日子,海內外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也多注意五四運動加速推動白話文運動發展,隨不少學者於五四運動後,奉五四運動時期提倡白話文為文學革命及新文化的代表,不少文學家及作家,更廣泛提倡白話文,攻撃文言文。
不能否認,白話文可以視為文學運動的主流,文言文視為潛流,但事實上,文言文未嘗終止。今天不少華文學界及華人作家也以文言文撰寫文稿,文言文也曾在五四運動前後,與白文並在,由是今天學者應多研究文白相存至相爭,再由相爭發展至並存的過程。這不獨是研究近代中國文學發展的課題,也是一個研究近現代思想文化新舊並存,及展示文學體裁內部發展的真實面貌。近十多年學界也興起重估民初新舊文學、文白並存及文言在當代中國價值的風尚,此也推動學界多討論今天雖重視白話文,但是否要併棄文言文。
自明代至今的漢語發展為一個整體
近閱李春陽《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一書,提出「白話文運動的幻想在於,以為消滅了文言,就可以徹底擺脫過去的不良影響,把外國好的思想、德賽二先生辦為白話,就可以得到文化上的更生了」(頁liv),作者更視自明代至今天的漢語發展為一個整體,「把百年來的語言變遷運動,放在千年來漢語的雙重機制——文言白話並存的背景上加以考察」,「致力於揭示白話文運動的意識形態本質,但本文並不是反對白話文」(lx)。作者不只是研究文、白的論爭,更注意從學術史、思想文化史及近現代文學發展的角度,研究一種文體的演變及其與時代互動關係。本書也更呈現以下特色。
其一,作者成功表述不少五四時期撰寫推動白話文的作家,也是不反對文言文。書中第二章〈白話文運動的內與外〉歸納不少五四時作家的觀點,認為白話文運動是「一種話語變革,而非語言變革,但它實在從開始就誤解了自己的使命」(頁75),如魯迅、周作人、胡適等人提倡白話文,主要是以「革命思路佔上風」,而魯迅於五四運動時期,是出自五四文學革命的立場,寫作實踐,始終遵從文字語言的內在規律,不在文言與白話之間的抉擇,文白相間,也不是廢文言,用白話,在作者看來魯迅更成功表現了「調動兩者的優勢」(頁96),周作人雖提倡白話文,但周作人多次說儒家思想,周作人自己認為是「儒」者,更認為中國固有的國民思想也是儒家的,周氏在〈國語改造的意見〉中,已說改變語言畢竟是不可能的事,一民族之運用其國語以表現情思,不僅是文字上的便利,遠有思想上的便利更為重要。胡適更言中國傳統史籍《史記》、《漢書》也有很多白話,古樂府詩也是大部份白話的,在創作上實是文白並重。
作者在書中也舉出五十年代,五四時期第二、三代文人,如唐君毅、方東美、余英時等,他們在香港、台灣及北美推動新文化復興,他們運用的語言也是文白夾雜,不是只運用白話文。
作者又廣泛引用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提倡白話的言論,指出雖然白話文一派佔優,但懷疑文言是否絕對被排斥,蔡氏也認為文言文為美文的語言,不會被廢除,白話文有利於應用文。作者又廣泛引用於1949年前民國政府的公告文獻,書寫的內容也是文言與白話並重,乃至1949年底,中國國內仍可以文言與白話並行,故作者說「由於西方觀念和思想的引入,新文學運動的確開創了新的意義空間,但是在語言上,是否存在同樣的斷裂,本書非常懷疑」。
其二,作者列出民國時的高等院校,仍開辦文白兼備的課程。書中引用新文學的重要人物朱自清,於1929年在國立清華大學創立並開設「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朱氏已說當時大學中文系的課程還有濃厚的尊古之風。1940年西南聯大中文系系主任羅常培認為中國文學系,就是研究中國語言文字,中國古代文學的系,愛讀新文學,就不該讀中文系。
誠如作者所言新語彙、歐化句法,乃是「濃重的意識形態指向,激進的反傳統立場,以及最後,可能也最關鍵的,就是改造語言,再造白話的理想」(頁245),及至文化大革命前夕,雖然文言被打倒,但也把「文言的思想意識和價值取向,順勢轉入舊白話的言說空間」。(頁250)

從中國文學史的角度,溯源白話文
其三,作者從中國文學史的角度,溯源白話文。李氏指出早於魏晉時,翻譯來自天竺梵文的佛經,唐以後大量譯經,促成佛經以外的文本,變文俗講傳入中國,乃至宋元時代,白話大盛,元代的詔書雖是蒙語,也譯為白話,清朝的白話小說如《紅樓夢》、《兒女英雄傳》均是盛行,這樣成功證明白話文早已發生,「文言從來不是白話的對立面,毋寧說它是白話文的高級階段」(頁436)。同時,作者也指出在近代白話文運動興起之前,古文內部也要求變革,清代洞城派學者要求的義理、考據、辭章,也見文言內部進行改革,成功反對部份學者認為用白話才是語言改革的重要工具。周作人也於1932年已發文表述明朝的公安派、竟陵派的文學作品,是近代中國文學的起源,「胡適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頁451)。
其四,作者深入研究,成功指出五四運動語文改革的矛盾,源自五四作家及學者對「歐化」的理解。書中第七章談及五四一代的共識視語言為改良工具,「然而語言本身就很難改良,不宜改良」(頁619),早於唐代韓愈提倡以模仿古人為能事,依傳統才可以進行改革,但近代白話文運動則以模仿洋人為圭臬,周作人已提出現代國語的建設,是用普通語加以改造,但五四時期的不少作家認為輸入歐化,並用以改革國語為職志,乃不知不同的語言,不可以同化。作者更指出從翻譯文化帶動「翻譯白話」,終致傾銷「歐化語言」,因為文言與白話對立,只知「盲目追求純粹白話」,不知「自有漢語書面語以來,無論文言還是半文半白的混雜」(頁633),終造成文白相對,此就是五四時代,文化激進主義,由激進的語言政策導致白話主義,終導致出現文白不可並存的觀點。
最後,作者雖是研究白話文運動,反對認為文、白不能並存的觀點。然而,本書也可以作為研讀自五四運動至今中國文學史的參考書。李氏在書中也研究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大眾語言運動、民族形式論爭、文革時期文學論爭,乃至近年討論中國語文受歐化影響的問題,李春陽《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一書,可以視為半部當代中國文學史、半部中國漢語史。
書籍簡介
書名:《白話文運動的危機》
作者:李春陽
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