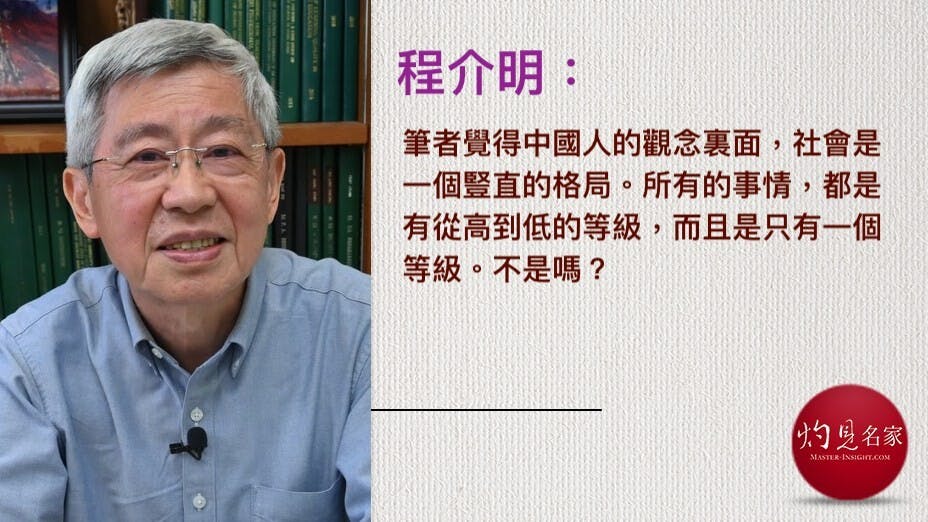這是「文化價值觀」的第四篇。上周提到Hofstede(下稱霍氏)早期四個與工作有關的文化價值觀的第一個:權威距離,也可以說是上下、長幼、尊卑之間的關係。距離遠的,就是這些關係之中,前者對後者有結構性的權威。前者可以指令後者,而後者也甘於服從;前者覺得有責任為後者做決策、安排前途,而後者也覺得可以依賴前者。
有兩點需要說明一下。一、這裏說是結構性的,就是說,是社會的結構和意識決定的,是社會的常態,而不是因為上級、長者、家長的性格、能力使然,也不是因為下級、少者、子女的性格與能力。
二、這種文化價值觀,並沒有被看成是一種壓迫關係。一方面,上、長、尊者,並不一定有欺壓、剝削、凌辱下、幼、卑者的意識與意圖;反而會覺得這是一種照顧,是為了對方好。而後者也不一定會覺得處於受壓、受欺的地位;也不一定會覺得是逆來順受。
上面這兩段話,一定有讀者覺得是在為「權威」辯護。也一定有讀者會說:那要看那權威是否合理。關鍵就在這裏,權威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但是某種權威是否合理,就有文化價值觀的因素。也就是說,同樣的一種權威,在不同的文化裏面,會有不同的價值判斷。而結構性的權威,沒有「合理」與「不合理」的元素。
長官意志 不由分說
極端的例子,軍隊,長官有絕對的權威,全球如是。理由是,在戰場上,不由得你要認為合理才服從,也不允許有反駁、爭拗,否則長官沒有了指揮權,就無法打仗。
正所謂「軍令如山倒」。這裏面,並不保證長官的命令就合理、就正確;不保證下面的士兵就理解其中的戰略奧妙;也不保證聽了直觀的命令就能打勝仗。恐怕在任何文化裏面,都是如此。
但是,在軍隊的生活裏面,會不會出現長官對下屬的壓迫與欺凌,或者對於這些壓迫與欺凌,下屬是否逆來順受,就每個文化裏面會很不一樣。美國很多的新聞、電影,都是描寫軍隊生活中長官濫用權威,欺壓下屬,甚至達到個人的利益。在美國的文化,這是不該容忍的。
雖則這些情況,也許還在不斷發生,但是文化價值觀判斷這是錯誤的行為。有這些事情發生,甚至可能有普遍性,是一回事;在新聞、小說、電影裏面貶責這些行為,卻又說明這是社會的價值觀所不容的,是另外一回事。
換句話說,在其他的國家的軍隊,有沒有長官濫權的,沒有報道,不知道。也許是根本不會發生,也許是沒有人願意透露與報道,又或者習以為常、司空見慣,那又是另外一些文化價值觀所決定的。這是在研究文化價值觀的時候,經常發生的:「你覺得對不對?」與「你覺得會不會發生?」答案可以是兩回事。其實Hofstede的探索,還研究了第三個問題:「假如你認為是不對的,但又實際上發生了,你認為是否應該容忍?」
課堂文化 教師權威
在教育也是這樣,讓我們專注學校教育,因為那是「權威」最集中發生的地方。在我們東亞「筷子文化」,上課時教師進入課堂,通常是學生起立,向教師敬禮,「老師早!」「老師您好!」「Good Morning Ms Chan!」這就奠定了課堂裏面的「權威距離」。大致來說,課堂裏面的對與錯,基本上是由教師裁定的。
華人社會的教育有一個特點,就是重視分數(當然這已經幾乎變成是全球性的現象),壞處是重視分數,不計實際的學習成效;但它有一個好處——「客觀、公平」(表面上無可爭議,雖然涉及很多問題,此處不贅)。
但是華人社會的學校,「德智並重」,傳統上還有「德育」,在學生的成績表上,除了各科分數,還有傳統的「操行」。有些學校,「操行」有甲乙丙丁。誰來定?就靠教師的主觀判斷。筆者教過一所學校,每名學生有操行分,滿分100,犯事就扣分,在教員室有一本冊子,教師可以自己在冊子上扣分。這是教師的權威,沒有學生爭辯的餘地。這也是類似上述軍隊裏的「長官意志」。
筆者初出道的時候,所謂「德育」,往往簡化為「紀律」。學校裏面,校長之下,必定是「教務主任」與「訓育主任」雙頭馬車。英文中學,這是Prefect of Studies與Prefect of Discipline。也許因為德育是無形的,而紀律是可以有形的。
最明顯的是校服,筆者做校長的時候,那是1970年代,有時候我們教師自己也發笑。為什麼?褲腳,時興闊的時候,我們要它們窄;實行窄的時候,我們要它們闊。腰帶、領帶,也一樣,興闊時不准闊,興窄時不准窄。
有些女校,規定雙膝跪地時,裙腳要着地。台灣以前女學生有標準的髮型(好像叫「髮禁」);香港也有學校,規定10度以下才能穿棉襖;等等。「犯規」的也許要記缺點,累積成為小過、大過。紀律,當然重要,那也是群體生活的學習要素。
但是,因為校服問題,而歸結為德育的過錯,好像又有點勉強,不過是容易執行而已。那也是學校可以容易行使權威的地方。
差距格局 預設等級
中國內地還有另一個方面的「權威距離」——結構性的等級觀念。有一陣有倡議學術界「去行政化」,筆者還以為是去掉那些行政主導的繁瑣管理手法,後來聽到陶西平老師(前不久離世)解釋,學術的職銜,是與行政級別掛鈎的。
才想起,當年筆者做副校長,到農村做研究,也就是普通研究員身份;然而每到一地,都會有當地的同級官員(一般是副廳級,有時候他們也搞不清楚,因為大學也有級別,相關的大學難以定級)陪同,後來簡化為請一頓飯,或者起碼要見面握握手。開放改革以後,就漸漸放鬆了。
有時候,這種等級觀念,是無形的。開會,發言是有級別的秩序的,往往是校長、副校長,順序而下。級別低的,基本上就是不會發言。改革開放以後,也逐漸放開了;像上海比較開放的城市,這種等級的痕跡,就愈來愈不明顯。
其實,在香港也有類似的情形,但是每所學校不太一樣。一個極端,開會基本上是校長一言堂,甚至有校長一個人講到晚飯時刻還沒有倦意的;另一個極端,開會時嘰嘰喳喳討論非常熱烈的。也就是說,每所學校內部的文化價值觀——權威距離——都有它自己的特點。
費孝通的《鄉土中國》,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個「差距格局」,在他的啟示下,筆者覺得中國人的觀念裏面,社會是一個豎直的格局。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從高到低的等級,而且是只有一個等級。不是嗎?進了大學不算數,要進了北大、清華才算真正成功。不是講好壞,而是要贏,不能輸。幼兒,是否健康成長不要緊,就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
讀者會說,西方社會不也是有等級嗎?對。然而,西方的等級,是在現實的需要、競爭中形成的。個人、機構,在開始的時候,都是平等的,等級不是結構性地預設的;而且等級的「梯子」可以有很多道,這裏爬不上,可以爬另外一道。
中國的「差距格局」,也許是孔子留下來的。是當時維持封建社會秩序的一種方法,在那個時代,也許是行之有效的;歷久不息,貫串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因此成為文化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深深地印烙在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上面,是絕對的差距競爭。
但是,文化價值觀是會變化的。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由於引進了市場機制,就出現了突破結構性等級的情形。以後有機會再討論。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