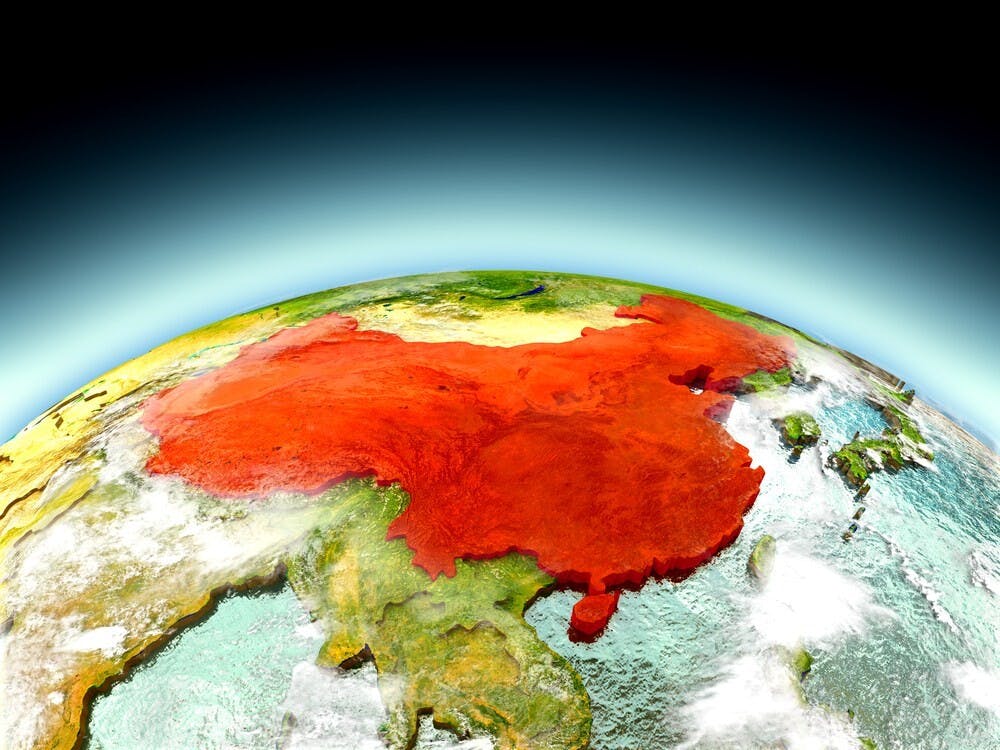中國的開放來之不易,中國的全球化更是來之不易;或者說,無論是開放和全球化在中國並不是必然的。中國歷史上曾經非常開放,明清之後數百年一直處於孤立狀態。直到近代,中國被西方帝國主義的槍炮打開大門,被迫開放。
改革開放之前的數十年裏也是處於相對的封閉狀態,只和有限的國家交往,改革開放之後才開始主動向西方開放。不過,向西方開放是血的教訓換來的。在1980年代,當鄧小平一代領導人決定對外開放時,他們的決策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判斷:封閉就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如果近代是因為挨打而被動開放,改革開放就是主動向世界開放。
中國的開放對中國和世界都是一個機遇,這也是開放政策比較順利的原因。這裏面有一個中國和西方世界之間推和拉的互動關係。中國主動推,積極推動自己的開放政策,西方是拉,拉一把中國,即歡迎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但中國和西方世界的全面交往和融入,是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的事情。
毋庸置疑,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轉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從封閉狀態轉型成為最大貿易國家,從農業大國轉型成為世界工廠,所有這些都是中國開放政策的結果。
冠病疫情會成為中國和西方世界的熔斷器,熔斷兩者之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關聯,導致中國的再次封閉起來嗎?
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一些人可能對此不以為然,因為他們總是認為中國和西方世界已經深度融合,沒有可能被冠病疫情所熔斷,更不用說中國再次封閉起來了。的確,直到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中美貿易戰,人們一直相信中國和西方經濟互相依賴的力量。美國的一些人甚至將其稱之為中美國,而中國的一些人稱其為中美婚姻關係。
中國繼續推進全球化的決心
即使在美國開始搞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領導層仍然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多個場合表示決心繼續推進全球化。中國也是這麼行動的,通過艱苦的努力和美國談判,達成了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但冠病疫情似乎正在改變一切。儘管改革開放40多年了,儘管人們以為中國已經深度融入世界體系,但突然間,人們發現中國其實還沒有準備好接受世界,西方也沒有準備好接受中國。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尤其是美國),勃興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不僅在促成中國和美國之間冷戰的升級,更指向中美局部熱戰的可能性。
事實上,中美(和西方)之間從往日的推和拉的關係,已經演變成為擠和退的關係,即美國(和西方)想把中國擠出世界體系,而中國自己也在無意識地退出這個體系。也就是說,中國和西方已經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馳了。
首先是西方的擠。西方對中國的不放心由來已久,也可以理解。自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西方盛行不同版本的中國威脅論,無論什麼樣的理論,其背後折射的是對中國的不放心。對一個具有不同文明文化、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價值體系的國家,西方國家的這種不放心情有可原。但也正因為如此,西方和中國從來就沒有建立足夠的政治信任,各種關係皆維持在利益關係上。
這也可以理解,國家間的關係都是利益關係,唯有利益是永恆的。不過,光有利益關係並不足夠。如果利益是硬力量,信任就是軟力量。沒有軟力量,硬力量就很容易被理解成為一種威脅。實際上,在冠病疫情之前的中美貿易戰過程中,西方很多人就一直批評中國,把世界和中國之間的經濟依賴度武器化,即中國利用這種高度依存關係來追求自己的利益。儘管武器化一直是西方對非西方國家慣用的手法,即經濟制裁,但因為對中國的不信任,即使中國並沒有武器化,也被西方認為中國在這樣做。
從不相信中國到感覺到中國的威脅,到排擠中國,這是西方的行為邏輯。中美貿易戰無疑是西方和中國關係的轉折點。之前,西方總是認為有能力改變中國,通過把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把中國塑造成他們想看到的國家。但貿易戰意味着,西方(尤其是美國)放棄了這一西方學者認為是天真的想法。既然改變不了中國,就轉而排擠中國。
病毒所引發的西方(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惡化,就是這一邏輯的延伸。從一開始,美國的政治人物就是有其議程的。對疫情在美國的擴散,他們從來就沒有承擔過任何責任,而是一直把責任推到中國。從病毒冠名之爭和病毒起源的各種陰謀論,到後來的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指責和對中國秋後算賬,各種行為都是這一議程的一部分。
很顯然,這種行為邏輯不僅屬於美國,也屬於整個西方世界。儘管中國在本土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後,盡力向包括一些西方國家在內的100多個國家提供醫療衛生物資,但西方對中國的不信任不僅沒有降低,反而急劇增加。中國的對外醫療援助被視為口罩外交影響力外交和地緣政治外交。秋後算賬的聲音在整個西方世界盛行,英、法、德高官也直接或間接地指責中國。
除非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西方和中國的關係出現逆轉,否則西方新一波更大規模的反華和反中浪潮不可避免,無論是在疫情之中還是疫情之後。
在西方對中國轉向擠的時候,中國本身也從推轉向了退。退不是表現在物理和物質意義上,而是表現在思想和態度上。實際上,在物理和物質意義層面,正如一帶一路倡議等項目所顯示的,中國近年來剛剛走向世界。然而在思想和態度層面,很多人開始從世界體系回撤,以至於愈來愈多的中國人也持有了美國人一般的我就是世界的心態。

民族主義的崛起與國際化
改革開放無疑促成了中國經濟愈來愈國際化。直到今天,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國的經濟都是相當國際化的。就投資貿易開放度來說,中國甚至比西方一些國家更加國際化。
人們的心態則愈來愈內向,即向內看。產生這種傾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義的崛起。因為國家的快速崛起,人們對國家的崛起變得無比自豪。同時,經過那麼多年的開放,很多人看到西方的體制原來遠非過去所想像的那麼美好,不過如此。這無疑是積極正面的。
但是,人民在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時候,並不十分了解這成果是如何得來的,國家是如何崛起的。儘管沒有人會否認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國家的崛起,是中國人民辛苦勞動得來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也是中國和西方互動的成果。如果沒有西方的拉的一面,中國儘管也會最終崛起,但崛起會困難得多。
沒有這個認知,愈來愈多的人就驕傲起來。在一段時間裏,超越西方的聲音盛行,人們相信西方已經衰落,中國已經全面超越西方。當然,也有很多人開始當西方的老師了。
但是,一旦面臨日益惡化的外部環境,而物質(尤其是技術)面受到西方大力擠壓的時候,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力量更傾向於內部化。人們不是像從前那樣選擇和西方互動,向西方學習,而是開始抱團取暖,通過團結內部力量來應付惡化的環境。這自然也符合行為邏輯,但這顯然是一種惡性循環。
冠病疫情發展至今,很多人的行為就是如此。民間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導致社會內部的急劇分化,每個人的意識形態認同都是旗幟鮮明,自己人和他人之間的關係猶如井水不犯河水。圍繞着《方方日記》和其人其言的種種爭論,使人想起了歷史上所發生過的攘外必先安內場景。
儒家社會本來就比較保守,比較內向,所以儒家社會的國際化很不容易。在東亞,日本和之後的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現在都是高度國際化的社會,但這些社會的國際化都是人為的結果。這些社會都是精英統治的典範,而精英是高度國際化的。因為近代以來,尤其是二戰之後,這些社會屬於西方陣營的一部分,因為精英了解這個西方世界是如何運作的,也努力促成社會和國際的接軌。
但今天的中國似乎不是這樣。不難看到,被視為最了解國際形勢和西方世界的精英,都變成最具民族主義色彩的一群,他們不去引導民眾,而是主動屈服於、甚至訴諸民粹。如此,其後果是不言自明的。
很多官僚部門不作為。人們忘記了,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而且經濟深度融入國際,實際上,國內和國際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界線;也就是說,內部發生什麼都會對外部產生巨大的影響。人們不禁要問,無論是地方政府官員還是從事戰狼式外交的人們,他們在說話做事的時候考慮到外部影響嗎?可能沒有,更有可能的是把中國當成了世界。否則,如何解釋這段時間裏頻繁發生的外交事件呢?
精英部門是這樣,民間更是如此。實際上,精英和民間是互相強化的。在自媒體時代,商業民族主義已經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愈來愈多的自媒體投入到愛國主義這一蒸蒸日上的行業之中。媒體操作和資本逐利可以理解,但管理部門為什麼也不作為?如果說對政治上敏感的媒體與人能夠有效管治,對類似xx國想回歸中國那樣愚昧無知,又能產生極其負面國際影響的的言論,難道不應當進行有效管治?
一旦有了退出世界的心理,人們與世界的心理距離愈來愈遠,和世界隔離的心牆會愈來愈高、愈來愈厚。以至於一旦走出這堵又高又厚的牆,人們猶如外星人,不知道如何與世界溝通,更不知道與世界溝通什麼。自然,世界也並不認同走出這堵又高又厚的牆的人們了。
「我就是世界」離封閉不遠
從經驗來看,如果有了我就是世界的觀念,離再次封閉也就不遠了。歷史上就存在過,筆者稱之為明朝陷阱。明朝有一段時間,無論從國家能力(例如鄭和七次下西洋)還是社會能力(例如反映民間海商力量的所謂倭寇),在當時都是天下第一。但在天朝什麼都不缺,哪用得着開放的心態主導下,明朝實行海禁,最終使得中國失去了海洋時代。清朝繼承了明朝的遺產,閉關鎖國,直至近代被西方徹底打敗。
但這並不是說,再次封閉是必然的。其實,自始至終,並非整個國家都驕傲了,也有清醒的社會和精英群體存在;尤其重要的是,領導層一直是清醒的。早期,領導層的清醒表現在和西方世界進行求同存異的互動,他們不僅發現了和西方世界的共同利益,更發現在一些共同價值觀上,也是可以和西方討論對話的。
在一段時間裏,中國和西方也進行了價值觀(包括民主和人權等)的對話。儘管並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因為中國本身也具有和西方不同的價值系統,對話可以,但並不能互相取代。但這種對話本身很重要,因為它指向人們心態的開放。
這些年和西方世界的對話因為各種原因少了,但領導層在一如既往地全力推動全球化。很顯然,領導層對中國崛起所面臨的挑戰具有清醒的認知。就以人們引以為傲的製造業來說,中國所處的現實仍然嚴峻。被視為處於衰落之中的美國仍然遙遙領先,處於第一梯隊,歐洲國家和日本處於第二梯隊,而中國仍然處於第三梯隊,甚至更低一些。
考慮到中國目前所處的地位,是前面所說的中國推和西方拉的結果,也就是西方技術在中國的擴散效應,中國如果要成為製造業大國,還須有30年的時間。簡單地說,如果美國和西方國家能夠生產大量的整裝產品,中國的很多產業仍然停留在組裝階段,中國的整裝產品少而又少。
無論美國和西方如何對付中國,中國不會停止發展,更不會滅亡。不過,隨着西方的擠和中國的退,中國再次封閉起來是有可能的。曾經被拿破崙稱之為東方睡獅的中國,會不會剛剛醒來不久之後又睡着了呢?沒有人可以對此掉以輕心。這自然也考驗着這一代人。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