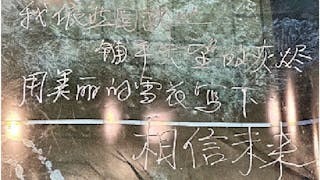編按:本文全部選自雨果《巴黎聖母院》──第三卷《巴黎鳥瞰》與第一卷《大廳》。從中可以深深領略名著之精彩絕倫,以及古蹟被燒毀的痛心疾首。
您要是想獲得現代的巴黎所無法給您提供的有關這古城的某種印象,那麼您不妨就在某一盛大節日的清晨,在復活節或聖靈降臨節日出的時分,登上某個高處,俯瞰整個京城,親臨其境地體驗一下晨鐘齊鳴的情景。等天空一發出信號,也就是太陽發出的信號,您就可以看見萬千座教堂同時顫抖起來。首先是從一座教堂到另一座教堂發出零散的叮噹聲,好像是樂師們相互告知演奏就要開始了。
然後,突然間,您看見──因為似乎耳朵有時也有視覺──每一鐘樓同時升起聲音之柱,和聲之煙。開始時,每口鐘顫震發出的聲音,清澈單純,簡直彼此孤立,徑直升上燦爛的晨空。隨後,鐘聲漸漸擴大,溶合,混和,相互交融,共同匯成一支雄渾壯美的協奏曲。最後只成為一個顫動的音響整體,不停地從無數的鐘樓發出宏亮的樂聲來;樂聲在京城上空飄揚,蕩漾,跳躍,旋轉,然後那震耳欲聾的振輻漸漸搖蕩開去,一直傳到天外。
然而,這和聲的海洋並非一片混雜;不論它如何浩瀚深邃,仍不失其清澈透亮。您可以從中發現每組音符從群鐘齊鳴中悄然逃離,獨自起伏迴盪;您可以從中傾聽木鈴和巨鐘時而低沉,時而高遠的唱和;還可以看見從一座鐘樓到另一座鐘樓八度音上下跳動,還可以看見銀鐘的八度音振翅騰空,輕柔而悠揚,望見木鈴的八度音跌落墜地,破碎而跳躍;還可以從八度音當中欣賞聖厄斯塔舍教堂那七口大鐘豐富的音階升降往復;還可以看見八度音奔馳穿過那些清脆而急速的音符,這些音符歪歪扭扭形成三四條明亮的曲線,隨即像閃電似地消失了。
那邊,是聖馬丁修道院,鐘聲刺耳而嘶啞;這邊,是巴士底,鐘聲陰森而暴躁;另一端,是羅浮宮的巨塔,鐘聲介於男中音和男低音之間。王宮莊嚴的鐘樂從四面八方不停地拋出明亮的顫音,恰好聖母院鐘樓低沉而略微間歇的鐘聲均勻地落在這顫音上面,彷彿鐵鎚敲打着鐵砧,火花四濺。您不時還可看見聖日耳爾·德·普瑞教堂三重鐘聲飛揚,各種各樣的樂聲陣陣掠過。隨後,這雄壯的組合聲部還不時略微間歇,讓道給念聖母經時那密集應和的賦格曲,樂聲轟鳴,如同星光閃亮。在這支協奏曲之下,在其最悠遠處,可以隱隱約約分辨出各教堂裏面的歌聲,從拱頂每個顫動的毛孔裏沁透出來。
誠然,這是一出值得人們傾聽的歌劇。通常,從巴黎散發出來的哄哄嘈雜聲,在白天,那是城市的說話聲;在夜間,那是城市的呼吸聲;此時,這是城市的歌唱聲。因此,請您聆聽一下這鐘樓樂隊的奏鳴,想像一下在整個音響之上彌散開來的50萬人的悄聲細語。塞納河亙古無休的哀訴,風聲沒完沒了的嘆息,天邊山丘上宛如巨大管風琴木殼的四大森林那遙遠而低沉的四重奏;如同在一幅中間色調的畫中,您再泯除中心鐘樂裏一切過於沙啞,過於尖銳的聲音;那麼,請您說說看,世上還有什麼聲音更為豐富,更為歡快,更為燦爛,更為耀眼,勝過這鐘樂齊鳴,勝過這音樂熔爐,勝過這許多高達300尺的石笛同時發出萬般鏗鏘的樂聲,勝過這渾然只成為一支樂隊的都市,勝過這曲暴風驟雨般的交響樂!
毫無疑問,拉瓦伊阿克刺殺亨利四世,才會有拉瓦伊阿克案件的卷宗存放在司法宮檔案室裏,才會有他的同謀犯處心積慮要把本案的卷宗毀掉;因此才會有縱火犯由於別無良策,只好放火焚燒檔案室,好把卷宗燒毀。總而言之,就才會有1618年那場大火。若不是那樣的話,古老的司法宮及其古老的大廳也就屹立如故,我也可以奉告看官:您親自去看吧!於是,咱們倆都不必多此一舉:我免得如實進行描述,您也就省得閱讀了。
不可估計的後果
這樣的一條新真理就被證明:一切重大事件必有不可估計的後果。
不過這也可能是真的:首先,拉瓦伊阿克沒有同謀者;其次,即使萬一有,他的同謀者也可能與1618年那場火災毫無關係。這樣,那場大火的起因就有其他兩種解釋,都是合情合理的。第一種解釋是:有顆熊熊燃燒的大星,一尺寬,一肘高,如眾所周知的,3月7日半夜後從天上墜落,恰好落在司法宮裏。第二種解釋是見諸於泰奧費爾的四句詩:
誠然,那是悲慘的遊戲,
正義女神在巴黎,
吃了太多香料,
自把宮殿焚為平地。
這是1618年與司法宮那場大火從政治的,自然的,詩歌的三個角度的三種解釋,不論人們對此想法如何,不幸的火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由於這場災禍,更由於連續修建把倖存的東西也毀了,所以時至今日也就所剩無幾,這座法蘭西最早的王宮也就所剩無幾了。堪稱是羅浮宮長兄的這座宮殿,早在美男子菲利浦時代就已很老了,有人還到裏面去尋找羅貝爾國王所建造的,埃卡迪斯所描述的那些華麗建築物的遺跡,幾乎一切蕩然無存了。
想當初,聖路易院完婚的樞密,洞房今安在?他在御苑審理案件,「身着羽紗短襖,無袖粗呢上衣,外罩披風,腳趿黑絆拖鞋,同儒安維爾臥在地毯上」,御苑今安在?西吉斯蒙皇帝的寢房現何在?查理四世的呢?無采邑王約翰的呢?查理六世站在樓梯上頒布大赦令,那座樓梯今何在?馬塞爾在太子面前,殺害羅貝爾·德·克萊蒙和香帕尼元帥,那現場的石板今在哪裏呢?
從一道小門宣布的廢除偽教皇貝內迪克的訓諭,他的那班傳諭使者們給人醜化,身披袈裟,頭戴法冠,也是從這道小門出去遊街,走遍巴黎大街小巷,向民眾賠禮認罪,現在這道小門又在哪裏?
還有那座大廳,金碧輝煌的裝飾,扇扇尖拱窗戶,尊尊塑像,根根大柱,鏤刻成塊塊圖案的寬闊拱頂,這一切如今又何在?還有那金燦燦的臥室呢?
那隻守門獅子,就像所羅門座前的獅子一般;耷拉着頭,夾着尾巴,顯出暴力在正義面前那副卑躬的模樣,這石獅子又在何處呢?還有那一扇扇絢麗的門扉呢?那一扇扇斑斕的彩色玻璃窗戶呢?還有那叫比斯科內特望而生畏的房門上鏤花金屬包皮呢?還有德·昂錫打製造的精緻木器呢?
……歲月流逝,人事更替,這些稀世之寶終於成了什麼呢?人家為了代替這一切,代替這整個高盧歷史,代替這全部哥特藝術,塞給了我們什麼名堂呢?
取代藝術的,無非是德·普羅斯大人那種笨重扁圓的穹頂,如聖熱爾韋門那種蠢笨的建築物;至於歷史,我們聽到許多對粗大柱子喋喋不休的憶述,巴特呂之流嘮嘮叨叨的聲音還在震響,時至今日!
原刊於夢影紅樓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