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日子以前,湯一介先生在「世紀大講堂」上,談中國古典思想。完結前,特別提到亞里士多德(為省篇幅,後文盡量簡稱亞氏),說他是西方古典思想界的表表者,值得大家研究。但為什麼要研究他的《倫理學》?再問︰為什麼讀過《倫理學》後,還要繼續讀他的「下集」──《政治學》?後一個問題,亞氏在《倫理學》一書結束以前,自有解答。我們不必在這裏「搶答」。那前一問題呢?
假定說,讀這本書,為要探索西方思想本源,那為什麼不從亞氏的老師入手?為什麼不先讀柏拉圖的作品,特別是《理想國》?這話不無道理。我也細想了好一會,才決定先選《倫理學》。
在古代希臘思想中,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沒有明顯的分界線。不過作者的表達形式,卻有不同。柏拉圖的道德學說比較抽象,更牽涉好些神話。亞氏的道德論述也有抽象的地方;但大體來說,比較「平易近人」。即使沒有受過哲學訓練的讀者,只要稍有耐性,都不難看得懂。為了讓讀者知道兩位智者的同異,我也在書中恰當的地方,把兩人的說法並列。
亞氏的論點,和我國先秦儒的看法有合有不合。但起碼,中國人看起來,總比較容易產生熟悉感。對一般讀者來說,這很有用。固然也有不合的地方;但比起柏拉圖的理論來說,陌生感與差距感,是小了。這點也十分重要。
一定有人會問︰這本書有什麼用?我倒要反問一句︰在西方學府,到今天還在讀的古代經典不多,《倫理學》是一本;為什麼?再說,什麼叫「用」?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用」,還是「學以致用」的「用」?這本書的特點,是體用合一;任何人好好讀過,都可以派上用場的。我們說的倫理,自成系統很久,從來沒有比較。近代學術,着重「參照系」。和中國的相比,亞氏的道德著述,就是個非常有價值的參照系。同意不同意他的論點,還在其次;最低限度本書幫助我們了解,中西同異的根源在哪裏。僅僅這一點,就可以說《倫理學》很有用。
《倫理學》假如是一本抽象的、純道德理論的作品,也許就不值得大家去細讀。它固然是談道德哲學的,可它更是指路明燈︰它告訴讀者,道德是怎樣實踐的。道德實踐,如果只是適合古代社會,那我們也不必特別關注。亞氏的教誨,不合現代社會嗎?
1976年,博克(Derek Bok)當哈佛大學校長。他提出當年引起學術界廣泛討論的問題︰你怎樣教導倫理學?按他日後的說法,是因為認為,當時的學院內外,包括了學院中的哲學教授,都不曾認真面對道德實踐的問題。終於,在1986年,他籌辦了一所探討倫理學的中心,設在哈佛校內。2007年5月,中心請來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泰·森(Amartya Sen)教授,特別主持了一系列討論會。主題正是怎樣實踐倫理和公義。森教授講題的主人公,一古一今。古是亞氏,今是羅爾斯(J. Rawls)。如果亞氏哲學不合今人所需,也沒有人會再提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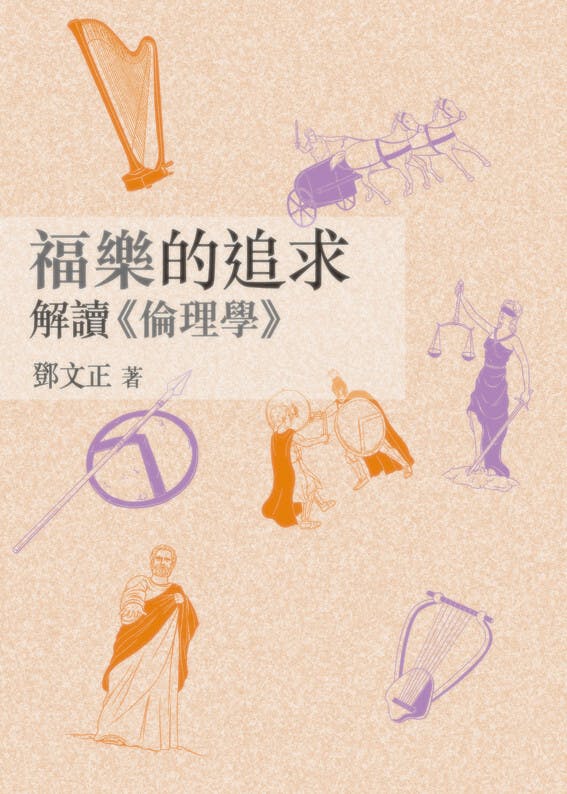
當然,亞氏的論述,不是本「會議手冊」;他還是有自己的理論的。我們也得虛心求學,才可以有所得着。就讓我先概略地介紹本書的綱領吧。
情誼和公義 關乎同樣情事
古典希臘人材輩出,傳世作品不少。花上整本書來探討道德哲學的,首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該書享負盛名,歷兩千年不墜。亞氏推崇「德善」(moral virtue,道德行為上的美善)──也就是人在倫理層面所能發揮的優點,說那是事物兩端的「中點」,是人追求福樂所不可或缺的。奇特的是,全書開十卷(依次列出,分別是︰(一)美好事物、(二)德善本源、(三)德善種類(上)、(四)德善種類(下)、(五)特別的德善──公義、(六)論智善、(七)論克己、(八)論情誼(上)、(九)論情誼(下)、(十)論快慰與福樂),每卷長度相若,泛談各類德善的只兩卷半(從卷三中段到卷五結束),而卷五終卷只談一個題目︰公義。嚴格算起來,論德善本身,僅一卷半(卷三中到卷四完),而他論情誼,就用上八、九兩卷,比德善所佔篇幅還多!這就奇怪了︰明明是一本倫理學作品,怎麼會這樣的?
稍稍涉獵過亞氏作品的人都知道,除了德善以外,他尤稱頌「智善」(intellectual virtue,理性知識上的美善)──也就是人在思維層面所能發揮的優點,特別以玄思的生命為高。這一點,我們要到卷六才開始看到;然後,卷七的論述又回到道德探索上。不過,後四卷(七到十)論的,只有三大重點;自制(說克己吧)、情誼、(愉悅帶來的)福樂。三者都不是他所界定的善,也不是什麼不走極端的執中。看看卷六,論的是智善;一開卷就問,我們怎樣才可以明白何謂執中。(顧名思義,那就是不走極端的態度。)再看看論公義的卷五,問題就更突顯了︰在他眼中,公義,也算不上完備的執中,甚至只能用算術的比喻才能述說它。(中國人說公義,側重社會倫範;亞氏說的公義,側重制度法律。)那麼公義也不是嚴謹的中庸行為;而智善要明白的,更是中庸的理性基礎。
略為抽離來看,可見一個十段長的秤,像個槓桿,支點在第六段,而後四段的份量,看來比前六段較重。那是不是意味着說,知識比起行為更為重要?
本書中互有關連、前後呼應的兩大主題,是公義和情誼;公義載卷五,情誼是八、九兩卷,談的是各類身分的人際關係。兩者分別置在支點的反向。公義,是善,也類近執中;情誼嗎,不太像善,也不近執中。亞氏卻說︰「情誼和公義都關乎同樣情事。」為什麼會這樣?那得從全書的安排說起。
勇者介乎莽夫與懦夫之間
卷一一開始就說,人以追求與善俱來的最高福樂為鵠的。福樂是人在實踐美善時的靈性活動,那是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了。他在開卷沒有排除智善,但談論再三的,是高貴情操與德善。那也許不足為奇。古典哲學傾向貶抑人貪求庸俗的快慰,要求人崇尚德善。這在柏拉圖的作品中尤其易見。到了卷十論愉悅,他卻說愉悅本身不是活動,但可使活動更完善;而人得愉悅──也就是快慰的感覺,竟然屬智善多於德善。首尾兩卷像個倒向︰福樂一開始從追求高貴德善而來,到最後轉移為從追求愉悅與智慧而來。
全書首尾已經點題。現在略說其中穿插。亞氏在卷二告訴大家,人寓德性於行為。他很簡單地把德善和執中連起來,說德善屬習慣而不屬理性,也不屬人的情意欲望。然後他回頭詳論執中這個主題,說事「必連續並可分」才有執中可言;而說執中,可對事言,可對人言,兩者不盡相同。經典例子是,他說六斤食物是兩斤和十斤的「中」,但人並不一定要吃六斤才算「執中」。孔子說「勇者不懼」。亞氏說「勇者不莽不懼」;勇者,是莽夫和懦夫的「中」。

說執中,不如說中庸。亞里士多德所談的,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境界,和我們說的中庸之道,頗有吻合。待人接物,恰到好處,固然是知易行難的東西了。事物的中點是中,人情的中庸也是中,兩種情況當然有差異。為方便計,下文就用中庸吧。不過,大家得小心。我用「中庸」一詞,是「為方便計」。對中文讀者來說,「中庸」多少有個概念,所以說「頗有脗合」。但他說的接近「黃金分割」,和我們慣用的「中庸」,並不一樣。不吻合的情況可能更多。要明白雙方差異,得先讀通他的書才行。
德善,是關乎苦與樂的,或者說是帶出苦與樂的情意與行動。那麼,苦與樂、情與行,都是道德行為上的。為什麼可以這樣看,暫時還不清楚。起碼,我們可以懷疑,這個德善有什麼理性基礎。在卷十中談到同一問題時,亞氏說愉悅與福樂,是個整體,不可分割,就像算術中的單位,幾何中的一點,或人的視覺。但為什麼善就是中庸?他跟着有解說。第三、四兩卷,談的是各項德善。首先說到的就是「勇氣」。他說勇氣是恐懼與鹵莽兩端的中庸之道。其後各項都界定得不十分嚴謹。我們可知他所云何事,卻不清楚知道何以德善是中庸,何以我們能這樣去理解它。亞氏提醒我們,說這類道德談論不是自然科學論證,不可要求絕對準繩的。
結束卷二時,他說人行善當褒,人不守中庸當貶。怎樣定奪是否偏倚行事,用的不是理智而是人的洞察力。洞察力因人而異,可以十分主觀。人的德善要能施展,需要有個共處的環境和某種客觀的準則。這準則,在卷五給籠統叫作「公義」。
卷六論的是智善。一起卷亞氏就說,他要看中庸是否理智決定的。完卷時他說,善不歸在理智旗下,它只是與理智相一致而已。那麼說人洞世事、察人情、施褒貶,不從理智來,卻可能與理智相去不遠。
福樂不能缺少快慰
「克己」是第七卷的主旨。亞氏說克己並不就是善,卻與善同類;它也是從習慣而來,卻受理性影響,甚至支配。克己與卷三談的節制有度相近──都跟苦樂有關,尤其涉及觸感。(所謂觸感,是指人的經驗知識。經驗知識通過五覺而來,左右着人怎樣趨樂避苦。)看起來,倒像重述卷三似的。讀者會問︰有節制者與克己者有何區別?亞氏說,克己者有低俗的欲望,有節制者沒有。那是說,克己者才真正表現出他有駕馭欲望的能力;而低俗欲望,從柏拉圖開始,就是人靈性中最底部分,必須讓理性束縛。所以克己者是最完整的,最能給理性來指引行事的。奇特的是,亞氏提到過度孝順之弊,還用上兩則軼事,披着「暴躁是自然」的外衣,給撻父掩過。談克己用這類例子,是不是伏筆?卷七終卷前,他指出追求賞心樂事是人性本然,花了好些筆墨給愉悅「平反」。那是卷十的先聲了。
卷八、卷九詳細討論的,是「情誼」。剛提過,那是人與人的某種關係,包括人對他人的、人對自己的。中國傳統的五倫,他都談論到;也細細地推敲,為什麼友誼佔那麼大的比重?為什麼人追求最大的自足,會發現「對己」的情誼會比「對人」的為高?為什麼最崇高的情誼,是哲學性質的?為什麼人對別人的情誼,必然是近親遠疏的?如果人在社會生活,和遠近的人都要打交道,那「情誼」可以站什麼位置?為什麼它不能應付所有問題?為什麼到最後得回到公義上去?亞氏論五倫,明顯把政治層(君臣)分了出來,認為不能混為一談;這跟傳統儒家說法全不一樣。他論父子,更會教一些讀者讀來難堪。大家也許有這麼一個印象︰不必說最高的福樂了,就是最高的情誼吧,也不容易得到呢!

卷十是《倫理學》最後一章。全卷分幾部分。首先重拾愉悅,跟着是福樂的最後定論,認為福樂必然是賞心樂事,所以不能缺少快慰。但接下去的,卻是兩組互需調洽的事物︰一是對哲學的推崇,一是向政治的過渡。亞氏花了不少筆墨,說玄思是最高境界;也就是說,人的哲學活動能帶來最美好的福樂;甚至認為,那是最能接近諸神所處的福樂世界;可諸神高高在上,並不需要靠賴什麼德行,來享有最高的福樂。那豈不是說,追求最高境界──像諸神的福樂境界,是一種精神境界,或者說哲學境界;那是智善層面的。這樣看,是智善高於德善了。
探討政治 使人間智慧臻完美
但眾生不是神。眾生是群體動物,在社會相處,必須靠德善來維繫。這就有賴教化。教化,需要有智慧的人來實施。(在我國古代,這叫「先聖昔賢之教」,或者是「先王之教」。)那麼眾生的德善教化,可以靠智者來達成嗎?不管怎樣,全書最後的述說,在表明老百姓有恰當的道德教育──也就是和諧的政治生活,所需的不是哲學家而是政治家。但政治家缺乏理論的認識,也不懂導民為善,所以,當政的要向有智慧的學習。亞氏跟着說,他的前賢並沒有好好探討立法的問題,所以他要在他的《政治學》裏詳為陳述。看來他是相信,他自己才明白什麼叫平章百姓。
如果玄思是最高的福樂,那為什麼哲學家要那麼不憚煩,去教化百姓?我們不肯定亞氏是否要教化萬民;他的目標,似乎是那創制律法的人,要他們懂得怎樣做個有啟迪的立法者。可他為什麼要那樣做?在全書最後一段中,亞氏表明他要探討政治,因為那可以把人世間的實際智慧推向完美。我們暫時只能說,他沉思世事,為要追求智者的福樂;但如果我們不能洞明世事的實質層面與哲學層面,我們也不可能闡明,何以玄思的生命是美好的。那份證明,亞氏說,唯有政治哲學家才能冀盼。
所以《倫理學》的「下集」,就是他的《政治學》。
新書簡介
書名:《福樂的追求:解讀《倫理學》》
作者:鄧文正
出版社:花千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年4月1日
解讀《倫理學》二之一
本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