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創新焦慮,從政府、商界到民間,近年都大張旗鼓講創新。香港應該怎樣創新?創新究竟又是什麼?
來自美國史丹福大學、專攻社會創新研究的Johanna Mair教授和Christian Seelos博士對此表示,近年全球瘋狂迷戀創新,但卻不甚理解創新是什麼,創新究竟為了什麼,又怎樣有效實踐。2018年12月10日下午,這兩位學者應社創基金邀請,來到香港理工大學舉辦講座,分享研究心得,吸引眾多業界人士和學者前來觀摩切磋,兩個多小時的講座中,兩位學者不停強調:如果還沒準備好還沒想清楚,請別再隨便說創新!
Mair教授和Seelos博士多年來致力研究社會及非牟利領域的創新,為社會創新問診把脈。他們認為,要帶來真正有影響力的社會創新困難重重,沒有一項「魔法方程式」,不過透過長期研究不同機構,他們總結出一套「創新病理學(Innovation Pathology)」,去解答「社會創新為何失敗」這一核心問題。2017年,他們聯手出版新書Innovation and Scaling for Impact,嘗試為在前線努力的社創人帶來啟發和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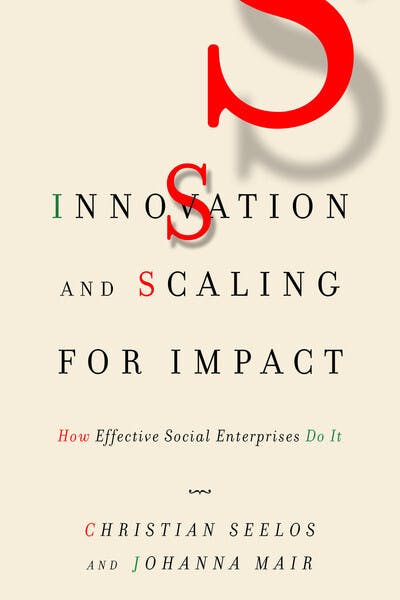
創新不會很快帶來奇跡的結果
Mair教授和Seelos博士發現,近年「創新」一詞愈發泛濫,各行各業都說自己在「創新」,但細看,很多時不過是產品升級或常規的企業發展。
兩位學者強調,他們眼中的真正創新,不單單等於一項產品或技術創新,而是人們對於真正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所提出的新方案,創新是一個不斷學習解決問題的過程。
過往多年,兩位學者在全球不同的發展中地區跟蹤研究十多個致力於解決當地社會問題的機構,對於個別機構的研究更長達15年。他們發現,這些機構大多沒有自我標榜自己在做社會創新或社會企業,但創辦機構的人,都是一些真正重視社會問題,希望去用新方法解決社會問題的人。
眾多研究個案中,擁有42年歷史的印度眼科醫院Aravind令兩位學者印象深刻。創立Aravind那一年,眼科醫生Govindappa Venkataswamy博士已經58歲,眼看印度農村地區年長人士深受白內障困擾,已經退休的他想參考麥當勞模式,在印度建立標準一致的眼科醫院,為此還說服同為眼科博士的姐姐和姐夫,變賣資產,為貧窮人士提供免費或收費低廉的眼科服務。
「做社會創新,永遠不要怕老!」Seelos博士笑着說,但儘管出身於一個醫科家族,又有一個好構思,Aravind在隨後數十年的發展仍然經歷重重困難,全靠一次又一次地創新,用驚人的毅力去突破困境。例如在八十年代,Aravind發現晶片的捐獻大幅下降,但如果自行採購晶片,又費用高昂,現存的社會資源已經無辦法提供更好的解決方案。最終,Aravind管理層決定大舉創新,投入未知領域,創辦Aurolab公司,自己生產晶片,這一決定令機構的影響力更進一步,今天,Aravind生產的眼科設備已經出口至全球130個國家。
「要將創新規模化、擴大長遠的影響力,不能靠運氣,而是需要堅持和投入。」兩位學者表示,「不要期待創新可以很快就帶來奇跡的結果。」

創新之前,要找到共同利益點
某程度,創新其實有違人性的一些特徵,因此格外困難。
「人們的天性總是不喜歡改變,喜歡維持原狀。」Mair教授說,因此創新的力量常常要面對各種阻力。
同樣在印度,創立於2007年的組織JEEVIKA致力於改變印度農村的不平等現象,為印度貧窮女性進行充權。「不過你直接走入一條村,說我要改變這裏的不平等,肯定不可以,會引發強烈反對,後來JEEVIKA想到一個方法,就是尋找人們共同關注的利益。」Mair教授說,在印度農村,乾淨的水源是人們強烈的需求,因此JEEVIKA決定協助人們建造水利基礎工程。
在一起做工程的過程中,JEEVIKA鼓勵男女村民、不同階層的人一起進入參與討論和決定,透過這些手法,花上數年時間慢慢改善農村生態。
Seelos博士強調,這個過程JEEVIKA至少做了數年,不要幻想社會創新可以在半年或一年帶來成果和影響。

香港要找準本身節奏
社會創新的過程耗時亦充滿困難,資金的長遠支持則尤其關鍵。
近年,許多政府和民間都開始大力資助或投資社會創新項目,Mair教授和Seelos博士也留意到,香港政府對創新的支持力度非常顯著。2013年,香港扶貧委員會就創立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社創基金),截至2018年10月透過協創機構推行的計劃資助134個創新項目。
兩位學者表示,許多社會創新項目都會經歷失敗的階段,一方面要留意失敗對相關弱勢社群的影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家要總結和反思為何失敗,從而總結經驗和模式。
「不要急着半年就看KPI,這不太有幫助,更重要的是服務的質量和影響力,還有我們從中學到了什麼,怎樣做得更好。」Mair教授和Seelos博士提醒,在很多地方,很多時候,由於資助者和受助機構訂立了很多不同的KPI,致使機構無法達到標準,資金可能很快就撤走,機構就會陷入財政緊張。
Mair教授鼓勵受助機構和資助者從多對話溝通,訂立更有效的指標,不過她亦明白,這並不容易。她期望學術研究可以有助受助機構和資助者更深入認識創新的過程。
他們亦強調,在鼓勵民間創新的同時,各地政府亦要嘗試自我創新、革新官方機構運作,「如果你不這樣做,單單只是向外推動創新,但自身的變革卻很緩慢,那只會製造愈來愈多的衝突。」
談及香港整體創新發展的未來,兩位學者都鼓勵,香港要找準自己的節奏,有效地回應自己的社會問題。
關於Johanna Mair 教授
Johanna Mair 教授是Hertie School of Governance的教授,她的研究重點是創新的組織和制度安排如何創造經濟和推動社會發展。她同時亦是美國史丹福大學慈善與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的傑出學人、該中心轄下的Global Innovation for Impact Lab)的聯合主任,以及史丹福社會創新評論(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的學術編輯。2016年至2018年,她協助建立哈佛甘迺迪學院社會創新+變革計劃(Social Innovation + Change Initiative)並出任其學術聯合主任。她曾在哈佛商學院任訪問學者,並定期在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和INSEAD歐洲工商管理學院任教。自INSEAD(法國)獲得管理學博士學位之前,她曾直接參與國際銀行業的行政決策工作。
除學術研究外,Johanna Mair教授亦為跨國公司、聯合國、政府部門、基金會和社會企業提供顧問服務。她於2008年被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評為社會企業家教育的「學院先鋒」。
關於Christian Seelos 博士
Christian Seelos博士是史丹福慈善與公民社會研究中心轄下的Global Innovation for Impact Lab的聯合主任、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經濟與商業學系講師、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人。他重點研究組織策略與全球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係,包括社會創新、扶貧的新商業模式、氣候變化和水資源壓力等。
Christian Seelos博士曾獲策略管理協會(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Best Paper Award for Practice Implications,肯定他近年對新興市場創新企業策略的研究。同時,他亦曾奪得IFC-FT私營市場發展論文比賽的金獎。他早年曾擔任聯合國伊拉克特別委員會主席的高級顧問,領導伊拉克生化武器的核查和裁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