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從1978年到2018年,中國各方面都發生了巨變,令人眼花繚亂。如何度量和評價所發生的變化,是一個可討論的問題。在一些人看來是積極的變化,但在另一些人看來則是消極的;在一些人看來是正面的變化,但在另一些人看來則是負面的;在一些人看來是進步的變化,在另一些人看來是退步的。這並不難理解,對所有這些變化,每個人、每一個社會群體心目中的答案都是不同的,每個人、每一個社會群體大凡都會根據自身的生活經驗來做判斷。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矛盾的局面呢?這裏頭的因素很複雜,有三個方面的因素是可以加以考慮的。第一,人們的主觀目標、道德因素、價值觀認同等不同,導致評價的不同,即平常所說的「人心坐標」。這些個體層面的因素很複雜,影響着人們對變化的評價。第二,客觀世界尤其是物質世界的發展,往往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或者說是客觀規律,人們可以稱之為「物質坐標」。在這個層面,很多發展即使人們不喜歡,甚至反對,也很難不發生。
例如,儘管經濟發展必然對環境造成影響,也會導致社會貧富差異擴大,但除了絕少數能夠不去追求,多數人還是會去追求的。人們如果認同這個客觀規律,評價會傾向於肯定;如果人們不能認同這個客觀規律,評價就會傾向於否定。第三,更重要的是,在人心坐標和物質坐標之間還有一個「制度坐標」。這是為了調節人心坐標和物質坐標。沒有制度,人難以和物質世界共存。因此,不管什麼社會,人們把制度看得很重。

從學術上看,制度坐標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個層面的問題是應然的,即中國的制度應當通過怎樣的變化而成為怎樣的制度?第二個層面的問題是實然的,即中國的制度實際上在發生怎樣的變化、會變成什麼樣的制度?
用第一種方式回答問題的,可以稱之為理想主義者,而用第二種方法回答問題的,可以稱之為現實主義者。但實際變化的結果往往是既不像理想主義者那樣理想,也不像現實主義者那樣現實,而是兩者的混合。理想主義者對改變現實有影響,主觀意圖對改變客觀環境的影響不可忽視,否則很難解釋歷史的進步。同時,理想主義又受制於現實環境,使得理想不會像原先所設想的那樣實現。這樣的結果肯定不是皆大歡喜,既不符合理想主義,也不符合現實主義。中國過去40年的改革歷程就是如此。
改革開放創混合經濟
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剛剛開始不久,中國的理想主義者設定了兩個改革開放的目標,即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簡單地說,當時的理想主義者的參照系就是發達西方國家,即市場經濟加民主政治。40年過去了,中國既沒有維持現狀,也沒有變成西方。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中國成了混合體制。在經濟上,官方也將此定義為混合經濟,或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政治上,也是一種混合體制,既非西方所說的專制,也非西方所說的民主。
就經濟制度來說,正在形成中的混合經濟,不僅僅是多種所有制的混合體,更是傳統與現代的混合體。西方把中國看成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國家資本只是這種混合經濟體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甚至是不那麼重要的一部分。中國從漢朝到今天幾千年,可以說是「吾道一以貫之」,一直存在着這樣一個混合經濟體。人們叫它為資本主義也好,或者叫它市場也好,至少有三個層面的市場,或者有三層資本。頂層的永遠是國家資本,底層的是自由民間資本,還有中間層面,就是國家和民間互動的部分。
從漢朝開始就是這樣,有些領域國家一定要壟斷,佔主導地位,但大量的空間要放給民間;中間的經濟空間,像鹽、鐵那樣的產業,對國家很重要,但即使對國家很重要的空間,也可以叫私人去做。到了近代,就產生官辦、官督商辦、商辦等經濟形態。由此可見,混合經濟體其實是中國非常古老的一個經濟實踐,並不是現代的創造。

在中國那麼長的歷史中,只有四個時期走了極端,變成經濟國家主義化,國家完全佔了主導地位,市場幾乎被管控甚至消滅,包括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朱元璋時期、當代的毛澤東時期。在這四個時期,國家跟市場完全失衡。除了這四個時期,中國的國家和市場基本上都是相對平衡的。從歷史經驗看,中國今後還會是這三種資本、三層市場,往前發展。這種制度有它的劣勢,與西方市場經濟比較,效率差一點,相比西方制度的優勢是其能夠預防大的經濟危機。
西方資本主義,正如馬克思所分析的,會爆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比如1930年代的大蕭條、1997/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機等。中國過去40年基本上沒有經濟危機,這跟政府的調控能力有關係,跟這個制度機制有關係。
中國政經俱行混合制
近代以來,西方經濟主要有兩個調整手段,一個是貨幣政策,另一個是財政政策。可是當利率趨於零的時候,貨幣政策就很難能發生作用。現在西方頻繁搞量化寬鬆(QE),但這並非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就西方的財政政策而言,當政府的財政赤字過大以後,財政政策就不管用了。中國除了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外,還有國有企業這個經濟部門可以調節。隨着全球化的持續,未來經濟會愈來愈波動。可以預見,中國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棄國有部門。不過,這三層資本之間,邊界在哪裏,每一個時代都在調整,每一個時代都在變化,以取得政府跟市場之間的平衡。
政治制度也是一種混合制度,這個制度的特點是:開放的一黨制、以黨領政、內部三權分工合作。一說政治制度,很多人心目中的標桿就是西方的三權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之間的互相制衡,但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制度也有「內部三權的分工合作」──決策、執行、監察。這個制度在漢朝建立,一直到晚清都沒有變化。
人們不能說這個制度沒有生命力。當人們說中國文明幾千年不中斷時,就必須思考,哪些東西沒有中斷?王朝是中斷的,皇帝來來去去,甚至中國的人種都有變化,中國的「漢」不是一個種族概念,而是一個文化概念。那中國哪些東西沒有變化呢?就是這裏所說的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從來沒有變化,只發生了一些小的變動。
1980年代中國開始政治體制改革,當時還有點想往西方的方向發展,提倡黨政分開。這也正常,因為近代以來很多人都希望往這個方向發展。孫中山搞了一個五權憲法,即在西方三權基礎之上,加上中國傳統的考試權和監察權。不過,孫中山基本上是個理論家,沒有機會實踐。從台灣的實踐看,中西方兩個體制背後有不同的邏輯,要麼西方的三權為主,要麼中國的三權為主,兩個體制加起來很難有效運作。台灣現在基本上是西方的三權機制,考試權基本上已經無用了,監察院還在,但基本上不起什麼作用。
政治重走黨政分工
今天的中國再次走上內部三權分工合作的道路。1980年代提倡黨政分開,現在則提倡黨政分工。黨政分開的道路走到1980年代後期已經走不下去。黨政分開,黨的主管和政府的主管兩個人之間如果有矛盾,就變成了黨政兩個機構之間的矛盾,會產生黨和政府的分裂。因此,1992年中共十四大開啟了三合一制度,即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由一個人擔任。這一制度其實是對黨政分開的直接否定。江澤民和胡錦濤時期都是這個思路。
西方建立在多黨制基礎之上的政治制度,可以稱為外部多元主義。在西方歷史發展過程中,先有市民社會後有國家,存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一個國家可以有幾個政治過程,最終的制度表述是多黨制和三權分立。但中國不是。中國幾千年來就是皇權,秦始皇以後一直是先有國家後有社會。因為皇帝只能有一個,所以只能有一個政治過程。但怎麼做才能讓統治比較有效呢?那就是把一個政治過程分成三段,第一段是決策,第二段是執行,第三段是監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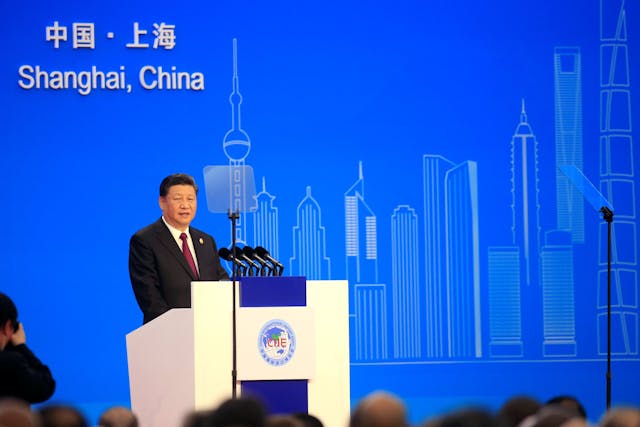
現在的三權分工合作體制有點類似傳統體制。必須解釋的就是傳統皇權怎麼演變成為現在的黨權?怎麼看這個黨?中國共產黨其實不是西方理解意義上的政黨。從結構上說,黨權就是組織化的皇權。以前的皇帝是個人,是家庭,現在的黨是一個組織。在這個轉型中,西方有些概念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比如民族主義主權和列寧主義的政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制度層面正是表現在這個地方。
一個基於個體家庭之上的皇權,已經轉成基於一個組織之上的黨權。以前的皇權分成三個階段,現在的黨權也分成三個階段──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但人們不能說這是簡單地對傳統的回歸,因為現在黨是個集體,而以前皇帝是個人家庭。這個制度一旦確立,不能低估其生命力。不過,中共十九大儘管正式確立了內部三權體制,但這個體制的有效運作還需要進一步的改革。比如決策權,以前主要掌握在皇帝和他的大臣、皇兄皇弟少數人手裏,現在則不一樣了。
執政黨中央委員會、全國人大、政協、重要的社會團體(共青婦)、各類智庫等,都可以成為決策權的一部分。現在的問題就是,決策權怎麼更民主化一點呢?以前不需要民主,但現在有了民主的觀念,民主就必須體現在制度層面。監察權對反腐敗很重要,但監察權也不能濫用。漢朝規定,不可以事無巨細地什麼都監察,規定只有六個領域可以監察,否則執行權就沒有辦法行使了。現階段的監察權就面臨這個問題。
這種制度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是矛盾的,但是和民主本身並不矛盾。不難觀察到,中國的內部三權分工合作制度可以吸納西方很多民主的要素,但不會成為西方的制度。
從歷史經驗看,人心坐標和物質坐標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但制度坐標的變化似乎更為恆定。不難理解,制度與人心和物質之間永遠存在着張力和矛盾,人們對制度的評價和認同永遠不會完全一致。不過,正是這些張力和矛盾,構成了制度進步的動力。對執政者來說,所需要的就是維持制度與其他兩者之間的平衡。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