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負如來不負卿」,據說是來自一位西藏詩人七言詩其中一句。喜歡詩的意境,詩人真不簡單,他所做的一切,既不違反佛法,亦不曾讓所愛的女子難堪。做人,能做到面面俱到,得有點智慧才成。
陳煒舜教授對古典文學素有研究,便向他請教詩句出處。
不負……
陳教授告之:那是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1683年至1706年?)的作品。這句詩是否由翻譯者添加上去的,有待考證。
煒舜傳送來一篇對話,是與另一位學者黃鈺螢談「不負如來不負卿:倉央嘉措詩歌與民國文學增域」。
一直以來,對學者探討問題的文章,有點抗拒,是怕理論過多,普通讀者,不一定明白他們在講什麼。但這篇對話,深入淺出,一點也不枯燥乏味,兩人不用拋書包,已可說出重點來,偶爾幾句幽默語調,竟擦出火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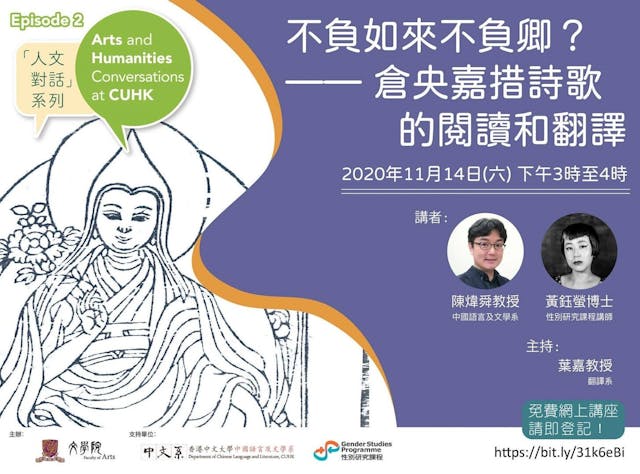
原來藏文「倉央」翻譯成漢語,是「妙音」的意思,「嘉措」是「海洋」。「倉央嘉措」是「妙音海」,讓人充滿聯想的名字。
藏詩,該是五絕,而不是七絕。像這一首:「最好不相見/免我常相戀/最好不相知/免我常相思」,倉央寫詩的時候,還是個青春洋溢的少年(青年),他為人浪漫,是個「情僧」來的。又敢反抗舊有思想框框,100年前,五四運動時期,他的詩作,很受年輕人歡迎。
這位活存在清康熙年間的西藏詩人,雖說是達賴喇嘛,卻愛過不受束縛的日子。不過,他也明白:「世間安得雙全法,不負如來不負卿」。
最後一句不錯有着倉央的想法,但可能給改寫成佳句了。

漢藏文化
陳煒舜喜歡倉央嘉措的詩作,得從他中學時期說起:「中學時代在香港觀賞過倉央的舞劇,知道了他的情詩。其後又看過不同的翻譯版本,讀到于道泉和曾緘七絕譯本,覺得大不相同,加上自己平時也創作舊詩,因此想通過比對翻譯,來進一步探求舊詩寫作手法。」
煒舜對藏傳佛教也頗有興趣,走進倉央嘉措的世界,樂而忘返。經過多年努力與堅持,寫下《漢藏之間:倉央嘉措舊體譯述研究》,並找來張曼儀教授寫序。
張教授的序言,講出翻譯之道:詩歌,用非文學的直譯,不會好看。于道泉的翻譯,一味求真,失卻詩的韻味。「文學翻譯,是一個創造的過程。讓譯品在另一個文化,另一種語言裏投生。」
道出翻譯這門藝術,不好掌握。
像這一首詩:「從東邊的山尖上,白亮月兒出來了,未生娘的臉兒,在心中漸漸地顯現。」改成五言絕句,效果會不會更好?
至於「未生娘」,有譯者改之為「少女」,錯了。其實,藏語「未生娘」不是指少女,黃鈺瑩的解釋:那是指「情人對自己的恩情,像母親一樣,彼此之間的愛與連結,與母子近似」。
而這,正好反映出藏漢文化的差異。
七言變成五言,可行麼?
陳煒舜指出絕句,一般以文言為基礎,文字簡潔。承載着倉央詩句,用五言,古樸風格,20字,剛好足夠。
拉薩民歌,反映出藏人對倉央的包容:「別怪他風流浪蕩,他所追尋的,和我們的沒有兩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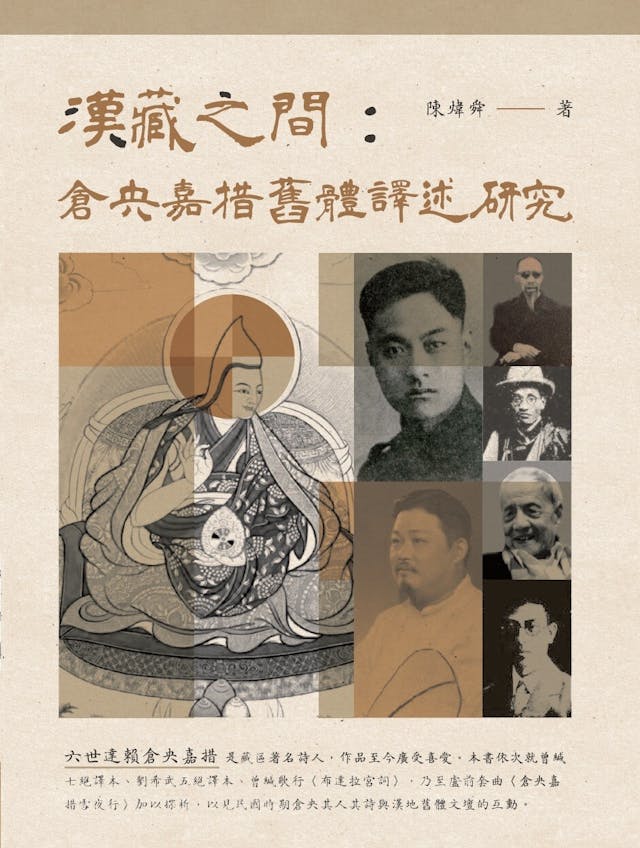
講詩·寫書
陳煒舜愛書寫不同類型的文章,我們想不到的題目、不好找的題材,對他來說,不是問題。這位學者拿起筆來,就像魔術師揮動魔術棒,從帽子裏拿出來的,不是兔子,不是鴿子,而是教人驚喜的故事、有說服力的文章。
當我膽粗粗的去寫「不負如來不負卿」,以為憑空想像,總可以寫出點什麼來。倘若沒有煒舜提供資料、沒有看他與另一位學者的對話,我什麼都寫不了。
下筆前,煒舜做足功課,不會人云亦云。寫倉央嘉措,寫出藏文化的特色,翻譯藏文的難處,微妙之處在哪。每篇文章,流露出他的識見。
煒舜傳來幾篇近作,包括對《宣統皇帝溥儀的詩作》,這位末代皇帝的舊詩,「寫得實在一般」,「溥儀把清朝歷代皇帝的文化平均值拉低」了。
溥儀幼年「失學」,「沒人有資格督促他」。這小皇帝又「處於少年叛逆期」,清朝氣數已盡,更沒人理他了。
女畫家周鍊霞(1908年至2000年)一生際遇,教人慨歎不已。日軍佔領上海期間,燈火管制。畫家寫出「但使兩心相照,無燈無月何妨」。白光唱的《無燈無月夜》,歌詞是「無燈無月何妨」的變奏。因這句話,在文革時,周鍊霞遭受迫害(另一原因,丈夫在台灣工作),「一目被毆打近失明」,她找來金石家來楚生刻了個「一目了然」印章。
煒舜與方穎聰合寫《女仔館》(Female Diocesan School)。
女仔館只營運了僅僅九年(1860年至1869年),「但這所學校,對香港中英雙語教育和女子後來的發展,卻有着深遠的影響。」「這女仔館與拔萃男書院、拔萃女書院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細說從前,煒舜與穎聰,寫出兩書院的前世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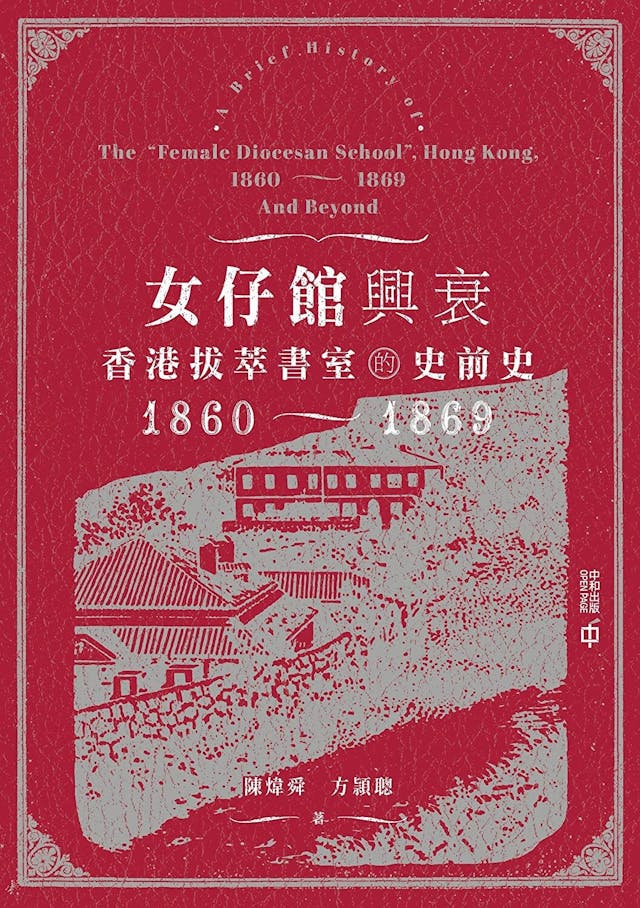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綜合轉載,題為編輯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