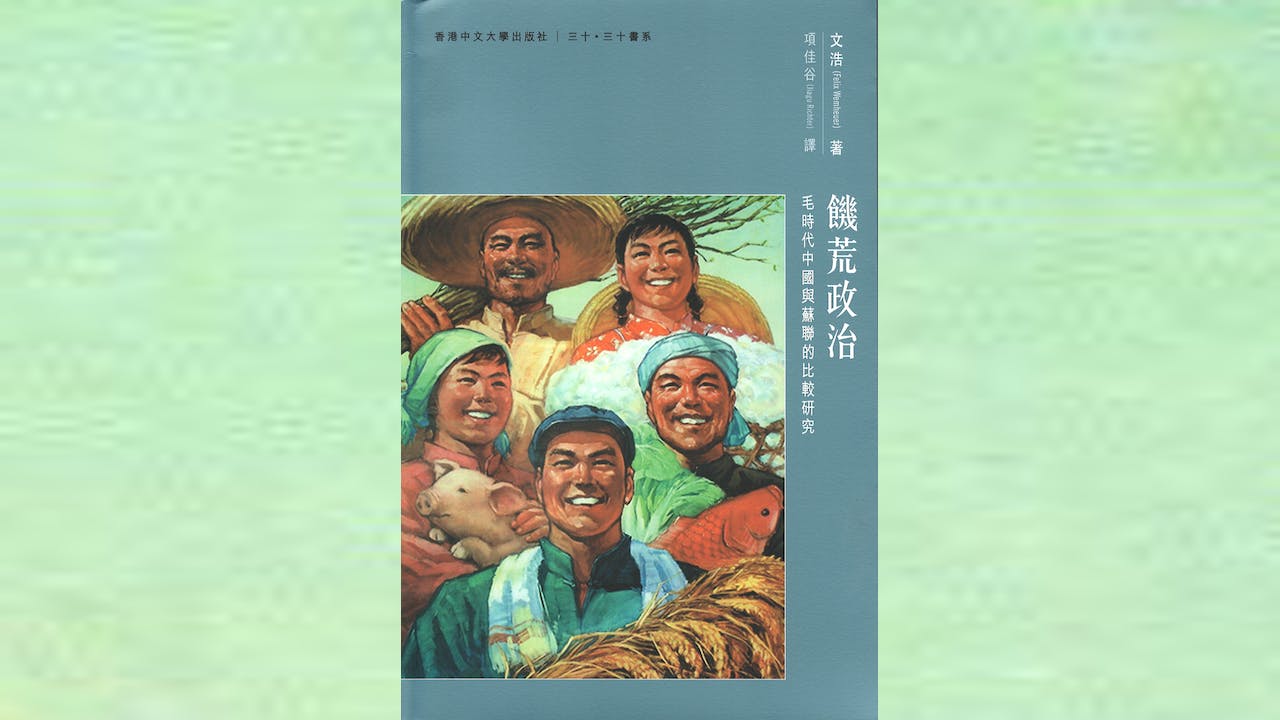20世紀死於饑荒的人數多於歷史上任何一個世紀。(註1)聽到「饑荒」這個詞,我們的腦海裏常常出現非洲嬰兒餓得奄奄一息的畫面。但是更符合歷史事實的是,如果聽到這個詞,我們也應該想到蘇聯和中國餓死的農民。因為,如斯蒂芬.戴維洛斯(Stephen Devereux)所估計,20世紀死於饑荒的7,010萬到8,040萬人中80%是這兩個國家的公民。(註2)這個數字還不包括以全球平均水平認定的食物匱乏和饑餓造成的死亡,而僅僅是根據與「正常」年份的人口發展平均數相比,由於饑荒而造成的過高的死亡率。這兩個國家在革命政權統治下,發生了多次恐怖的饑荒,比革命前的自然災害造成了更多人的死亡:俄國1919至1921年內戰期間和之後城市發生的饑荒,以及1921至1922年農村的饑荒;蘇聯1931至1933年集體化之後的饑荒;1941年德軍入侵之後的饑荒,當時納粹以饑餓作為種族滅絕政策的一部分;戰後1947年在蘇聯發生的饑荒;中國大躍進期間(1958–1961)發生的饑荒造成了千百萬人的死亡。很明顯,大躍進導致的饑荒不是中國特有的,應該將其放在農業帝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大的背景下來分析。在這本書裏,我重點對蘇聯1931至1933年的饑荒與中國大躍進期間的饑荒進行比較,因為它們具有相似性。
社會主義下的饑荒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饑荒與當今非洲國家發生的地方性饑荒很不一樣。大規模餓死人的時間相對較短,同時具有高死亡率和出生率降低的特點。(註3)在21世紀初的當今,在人們稱之為「第三世界」的國家,大多數人不是死於嚴重的饑荒,沒有很高的死亡率,而是死於「常態」的生活條件,如地區性的饑荒或疾病。根據聯合國的統計,2007年全世界有9.23億人食物缺乏。(註4)每年大約有3,600萬人直接或間接死於饑餓。(註5)其中很多是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和兒童。在過去20年中,死亡率很高的饑荒僅僅發生在非洲內戰國家,如索馬里和蘇丹。(註6)
人們一般覺得,饑餓和饑荒常常與落後連在一起,大自然的變化無常影響了農業生產,水災、旱災和蟲害毀掉了莊稼。中國農民「靠天吃飯」的說法就是一個很好的寫照。實際上,古代也有過嚴重的饑荒,但17世紀到20世紀間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迅速上升。(註7)據威廉.丹多(William Dando)估計,17世紀至少有200萬人死於饑荒,18世紀為1,000萬,19世紀的數字是2,500萬。(註8)這些可能是過於低估的數字。戴維洛斯的估計是20世紀7,010萬到8,040萬人死於饑荒,這個數字表明,嚴重的饑荒不僅僅是古代的災難,也會發生在現代。而且,戴維洛斯的數字還不包括二戰期間因納粹的種族滅絕政策而死亡的幾百萬蘇聯人。(註9)他對中華民國期間(1911–1949)饑荒死亡人數的估計也比較低,僅1,350萬至1,650萬。
在現代,嚴重的饑荒發生於殖民統治時期、中國的國民政府時期、農業國家社會主義時期、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和非洲的後殖民時期。在非洲的後殖民時期,饑荒常常與戰爭或內戰交織在一起。英國的殖民主義採用放任式自由主義,並且以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為指導。(註10)18世紀後期英國學者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提出,生產的增長趕不上人口的增長,用他的話說就是會產生「人口過剩」。同時還存在貧困人口的生存保障問題,這更加重了人口問題的嚴重性。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下(1837–1901),1846至1850年愛爾蘭饑荒期間110萬至150萬人餓死,(註11)1879至1902年期間1,200萬至2,900萬印度人死於饑荒。(註12)
在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在東歐佔領區用饑餓作為武器,為了保證國內戰場和軍隊的糧食供應,納粹以饑餓對當地居民執行殘酷的種族滅絕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的圍困和糧食短缺,造成了海軍士兵和工人反政府的起義和革命,對此,納粹記憶猶新。(註13)為了保證向德國的糧食供應,德國政府不惜餓死東歐被佔國家和俘虜營中幾百萬「無用的食客」。(註14)當盟軍1945年解放集中營時,被關押的人個個掙扎在死亡的邊緣,看上去像是一個個活骷髏。這是德國20世紀在歐洲大地上製造的恐怖景觀。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說過,那種餓得快要斷氣的「皮包骨」,看上去像是生與死之間的幽靈,他們是集中營的一種主要產品。(註15)在德國的佔領下,1944年荷蘭和希臘也發生了嚴重的饑荒。(註16)
饑荒和饑餓的定義
在談蘇聯和中國的情況之前,我想先談談饑荒和饑餓的定義。關於饑荒的定義,學界已有長時間的討論,最大的挑戰是區別饑荒和也可以造成幾百萬人死亡的日常的食物匱乏。(註17)如果一個政府宣佈出現饑荒,一般要組織救災,而日常的食物匱乏則容易被忽略。亞瑪特亞.森(Amartya Sen)提出,印度1947年獨立後沒有出現過嚴重的饑荒,但是印度每年死亡人數比中國多390萬,我們可以看出,對這兩個國家使用了不同的死亡率來計算。(註18)「這就是說,按每8年左右的時限來計算,印度正常的死亡人數就會多於中國1958至1961年嚴重饑荒年間的死亡數」,這是基於讓.德勒茲(Jean Dreze)和森(Sen)1989年提出的大躍進饑荒造成2,950萬人死亡的數字所做的比較,「印度8年掩埋的屍骨多於中國那段恥辱的日子裏所創下的紀錄」。(註19)
有些經濟學家認為,用糧食價格指數也可得出另一個饑荒的定義。在社會主義國家,影響生存的主要因素不是糧食的市場價格或者農村的信貸體系,而這兩者在孟加拉1943年饑荒時則是主要的因素。在計劃經濟中,糧食的分配和統購統銷發揮着關鍵的作用。由於國家對食物分配進行壟斷,偷竊成了許多農民生存所必須的手段。經濟/人口學家科馬克.歐.格拉達所定義的饑荒就包括對社會正常生活的破壞:「傳統意義上的饑荒指的是,它並非某一地區特有的現象,通常具有日常生活中所沒有的特徵,包括物價上漲、哄搶糧食、搶劫財物的犯罪增加、餓死或行將餓死的人很多、人口流動增加,同時還常常還伴有人心惶惶和爆發饑荒引起的傳染病。」(註20)
下面我們來看看,在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饑荒中有沒有這樣的現象。亞歷山大.得瓦爾(Alexander De Waal)指出,經歷了饑荒的民眾對饑荒的定義常常與專家或政府機構的定義不同。在非洲各地,「饑荒」與「饑餓」兩個詞的含義通常是一樣的。(註21)在俄文裏也是一樣的(Golod)。只是過去的20年裏,在烏克蘭人關於烏克蘭1931至1933年饑荒的討論中才出現了饑荒這個新詞(烏克蘭語為Holodomor,俄語為Golodomor)。但中文中「饑餓」和「饑荒」這兩個詞是不同的。自然災害為「天災」或「災難」,可能會造成「荒」或「災荒」,但「荒」或「災荒」不一定會導致饑荒或餓死人。(註22)不過,在實際運用中有一個如何解釋這個詞的問題。得瓦爾認為,在非洲,農民常常對饑荒和一般的食物匱乏不加區別。
饑荒不等於缺乏食物
在社會主義國家,饑荒和一般的食物缺乏比較容易區別。幾個最嚴重的饑荒,如蘇聯1919至1921、1931至1933和1947年的饑荒,以及中國1959至1961年饑荒都在短時間內造成了大量的死亡,社會主義國家的饑荒具有大量餓死人的特徵。從人口統計方面,我們可以對饑荒的開始、高峰以及結束都有清楚的數據,即使對總死亡人數有爭議。而饑餓和食物缺乏的時限則比饑荒難定義得多,因為對「饑餓」的理解有文化和主觀的因素。如今,人們認為,甚麼是食物,一個人需要多少食物才能生存取決於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環境,大多數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都認為這是很自然的事。
特奧多爾.亞多諾(Theodor Adorno)在關於需求的短文中提出,「食物」是一個帶政治和社會含義的概念。(註23)不過,國際組織認為他們可以制定一個全世界都適用的標準。根據聯合國糧食計劃署的定義,一個人一天所需的最低能量為2,100卡路里。(註24)「最低能量需求」意為,可以讓人從事輕微體力勞動,不會體重減輕或病倒。這個標準與英國醫學協會1930年代制定的標準相比是相當低的,後者為每人每天3,400卡路里加50克蛋白質,當時很多人在工廠從事重體力勞動。(註25)20世紀初的營養學家認為,人像機器需要燃料一樣,需要足夠的卡路里攝入。但是,多少食物是足夠的,取決於氣候條件、季節和工作性質。住宿地十分寒冷或者冬季在室外,同時從事重體力勞動比坐在溫暖的辦公室裏的白領需要多得多的能量攝入。
傳統和文化習慣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沙俄政府給農民在常規條件下制定的標準為每人一年平均295公斤穀物(大約一天808克)。這個標準相當於一天2,500卡路里。19世紀後期,沙俄中央統計委員會為饑荒期間制定了220公斤穀物的標準(大約一天1,700卡路里,602克),作為避免人體狀況嚴重惡化的最低攝入量。但1891年的饑荒時,內政部將一年150公斤(一天大約410克)作為貧困農戶不被餓死的人均最低標準。(註26)
營養歷史學專家在與蘇聯歷史專家就此問題進行的辯論中說,俄國1919年饑荒期間,俄國城市裏工人家庭每人每天卡路里攝入量在1,550至2,050之間,這並不比19世紀英國工人的攝入量低很多。(註27)但是,如斯蒂芬.維特克羅夫特所說,卡路里的絕對攝入量不應該被看作是判定饑餓的唯一標準,攝入量從通常的水平降低了多少也應予以考慮。對俄國農村地區來說,這場饑荒期間卡路里攝入量降低了55%。(註28)
與二戰期間的德國和蘇聯的供給制不同,中國政府用「斤」(相當於500克),而不是卡路里作為供給分配的計算基礎。(註29)問題是,如果城市每人可以分到700克細糧,但是不知道這些糧食能提供多少卡路里,因為質量好的新糧和陳糧會有很大的區別。一般認為,中國1950年代90至95%的熱量攝入主要靠糧食。(註30)30中國國家領導人如陳雲建議將500克細糧作為一個農民在「正常年間」的日消費量。(註31)這個數量的糧食如果是小麥可以提供1,700卡路里,如果是大米可以提供1,830卡路里。(註32)這個量與沙俄統計委員會為饑荒時期提出的最低標準相同。
一些西方學者試圖根據中國官方的數據對中國民眾卡路里的攝入進行評估。喀納斯.沃克爾(Kenneth Walker)發現,在1950年代的中國,在北部和西部省份的很多地區,農民的卡路里攝入量較低(1,800–1,900),如果按日平均則更低(1,800以下),只有東北的滿洲攝入量較高(2,500)。(註33)即使在饑荒還沒開始之前,中國很多農民卡路里攝入量也比國際機構如今所確定的最低標準要低,比俄國工人在內戰期間的饑荒中吃得要少。大躍進的前一年,1957年,全國糧食的供給和需求量十分接近。瓦克拉夫.斯密爾(Vaclav Smil)認為日平均卡路里為2,100至2,200,可是在農村,從事無機械化的中等及重體力勞動的人一天大概需要2,100卡路里。因此,只有「完全公平的分配才可以避免大規模的食品匱乏。」(註34)在大躍進的幾年中,人均日卡路里可獲量逐年下降,1958年為2,071.9,1959年為1,736.81,1960年則降為1,462.32。(註35)一個問題是,統計中沒有顯示年齡、性別、體重和體力活動要求。(註36)
在進行熱量需求統計的比較時,我們應該考慮到社會和文化上的區別。東北重工業企業的工人對饑餓的定義,可能與北部省份窮鄉僻壤的農民有很大的不同。在不同的文化中,饑荒的定義也不相同。區別每天發生的、通常的食物匱乏和饑荒最重要的標識,是人口統計中是否有大量的死亡人口。
註釋
1. Stephen Devereux, “Fam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DS Working Paper 105(2000), 7. Http://www.dse.unifi.it/sviluppo/doc/WP105.pdf; accessed May 10 2010.
2. 同上,頁9。
3. 關於中國死亡率的概況,見 Yang Dali,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8. 關於蘇聯1931至1933年死亡率的情況,見 Stephen G. Wheat croft, “Soviet Statistics of Nutrition and Mortality duringTimes of Famine, 1917–1922 and 1931–1933,”Cahiers du Monde Russe 38, no.4 (1997): 526–527. 對於蘇聯內戰期間的人口情況未找到可靠的統計。關於1947年饑荒見 Nicholas Ganson, The Soviet Famine of 1946/47 in Global and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xv.
4.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Department, “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08: High Food Prices and Food Security—Threats and Opportunitie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2008), 2. ftp://ftp.fao.org/docrep/fao/011/i0291e/i0291e00.pdf; accessed January 10, 2011.
5. Jean Ziegler, “The Right to Food: Report by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Food, Mr. Jean Ziegler, Submitted in Accordance with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Resolution 2000/10,” United Nations, February 7, 2001, 5. Http://graduateinstitute.ch/faculty/clapham/hrdoc/docs/foodrep2001.pdf; accessed January 10, 2011.
6. Devereux, “Fam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6.
7. Cormac Ó Gráda, Famine: A Short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25–32.
8. William A. Dando, The Geography of Famine (London: E. Arnold, 1980), xii.
9. Devereux, “Fam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6.
10. 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Verso, 2001), 32.
11. Kerby Miller, “‘Revenge for Skibbereen’: Irish Emigr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the Great Famine,” in The Great Famine and the Irish Diaspora in America, ed. Arthur Gribbe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9), 181.
12.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7.
13. Gesine Gerhard, “Food and Genocide: Nazi Agrarian Politic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of the Soviet Union,”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8, no. 1 (2009): 45.
14. 詳見 Christian Gerlach, Krieg, Ernährung, Völkermord: Deutsche Vernichtungspolitik im Zweiten Weltkrieg [War, Nutrition, Genocide: The German Policies of Annihila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Zurich: Pendo, 2001), 和Christian Streit, Keine Kameraden: Die Wehrmacht und die sowjetischen Kriegsgefangenen 1941–45 [Not Companions: The Wehrmacht and Soviet POWs, 1941–1945] (Bonn: Dietz, 1997).
15. Giorgio Agamben, Was von Auschwitz bleibt: Das Archiv und der Zeuge, Homo sacer III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Frankfurt [M]: Suhrkamp, 2003), 45.
16. Devereux, “Fami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6.
17. Stephen Devereux, Theories of Famine (New York: Harvester/Wheatsheaf, 1993), 10–14.
18. Jean Drèze and Amartya Sen,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2), 214.
19. 同上,頁215.
20. Ó Gráda, Famine, 6–7.
21. Alexander De Waal, Famine Crimes: Politics and the Disaster Relief Industry in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
22. Lillian Li,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1990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23. Theodor W. Adorno, Soziologische Schriften [Sociological Writings] (Frankfurt [M]: Suhrkamp Verlag, 2003), 392.
24. UN World Food Program, “What Is Hunger?” http://www.wfp.org/hunger/whatis; accessed January 15, 2011.
25. James Vernon, Hunger: A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07), 125.
26. R. E. F. Smith and David Christian, Bread and Salt: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Food and Drink in Rus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330–331.
27. Wheatcroft, “Soviet Statistics of Nutrition and Mortality during Times of Famine,” 530.
28. 同上,頁532.
29. 見〈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建國以來中央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卷7,頁116–118。
30. Kenneth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97.
31. 〈決定我國糧食問題的方針〉,《人民日報》1955年7月22日。
32. 我採用了Alan Piazza書中有關的轉化率,見 Alan Piazza, Trends in Food and Nutrient Availability in China, 1951–198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83), 7.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No. 607.
33. Walker, 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100–101.
34. Vaclav Smil, China’s Past, China’s Future: Energy, Food, Environmen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75.
35. Piazza, Food and Nutrient Availability in China, 1951–1981, 9.
36. Smil, China’s Past, China’s Future,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