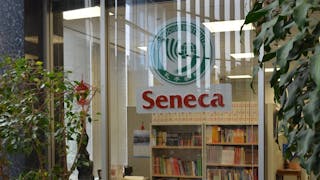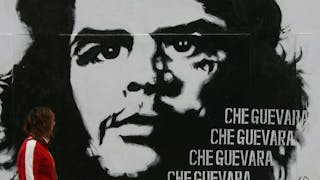近年來,亞洲地區出現的最重要的思潮變化,概括地說,表現為三大方面,包括政治化和政治激進化、宗教思潮極端化和對經濟新自由主義的反思。亞洲國家和地區過去成功的經驗,就是通過借鑒西方的經驗來塑造自己的模式。如果要繼續取得成功,仍然需要在繼續學習西方的基礎上,繼續放棄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尋求自己的發展模式。

無論從中國外交的實際行為還是話語看,從十八大到今天,中國的大外交戰略基本形成。人們已經把2014年視為是中國的「大國外交年」,但這不僅是指亞太經合組織會議、領袖外交等這類日常外交,更是指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其大外交思路和戰略等的籌劃。新的外交思路就是「兩條腿走路」的大外交:一方面是與美、歐、俄等建立新型大國關係;另一方面是面向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的新絲綢之路;連接這兩個方面外交的則是周邊外交。這個大外交戰略的核心話語就是和平與發展,在維持和平的基礎上求發展,在發展的基礎上爭取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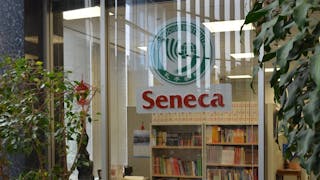
塑造國家形象不是容易的事,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這些工程不是說沒有任何效用,但一些工程經常是適得其反。中國愈推動,外界的反彈就愈大;中國的投入愈大,外界的阻力也愈大;中國的愈努力,國家形象就愈差。

亞太地區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這個地位在今後數十年不會有甚麼大的變化。世界經濟重心在那裏,一個國家的戰略也會走向那裏。在很多年里,美國愈來愈像一個亞太國家。美國實際上在希拉莉宣布重返亞洲之前,就已經開始把其戰略重心轉移到亞太地區。如果回溯歷史,不難發現,美國一直在亞太地區,從來就沒有離開過。

文明的進步都是在開放狀態下取得的。在全球化時代,誰最終能贏得國家間競爭的勝利,並不取決於誰最民族主義,而是誰最開放。今天的中國已經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制度建設,這需要更大的開放,向其他國家學習他們的制度細節,尤其是技術層面的制度細節。

經驗表明,法治政府有助於解決空轉政府和官員不作為的問題。有關部門已經提出要以法來治理官員的不作為現象。但法治和有作為政府之間並不能劃等號。在民主國家,很多政府的確是法治政府,但空轉政府大行其道。在中國,如果要在法治基礎上建立有作為政府,仍然面臨很多挑戰。

通過三中和四中全會,中國改革的頂層設計已經到位。但如果解決不了官員不作為的問題,頂層設計就會變成空中樓閣。如果改革方案實行不下去,不能為社會提供實在的改革成果,社會對改革和政府的不信任會降得更低,政府的壓力也會更大。可以說,改革方案能否實施下去,也是一場輸不起的戰爭。重在執行,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硬道理。

群眾路線必須在制度上體現黨的性質。中共是中國政治的核心,黨管政治,因此黨應當是聯繫群眾的工具,必須是群眾中間先進的部分,否則執政黨的合法性就會成為大問題。如果說民主社會,政治官員的合法性是民眾的投票「投」出來的,中國政治官員的合法性,應當是走群眾路線「走」出來的。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替代了階級鬥爭,因為社會難以承受不間斷的群眾運動,階級鬥爭產生不了執政黨所需要的政治合法性資源。不過,在經濟建設過程中,群眾路線在共產黨的政治生活中,愈來愈邊緣化了,結果造成了執政黨愈來愈官僚化。至少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組織和官員的高度等級化;第二,政黨行政化;第三,最為嚴重的結果是,執政黨與社會嚴重脫節。

民族問題不會因為民主政治的出現而消失。民主意識永遠替代不了民族意識。美國在經歷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種族問題之後,人們過分樂觀地以為種族融合了,種族問題解決了,於是出現了美國是種族「大熔爐」的民族理論。但這一次弗格森槍擊事件,再次說明了表面上的種族融合是如何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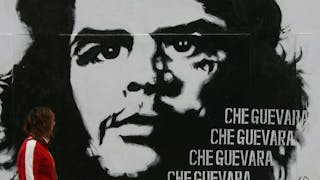
儘管革命可以捲入千千萬萬的人民,但革命總是少數人的事情。不管革命的話語多麼漂亮(如「為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等),革命總是少數精英對少數精英的事情,也就是既得利益者和希望取而代之的人之間的事情。對被動員進入、被無辜捲入的普通社會成員來說,革命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意義。相反,他們要承受大部分犧牲。儘管很多革命領導者和積極分子也會因革命的成功或者失敗而犧牲,但普通社會成員承擔了大部分的犧牲。

亞洲並沒有類似西方那樣的妥協文化。亞洲盛行的歷來就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不妥協文化。傳統上,革命很簡單,只是意味着政權更替。這種文化在現代社會是否已經轉型?從經驗來看,沒有。結果,在沒有妥協文化的情況下,民主出現「弔詭」,民主的結果往往是「反民主」。

在今天的世界,追求民主似乎已經成為一個大趨勢,但同時愈來愈多的地方因為民主化,而使得政治陷入無政府狀態。可以說,在這個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政治挑戰,便是如何重建政治秩序。今天人們似乎更多地談論政治治理問題,但如果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問題遠遠超出了治理問題。很簡單,治理問題只是國內的內部制度建設問題,而地緣政治則表明,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內部制度,必須符合這個國家和地區所處的地緣政治秩序。

亞洲正在經歷着激進政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不同的激進政治同樣具有烏托邦性質。這裏不可能對亞洲的激進政治進行全面的討論,但從香港和台灣的情況,就不難看出激進政治的烏托邦性質。

儘管激進政治花樣繁多,但對其組織者來說,本質幾乎是一致的——都是起始於組織者對現實的不滿,而去構想一個政治或者社會烏托邦,並且相信通過動員同樣抱有不滿的社會成員的政治運動方式,把烏托邦轉型成為現實。激進政治不是新生事物,有政治的地方就會有激進政治,激進政治可以說是政治生活的內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