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十八大之後的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所通過的改革決議,可以說是對中國長遠的頂層改革設計。然而,即使有了頂層設計,也不代表能順便實行政策,執行才是關鍵。政策如果不能順利執行,將導致不可預計的後果,不但不能推進改革,更可能導致改革的倒退,甚至出現顛覆性的錯誤。如何執行頂層設計的改革,正是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剛剛過去的股災,已經從不同層面,充分展示了中國的政策執行,會遇到怎樣的嚴重問題。三中全會決議推進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改革。經濟改革可以從各個方面推進,但現實上難以全面推進,需要找到有效的突破口——金融自由化就是一個突破口。今天,無論從國際層面,還是國內發展的需要來看,中國都急需推進金融自由化。 在國際層面,中國已經轉型成為資本過剩國家,在產能大量過剩的情況下,經濟力量需要走出去,人民幣需要國際化。同時,如果中國要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得到與其經濟力量相稱的地位,就要繼續登上國際金融體系的頂端(例如讓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的儲備貨幣)。以上種種都要求中國在金融自由化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 就內部發展而言,金融自由化更是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多年來,中國政府視中小企業為推動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最重要一環。很多國家都是如此。這並非政府不再重視大型企業,而是大型企業自我生存和發展的能力遠較中小企業高。重視中小企業的好處有幾個方面:首先,有利於企業創新。縱觀全球,大型企業都傾向壟斷市場,為增強競爭能力,中小企別無他法,必須積極創新。 第二,培養未來的大型企業。大型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無論怎麼努力,都必然走下坡路,被從中小企業蛻變而成的新型大企業所取代。 第三,中小企業有利於社會公平。在任何社會,中小企業的一個主要功能就是解決就業問題。就業是社會的第一次分配。如果不能解決就業問題,窮人問題難以解決。 第四,在中國,近來的眾創運動又給發展中小企業新的意義,培養新一代企業家。目前中國大部分企業家都是在1980和1990年代兩波經濟分權過程中闖出一片天的。到了今天,他們大都上了年紀,不再具有再投資和創新的鬥志。政府應進行新一輪的經濟分權,為新一代企業家提供有利的政策環境。 保留「平準經濟」能力 由國家所控制的金融體系,至今仍未有實質改革成果,中小企業仍然難以從銀行系統融資。中國的金融系統(儘管仍然是國家控制的),也具有了華爾街那樣的「過大而不能倒」的特徵。沒有人有能力或者敢於把這麼龐大的國有銀行系統「私有化」。這不僅是因為很多學者所說的「龐大的國有銀行系統對改革具有強大的阻力」,也是由於其他幾個問題。 其一,在中國這麼龐大的經濟體系,如果政府仍然要保留「平準經濟」(這是中國數千年經濟哲學的核心)的能力,仍然需要掌控龐大的金融系統。其二,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金融私有化」,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反而往往導致了寡頭經濟。其三,從西方私有銀行系統運作的經驗來看,私有化並不見得能夠有效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通過金融自由化,動員社會資本成為必然,是理性思考的結果。 為什麼由理性思維推動的金融改革會導致股災?股災發生在經濟活動的微觀層面:中國股票市場已經運作多年,建立了諸多制度,而且和西方國家的制度設計並沒有多大的差別。問題在於,為什麼那些在西方能夠有效運作的微觀制度,在中國不能有效運作甚至完全失效呢?箇中原因不能僅在微觀層面找尋,事實上,而要重新審視頂層政策設計,以及中間的政策執行層面。 在中國,任何頂層設計都是一個政策概念,表達的是改革和發展的方向,我們不能要求頂層設計出完整的制度體系。即使設計了,也會出現很多問題,因為頂層沒有足夠的信息和經驗。這就需要中間層次做大量的工作,把頂層政策理念轉變成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才能到達微觀層面的運作。 現在看來,問題在於頂層設計,沒有回答「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市場化改革?」這個重要問題。這裏面包含一種錯誤的認知,以為市場化就是政府不干預經濟。就股票市場來說,就是簡單地降低企業和股民進入市場的門檻。其實,市場化並不是說政府不需要在經濟生活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而是政府角色的轉型,要從以往的直接干預經濟,轉型到規制型政府,對經濟活動提供有效的規制。 問題是規制什麼樣的經濟活動?怎樣規制?怎樣使得規制制度在中國的環境中能夠有效運作?這些都是中間層需要思考的問題。如果中間層沒有做處理得宜,把一個抽象的政策概念直接演變成微觀層面的個體經濟行為,必然會出現問題。 在微觀層面的確是有制度設計的,但問題是過於微觀,並且只是照搬其他國家的做法。諸多微觀層面的制度設計,根本就沒有考量到中國社會的特性和來自外部的潛在影響。這兩方面的問題在這次股災中相當明顯。首先,股票市場的設計,沒有考量到中國股民好賭博的民性。其次,就外部因素來說,制度設計沒有充分考量到在全球化狀態下,金融市場的運作必然要受到外面的巨大影響。 危機發生後,有人抱怨國內的機構和散戶做空股市,出現了「經濟漢奸」和「階級敵人」的概念;也有人抱怨是海外力量的「陰謀」所致。實際上,如果估計不到這些潛在的內外部因素,是決策部門本身的錯誤。內決策者對內外部因素估計不足,不作自我反省,反而指責內外部因素,充其量只是逃避責任。究其根本原因在於中間層次不作為,沒有清楚了解可能影響政策實施過程的因素。 類似政治錯誤足以顛覆黨國 政府動用了各方面的力量救市,試圖穩定市場。或許有人不滿意政府的做法,但畢竟政府有能力穩定市場。不過,如果類似事件發生在政治領域,就有可能導致國家顛覆。經濟、社會的改革出了差錯,執政黨可以動用一切力量扭轉局面,但政治領域則不一樣了,如果出了問題,再也難以扭轉局面。前蘇聯戈爾巴喬夫所實行的政治改革就是這樣一種情形。 實際上,今天中國一些領域的經濟改革,不僅達不到原來設想的目標,反而逐漸走向反面。例如,金融自由化的目標,本為鼓勵實體經濟發展,但因為缺乏有效的監管制度,很快演變成金融投機,資金不但沒有走向實體經濟,反而從實體經濟領域抽走了大量資金到投機活動,對實體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另一個例子就是近來流行的互聯網+政策。互聯網+意在產業升級,結合互聯網技術和實體經濟。但現在的互聯網商業活動對傳統商業活動有兩種影響。第一,商業活動從分散到集中,是商業活動的轉移而非升級。就是說從以前的非常分散的活動(例如百貨商店、小商店)轉向了集中,集中在幾家互聯網公司。說它是轉移而非升級,是因為互聯網商業並沒有多少的技術成分。第二,商業活動的向下競爭,而不是向上競爭。因為監管不嚴等原因,互聯網商業充斥着假冒偽劣產品。互聯網商業為那些假冒偽劣產品提供了巨大的商業機會,對那些真正致力於技術升級的企業產生負面的影響。從這個角度說,互聯網商業是對產業的反「升級」,而非升級。 這說明如果沒有中層的配合,理想的頂層設計會走向反面。今天中國的問題就是中層不作為,使得頂層的政策理念不能有效轉化成為切實可行的政策和制度,把理念轉化為現實。 1980和1990年代改革的成功,在於有效地調動了中層的積極性,有中央和地方兩條腿,兩個積極性。當時中央高層有改革的決心,有宏觀的改革理念,而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均積極實施和推動高層提倡的改革政策。當時,各省市到處試點,大家互相競爭,從競爭中尋找最佳的改革實踐模式,成功之後,再向全國推廣。更為重要的是,當時高層是容許地方進行試錯的,沒有試錯,就不可能有創新,容許試錯是改革創新的前提。 現在中間層不作為,有很多客觀因素。今天中國,需要一種集權式的改革,過去高度分散的改革模式已經過去,因為分散性改革所產生的諸多利益,到今天已經儼然成為了既得利益,要克服它們對改革的阻力,就需要集權。再者,反腐敗也促成了很多中層幹部的不敢作為,這倒不是因為他們有腐敗行為,而是因為反腐敗運動不能夠把反腐敗和改革試錯區分開。在這樣的情況下,誰也不敢試錯創新。 集權改革和反腐敗都是深化改革所需,因此中間層受到制約可以理解。但這並不是說,今天中間層不重要了。恰好相反,在頂層設計已經到位的情況下,今天的中間層要比任何時候都顯得重要。如果沒有中間層的改革和創新,頂層政策就是空中樓閣,沒有可能落地生根。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如何把集中起來的權力盡快交給具有改革精神的中間層;如何在繼續推進反腐敗的同時,把腐敗和改革試錯區分開來。在頂層政策設計之後,中國改革能否成功,就取決於能否動員中間層,發揮中間層的改革動力了。

一些幹部官員比老百姓更需要「巫術」,升官、求平安都需要求助於不同類型的「巫術」活動。此外,很多商人明明是通過自己的辛勞和努力打拼出一片天下的,但他們往往傾向於把自己的故事「巫術化」,好像自己和別人有什麼不同,而得到了神秘力量的幫助。

類似王林那樣的「氣功大師」的例子,自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可以說是層出不窮,倒一個,又出來一個……不同現象或多或少都從不同角度折射出文化的墮落。

一個和平的國際秩序需要中美兩國的有效合作。美國需要中國,也不能失去中國;同樣,中國也同樣需要美國。在實際國際政治生活中,兩國的合作也一直是主流。如果雙方都能意識到,兩國的合作是雙贏的,而在核武器時代,衝突一定不是零和遊戲,即一方勝利和另一方的失敗,而是雙輸局面,那麼要建立和平共存的新型大國關係並不困難。

中國這場股災的確提出了一個嚴峻的問題:執政黨是否選拔得出和留得住出類拔萃之輩,來統治和管理國家和社會。

中國需要新的經濟政策來提供足夠的增長和發展新動力。在這個內容裏,人們可以把目前的內部「眾創」和外部「一帶一路」視為是中國經濟政策的兩個新主體……

中國憲政是否成功取決於「關鍵少數人」。例如,如果執政黨的精英不能踐行法治,如何可能要13億老百姓來服從法律?執政黨最近提出的「四個全面」,其中兩個「全面」就是全面建設法治社會,全面治黨。可以預見,把法治和治黨結合起來,應當是中國憲政之路的突破口。

兩個大國之間的衝突和戰爭是「常態」,而和平則是「非常態」。這個「非常態」則是中國所必須追求的。避免中美衝突的「宿命」,是「新型大國關係」戰略的全部意義之所在。

當今世界,隨着全方位的全球化的深入,已經產生出越來越多的非正式力量,它們能夠跨越國界,在全球範圍內活動。目前,至少有三種這樣的跨國界非正式力量,正在影響甚至左右着很多主權國家的行為……

對西方,中國存在着兩種傾向性,即過分恐懼和過分輕信。這兩種傾向性既表現在政策話語中,也反應在實際的外交政策層面。兩種傾向性都是極端心理,是自信不足的表現……

九七回歸之後到今天,香港出現了很多的問題,並且問題的複雜性愈來愈甚。實際上,香港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大挑戰。為甚麼會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這裏,在很多方面的因素是可以考量的。

「西進運動」指的是中國的戰略重心,移向國家西面的趨勢。儘管類似的風險也存在其他各種戰略調整,但西進所包含的風險巨大,如果不當心,中國就會陷入中東衝突的泥潭。中亞和中東地區過去是埋葬帝國的地方,現在仍然是。中國如果沒有足夠精明的策略,就會很難避免重復其他大國所走過的老路。

美國領導的西方很快把其地緣政治秩序擴展到前蘇聯的領域。蘇聯東歐共產主義一解體,美國各方面都沒有了競爭對手。整個世界似乎都在美國的掌控之下。這是人類地緣政治歷史上的奇跡。但是,為甚麼在冷戰結束之後短短的20多年時間裏,美國衰落了呢?

其實,人們可以從更深層次來思考 TPP 這樣的貿易投資形式,提出類似這樣的問題:從非經濟的角度來看, TPP 是什麼、它的實現會對當地社會帶來什麼影響?

去年以來,經濟下行壓力之大遠遠超出了預期。本來「新常態」就是要實現長期平穩的發展,但現在看來,這並不容易實現。

1980年代,文革剛剛結束不久,一代受害者感覺到文革的可怕,討論着如何才能消除其餘毒,避免死灰復燃。但久而久之,隨着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和各種制度變革的開始,人們覺得文革已經成為過去,相信文革那樣的事情既不會回來……可是,最近中國意識形態領域和某些實踐領域所發生的變化,使得很多人開始改變這個觀念……是甚麼樣的變化使得這些人開始有了這樣的擔憂?概括地說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政商關係無疑是中國腐敗的一個重要根源,不過,要對政商關係作現實主義的和科學的理解。二戰之後,世界上最成功的發展要數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體,被稱之為東亞奇跡。東亞經濟體的成功是同時發揮了市場和政府兩個作用,政府和市場的有效配合,使得東亞社會僅用了30來年的時間,走完西方100多年的歷程。

市場衝垮了家庭和地方社區的功能,但本身又不能承擔社會福利功能,因此就把所有家庭和地方社區的功能移交給了國家。誠如馬克思所言,市場把一切社會關係貨幣化。社會和國家的關係也變成了一種貨幣關係。「一人一票」的制度又使得社會個體擁有政治權利,向國家要求社會福利。這樣,市場所產生的貨幣關係,和「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互相強化,不僅使得國家的福利功能愈來愈得到強化,而且也使得國家這一制度設置不可重負,難以持續。

儘管極右派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能否在法國執政,及其執政後會否把它的意識形態轉化成為實際的政策等,還都是未知數,但人們必須對即使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變化給予足夠的重視。在亞洲,意識形態在政黨政治中並不重要,亞洲的政治力量往往是先有利益,再去找意識形態來論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但歐洲則相反。

當人們把李光耀和新加坡放到後殖民地時代世界政治變遷的大歷史中去考察的時候,其非凡的意義才顯現出來。李光耀所建立的新加坡模式,不僅關乎李光耀本人,也不僅僅關乎新加坡本身,而是關乎不同社會所需要追求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選擇和創新。

中國的崛起會使亞洲價值成為西方價值的另一個選擇嗎?這涉及1990年代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提出的文明衝突的命題。西方並不認為亞洲價值會取代西方價值,因為作為文明的西方價值根深蒂固,沒有任何其他價值可以取代。西方所擔憂的是,會出現西方之外的價值選擇嗎?

如果說抵制任何形式的民主的發生在政治上並不可行,甚至會導致政治的失敗,不加選擇地引入西方式民主,也會導向同樣的結局。如果說民主不可避免,民主也不可避免是多元的。未來的歷史會告訴人們,贏得最終勝利的,是那些能夠找到符合自己國情的民主模式的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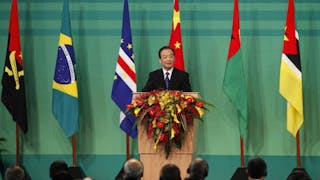
從宏觀層面看,宣揚文化「走出去」並沒有什麼錯誤。問題出在文化如何「走出去」?文化必須「走出去」,但「走出去」的方式很重要。

如果中國出現顛覆性錯誤,少則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多則已有的改革成果會付之東流。因此,「在哪些領域存在犯顛覆性錯誤的可能性?」這一問題就成為關鍵。

十八大以來,中共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腐敗運動,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着。反腐敗的現狀如何?運動到今天有什麼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如何深入下去?反腐敗運動向何處去?

中國所從事的多邊主義實踐,無論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到現在為止,具有一些特點。第一,中國的多邊主義既沒有挑戰現存秩序,但也沒有確立起為其他國家普遍接受的區域秩序。第二,中國所確立的多邊組織,不能說沒有用處,但其有效性並不令人滿意。第三,對相關國家來說,中國所確立的多邊組織發生了一些作用,但對自己的國家的發展也並非那麼相關。

絲綢之路不能僅僅停留在宏觀的設想,口號式的政策更是不可行。絲綢之路要成功,中國既要搞清楚要做什麼,更要搞清楚怎麼做。沒有一系列切實可行的策略和政策工具,絲綢之路很可能只是紙上談兵。這方面,中國已經有很多經驗教訓了。

對中國來說,問題已經不再是要不要走到亞、非、拉等地的市場去,而是如何有效、安全地走出去。再者,從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戰略來說,中國也必須走到那些地方去。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對發展中國家,中國應當如何履行自己應當履行的國際責任?可以說,絲綢之路是中國走向國際、承擔國際責任之路。

中國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必須尋求一條和發展中國家尊重與發展、合作與共贏的道路。尊重與發展、合作與共贏應當是絲綢之路的主題。

今天的中國正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在實現本身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帶領發展中國家走出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困局,讓全球經濟在激發增量的過程中,平穩達到結構再平衡。在國際責任的構架內,中國能夠避開西方和美國對中國的潛在圍堵,正面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從而實現長期的和平發展、民族復興的目標。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絲綢之路才顯現其不尋常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