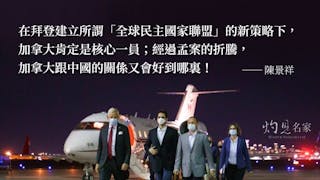人多好辦事,當前的抗疫工作在在需人,但政府動員能力差,連內地送來的物資也組織不了人手派出去,試問更龐大的全民強檢又怎能推行?下屆政府如果是反林鄭派的人上場,又會否為了顯示前任「不負責任」而硬推?

對抗疫情,最「正路」的方法始終是開發疫苗、特效藥,以生物科技帶動研發工作。動態清零的方式是結合醫護和行政措施,好處是見效快,但耗用的人力物力太大,只屬一時之計。

疫情緩和之後,香港真的是百廢待舉。如何重振經濟、恢復對外往來,都要從長計議。中國終歸要重回國際社會互聯互通,香港何嘗不然?適當地展開探討疫情緩和後「與病毒共存路線圖」是務實做法,不是彌天大罪。

本地疫情反覆,限聚令時鬆時緊,經營者「今日唔知明日事」,根本無法正常營運。前景不明是營商大忌,現在疫情失控、確診個案急升,香港其實已陷入一場疫症危機,但政府似乎束手無策。

以香港的政治格局,不管誰當特首,都難逃弱勢宿命,故此再猜誰會出來參選已沒有多大意義,押後選舉也不會令選情突變,因為形勢已經明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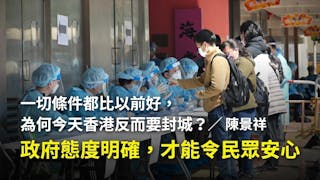
問責是一回事,但硬說政府沒有落實動態清零,而且是故意放軟手腳、陽奉陰違而造成今日局面,我覺得是言過其實,把抗疫工作過度「政治化」了。

好的方法,誰會抗拒?問題在每個地方條件不同,特區政府的執行力弱,民眾多不願聽政府指揮,甚至有抗拒情緒,內地一套很多時候想學也學不來!

財多好辦事,香港這幾年相當困難但仍可捱得過去,皆因財政充裕。過去積累下來的儲備,在困難時不用,還待何時?再派「無條件基本收入」,財政司長還要考慮什麼?

架構重組,目的是為了令政府功能更有效地發揮,政策推行更協調、更有力;但這些都只是組織設計和官僚體系的理順,難度不大,行政長官要做,一定可以做得成。真正難的,是未來3司15局到底可以找什麼人出任?

北京明顯挺特首處理這次事件的手法,林鄭可以避過一次政治危機,但這是否表示中央挺她連任?兩者又不能畫上等號。至今為止,北京對下任特首的安排似乎仍舉棋不定,正是因為局勢迷離,要求林鄭下台的聲音才陸續有來。

一個開放社會,不需要政府教新聞界如何做新聞,政府不應也不能這樣做。現在新聞界要求的,不是要政府提供「指引」,而是要清楚交代檢控的理由和證據。

可以預見,即使經過「淨化」,未來的議會仍然會有各種各樣的利益分歧,以及不同的政治傾向;各個政黨和團體代表不同利益,它們在一系列如土地、稅制、青年、教育、財富分配等議題上,仍然會有不同立場和意見。

對中國的科技公司來說,美國投資者習慣投資創新,美國交易所也接受各種估值方法。然而,近幾年美國對中國的敵意不斷加深,北京也不願見企業長期「依賴」在美國上市集資。

中國要抗衡美國的國際統戰、爭取西方國家支持,應該以香港為基地;以此考慮,香港不應再處處封殺西方媒體記者,這是平白浪費了香港的優勢,也削弱了中國爭取國際支持的機會。

美國將會跟中國激烈競爭,但會盡量避免觸發正面衝突,尤其爆發戰爭(災難),除此之外,美國會去得很盡。現在美國循各種途徑打擊中國,但又準備跟中國舉行軍備控制談判,就是要保證「沒有災難的競爭」。

儘管很多評論認為香港經濟要多元化,放棄過度依賴地產、金融,但事實卻是,地產和金融業仍然是公共財政的「大水喉」。科技創新是香港經濟轉型的主引擎,但現在仍未見成績,香港要繼續「吃老本」。

通關固然重要,但香港的國際聯繫也是我們的強項,一面倒跟從內地防疫措施,將令香港國際城市褪色,長遠對內地也非好事。

立法會內仍然會有不同政黨,但中央不會容許「一黨獨大」,政黨不能成為議會多數黨進而成為執政黨,這只是西方模式,並非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

內地堅持清零、堅守外防輸入的做法短期內不會變,如此,香港只有兩個選擇:一是要配合國家要求,設計內地版的健康碼;二是乾脆讓港人直接向內地申請「內地版健康碼」。

泛民政黨的出路不外兩個選擇,一是另組政黨,改弦易轍,和過去的泛民政治立場徹底「脫鈎」,重新處理和北京及特區政府的關係,如此方能生存。不走政黨路線,另一選擇是重返1970 、1980年代。

富不與官爭,大地產商富可敵國,但政府掌控權力,可以制定政策,也可以改變遊戲規則,到最後地產商都只能選擇與政府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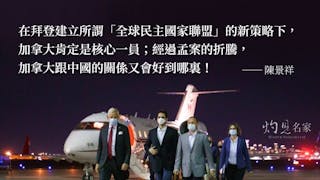
有分析認為,美國釋放孟晚舟是向中國示弱,損害了美國的國際形象,但與美國在阿富汗倉皇撤軍比較,後者不是更加不堪嗎?美國撤軍,是為了調集更多資源應付中國和俄羅斯,釋放孟晚舟,美國肯定別有所圖。

縱使內地和特區政府都表達了良好願望,希望香港融入國家的「五年規劃」,但由於體制不同,香港要融入真是談何容易!

然而,一份全球協議並沒有達成,大國之間不但未能合作,反而美國因遏制中國而掀起貿易戰,進而推動西方陣營跟中國脫鈎。對中國而言,全球化帶來的美好歲月已所剩無幾,中國必須因應形勢重整發展策略。

選委會成員雖然來自不同功能界別,但他們不能只顧自己界別的利益,中央寄望他們能兼顧全局,對中央的香港政策了然於胸。

近年香港運動員取得佳績,跟政府大手投資在體育上有關。但在體育盛事化方面,香港的成績並不顯眼,政府是否應該積極引入更多國際級大賽來香港舉行?

科技都那麼進步了,為何肆虐幾千年的自然災害,如大旱、洪澇、大山火等,人類仍然無法應付?災禍一到,為何我們依然束手無策?

拜登政府大體上延續了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某些領域對抗的力度甚至更大,要削弱中國的實力,從香港入手可以打擊大陸的融資能力。保持外資對香港的信心,應是特區政府此時此刻對國家的最大貢獻。

基層市民和外傭都是弱勢群體,最需要政府支援,然而每一次政府的措施都落不到實處,他們的訴求都得不到回應。政府的一意孤行,令人十分失望。

香港新選舉制度一大特色,是選舉委員會內很多成員均由團體產生,而澳門的「社團社會」,正是澳門政治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