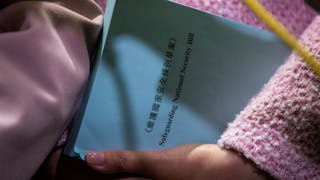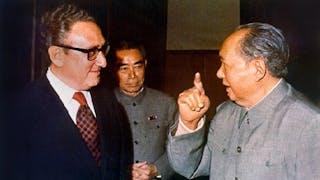在面對超大型企業時不亢不卑、以理服人最重要。港人對這場風波特別關注,是因為大家都希望消委會能夠一如既往,以專業精神捍衛香港消費者權益。在這個關節點上,消委會是不應跪低的!

拜登雖經多次因年齡問題受到質疑,但在任內所實施的各項經濟政策,卻為美國未來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民主黨正面臨是否更換候選人的挑戰,令人期待拜登能否順利續約。

香港的制度優勢獨特,可補充內地體制之不足,內地或難以複製香港的一套。自改革開放以來,香港在國家發展進程中都有無法取代的作用。

香港高等教育在國家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香港的主要競爭力之一。除了教育質素和國際化水平,在配合新時代需要推動高教創新變革上,香港也應走在前頭,為國家高教發展探索更多新方向、新模式。

北上消費熱潮令香港的購物天堂、美食天堂等傳統優勢大大失色,兩地價格差加上內地服務業水平突飛猛進,本港在購物和美食方面的競爭力都大不如前。反映了香港要保持吸引力,必須彰顯「香港有、內地冇」的特色。

翻開本地高校發展史,從來無出現過校董會/校委會與校長勢成水火的內鬥。政府介入了解事件,應一併調查到底是大學組織體制出了問題,還是個別主事人出了問題?大學與校委會之間的權責分配,是否應來一次徹底檢討?

今年11月美國大選,不管特朗普能否參選,「中國產能過剩論」、「中國威脅論」都會是這次選舉的最重要議題。中美關係不會轉好,只會更差。香港同樣處於風眼,也難求安靜。

城寨的命運有點像香港寫照,都是在中英上百年政治角力之間「巧妙」地生存着,並發展出自己一套求生方法和管治方式──並不完美,但大部分人都安守本分,在夾縫中求自己的託庇之所和生存空間。

在可預見的將來,中美對弈只會愈鬥愈激烈,衝突只會不斷升級。在大國頻頻過招之中要保持中立,甚至要當「和事老」,就如走鋼線,難度高且非常危險。

政治博弈往往超越市場實際,「不可能」的都會變得「有可能」。審時度勢,香港對聯匯制度的去留,應未雨綢繆,及早做好準備了。

很明顯,美國提出「產能過剩」只是表面理由,真正目的還是要在中美地緣政治上壓制中國。可以預見,在美國總統大選臨近之際,要求更嚴厲對付中國的呼聲將愈來愈強烈。中美關係看不出任何緩和跡象。

商人曰利,政府曰治。2019之後特區政府的角色已生大變,必須帶頭振興經濟;但這並不表示政府官員要事事參與,甚至為商人、投資者「站台造勢」。香港過去何嘗不是如此?

香港現在不是缺錢,是缺乏方向、缺乏領導力,不知道「後復甦」之路應該怎樣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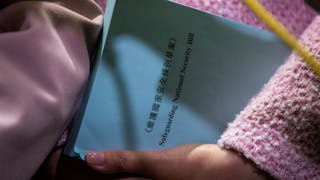
國安法處理的都是嚴重罪行,按理不會動輒應用。澳門2009年就已完成23條立法,之後一直沒有動用,這方面經驗可供香港借鑒。國安法盡量備而少用,也許是減少對港造成衝擊的其中一個方法。

中美關係不但沒有好轉,美國對華敵對行動反而不斷升級。從華為到TikTok,中美鬥爭的戰場擴展到企業。可以預見,大陸企業遭美國審查、打壓的數目,將愈來愈多。

在港英年代,港人的「共識」是沒民主但有自由;雖然手中無票,但港人卻可以百無禁忌,對政府施政放言高論。不過現在大家感到的卻是一股壓抑,一切要小心翼翼、好自為之的氣氛。表面的平靜,掩蓋不了社會內部的焦慮。

要避免結構財赤,除了縮減開支、發債支持基礎建設,還要加上經濟增長,節流之外還須開源。未來兩三年可以回復收支平衡,本地經濟的增長點在哪裏?增長幅度是否可追得上開支?

我們看不出政府解決財赤的方法,也看不到經濟復甦的苗頭,政府官員卻不斷強調大家毋須過分擔心。是官員真的有把握,還是我們「太過悲觀」?

特區政府經常說,23條立法後香港就可專注發展經濟。現在看來,23條立法之後,香港面對的西方打壓只會愈來愈嚴重。香港最大的難題仍然是政治,而非經濟。

垃圾徵費、廢物回收,都是政府今年的施政重點工作。新區議會的使命之一是協助政府施政,對區議會來說,正是發揮它們在新時代履行新任務的最佳機會。

不統、不獨、不戰,相信已成為台灣三大黨大陸政策的「共識」。問題是北京能「容忍」這種局面到什麼時候?更難預測的是,西方國家如果用「烏克蘭模式」,這種策略會否終於觸發一場戰爭?

香港在新聞自由排名榜近幾年急跌,政府的官式回應都是強調《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新聞自由一如既往未受影響云云。此話當真?

去年全球主要股市都錄得升幅,唯獨大陸和香港下跌,充分說明了香港與內地經濟已連成一氣,榮枯與共。內地經濟一天未轉好,香港都難言真正復甦。

按《基本法》量入為出的原則,特區的財政預算須「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但事實卻是,香港已在4年內有3年錄得赤字,現在看來,回復預算平衡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當年區議會的定位,是港英政府逐步推行代議政制的試驗場和起步點。經「完善選舉制度」後,區議會全面「去政治化」,還原了本來「地方行政」的角色,從此區議會不再是踏入政壇的起步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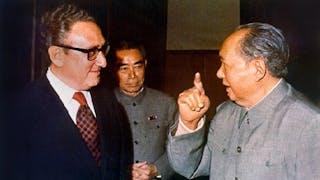
關於基辛格與中國,史家津津樂道的都是他「詐病」飛往北京密會中共領導人,為中美關係破冰打開第一扇門。環顧現今西方國家,還有哪一位政治人物能夠稱得上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會不會是最後一個?

相比香港,新加坡沒有被美國制裁,跟中國關係友好,左右逢源,令區內競爭優勢正向新加坡一方傾斜。而由於香港面對的困局不容易扭轉,長遠來看我們的處境十分不妙。

這一回合的習拜會,拜登是「有備而來」,對華競爭策略和方案俱備,都是以削弱、壓制中國為目標。在這樣的狀態下跟中國領導人會談,試問又可以談出什麼結果?

可是,這一切現在都近乎徹底消失──議員、政黨、仍然生存的社會團體,大多是讚好、擁護,異議或批評聲音弱不可聞。這種「和諧氣氛」,到底是真正和諧,還是群眾有話不想說、不敢說?

政治領袖逝世,通常有兩種版本的評價,一種是官方的,一種是民間的;官方評價沒有否定李克強的功績,但民間「口碑」更多的是稱讚他「貼地」、務實,更了解一般民眾的所思所想,而且肯講真話、實話,不迴避、不掩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