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rnstein乃性情中人,台上是藝術家,全情投入,揮動指揮棒,把樂隊演繹樂章帶到更高層次。台下他是凡人,吃人間煙火,為愛情而煩惱。

文章最後幾句寫道:當宗教變得庸俗、商業化,教徒唯有依賴個人的修為,從冥想、禪養、讀經、思辨中,培養自己的品格、提升人生的境界。當然,也別忘了美妙的音樂。

書中有好幾位算是認識的,有同輩,有老師,有只有一面之緣,卻是一見難忘,印象深刻。孔慧怡書寫他們的時候,我們早已沒有見面。原來同一個人,在不同人生階段,出現我們眼前,會讓人有不同觀感的。

朱凱鈴(Jessica)年紀輕輕,少女時已「立志成為一位以生命影響生命的體育老師」。儘管教學繁重,朱凱鈴仍然積極參與義工活動,忙裏偷閒,又在12月17日完成了運動靜觀證書課程。

有舊生說:「我們唸書的日子,最怕到校長室見校長。入去見校長,就是接受體罰,讓校長打藤(那是個體罰合法的年代)。」大家當年進入校長室,接受「打藤」處分,受點皮肉之痛。為此,卻是引以為榮。

談到感情史,李歐梵(Leo)當然有話想說。他的成長,就由大學舞會開始,他們那一代文藝青年,「都是一群感情壓抑的『憤怒的年輕人』。」Leo是通過文學、電影、音樂得到慰藉。

不是一般人都願意去做的工作,SEN(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學生卻樂意為之。何穎璇老師說長者普遍接受SEN學生,愛護同學,而同學亦十分樂意服務長者,愛與長者相處。

Doris竟然也成斜槓一族。「一把年紀了,仍然可以靠學回來的知識搵食,仍能獨立自處。」 Doris說得開心滿足呢。

張愛玲在香港大學的日子到底過得怎樣?唱不完說不盡的張愛玲從來就不是目的,也不是終點,而是一個窗口,一套方法、一條蹊徑,從張愛玲重新出發,我想看看她還能將我們帶到多遠。

黃心村這位香港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系教授,「重新梳理張愛玲和她母校乃至香港的因緣……以檔案資料為佐證,還原一些模糊的歷史影像」,都寫在她的著作《緣起香港: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裏。

聶華苓說她一輩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陸,台灣,愛荷華,幾乎全是在水上度過的。長江,嘉陵江,愛荷華河」,又說她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

隔了多年,我們終於有機會在「他鄉」重逢,感到高興不已。曾經我們是「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忙碌。然後,我們不約而同,來到同一個國家生活,在不同城市居住。

Beckett的《等待果陀》,說的可就是一個「沒有結果的等待」故事。這與挪威作家喬恩·弗斯筆下的女主角等待奇蹟出現,一去不返的丈夫,或許仍會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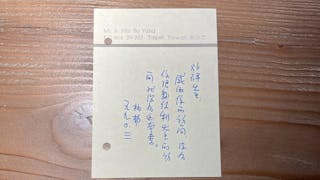
先說柏楊的雜文,問柏楊:「寫出人性黑暗面,觀點是否過於偏激?」「如果社會沒有毛病,要挑也挑不出來……如果只是歌功頌德,才會真的是滿天毛病。」

Morrie說了很具哲理一句話,這句話與孔子所講的「未知生,焉知死」有所不同,我們不是要探究死亡是甚麼一回事,而是知道每個人會有這麼一天,辭世而去。那麼活着的日子,就要過得有意思了。

兩天內看了三套與「告別」有關的電影:《從前的我們》告別過着不同生活的青梅竹馬,了斷多年的牽掛;《喜歡這個我》告別父母獨自生活,活出自我,擺脫世俗束縛;《怪物》思索成年人何時才能告別無知和偏見。

西西最後一首詩《疲乏》,對生命有了新的體會。人來到某個時刻,再也走不動了。眼、耳都累了,腦袋也疲乏了:「千千萬個問號/是非對錯,一直如影隨形/撕裂着你我的神經」。腦袋,一如眼、耳,都想休息了。

魔術師Carson(梁家榗)說:「疫情後,我經常都會變花(玫瑰為主,不怕有刺?),送畀觀眾……」收花者(不一定是女士)的反應多是一樣的,都會大聲嘩叫起來。他沒有想過,一支玫瑰魔力會那麼大的。

奧本海默為此覺得自己有份「殺害」日本平民百姓,接受審訊,他沒有為自己辯護,他要「博取」世人同情麼?在聽證會、在審訊時,這位科學家顯得出奇懦弱,與他在領導科學家研究製造原子彈時充滿自信,像兩個人來的。

唱藝術歌看似小眾活動,但日常生活以外的活動,喜歡唱藝術歌曲,沒有什麼不好呀。

寫於百年前的古典詩詞,一點不過時。當年的人物,有過風華正茂時刻,他/她們並不古板守舊。

唐朝一代寫詩的詩人多不勝數,志清選出100首詩(有只選其中幾句),畫面意境各有不同,有高雅,有貼地,有趣緻,詩與畫皆能道出不同的人生況味來。

誰說鄉居生活閒適?曉文不是個愛停下來之人。傳來她的生態導賞活動,又拍下秋海棠、獅子尾、球蘭、四照花,逐一向我介紹這四種夏天開花植物,講出它們的特色來。

昆德拉就是太愛講道理,不管他講的是《小說的藝術》,還是《可笑的愛情》。當他放慢步伐,不再用文字來諷刺人世的不堪,他還有什麼話要說呢?

年初問何福仁:「西西講足球的文章,可以結集成書呀。」「字數不夠出一本書。」半年過去,《港島吾愛》出版了,第一部分講足球,是為《再看足球》。西西談「看足球」,讓我們也看出人生道理來。

想對請我吃飯的朋友說:「其實最懷念的,不光是你們請吃的精緻美食,而是大家在一起的好時光。」

我們到過粉嶺打高球的,都會察覺到球場的保育工作做得好。Robert的觀察:那是「球會百多年來悉心料理,僱用無數的工作人員,採納了不少專家意見的成果…..房屋發展只會令這片土地的環境破壞更加快。」

四名澳洲中學生在校方允許下,試做一天生意,向同學售賣午餐。縱然結果未如理想,但「經一事,長一智」,比起金錢,他們收穫到更重要的事物。

在圖書館閱讀,80年前的讀者是那麼專注,今天的讀書人在閱讀,也是一樣全神貫注。當年圖書館只有書,來到2023年,圖書館的書架仍是放滿書,就是多了電腦、iPad。

談及當年的風雲人物,William三言兩語,講出他們不尋常的「本領」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