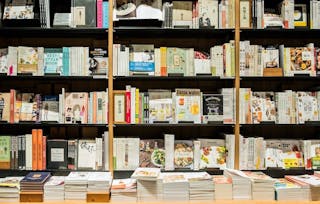1950年代以來的「共產風」歷史告訴世人:官方低價「贖買」民間資產,用其他經濟犯罪、刑事罪行以至政治理由扣大帽子,事例屢見不鮮。

屆時,難道中國寄望塔利班向美國發動攻擊,來一次真的圍魏救趙嗎?這種想法不切實際,也不合符中國的利益;因為屆時內部問題、兩岸問題也許會發生變化,應付乏力。

東奧政治爭議不絕於耳。作者認為,政治化是一種慣性,但只要大家清醒,泛政治化必會退潮。

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最終都會作出自己的選擇。這只是一個過程和快慢的問題。

不少運動員既是體育精英,也是「讀得書之人」,用一句通俗的話說,就是文武雙全;何詩蓓就是典型之一。反觀今天的教育方向,就是一種「倒模式」的設計,把年輕人的腦袋束縛起來,長遠來說,只會導致「思想便秘」。

當體育記者時,最深印象的是國家體委副主任袁偉民:他上場比賽,盡全力,退役後成為教練,就把力量傳給其他運動員。中國女排當年成為「多連冠」,就是袁偉民當教練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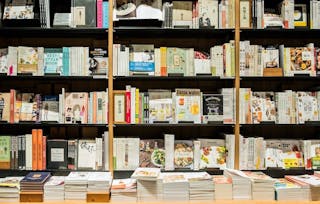
不少讀者在書展中跟我拍照留念,我都跟他們說:「希望不要因為這些照片而連累你!」他們都說不介意。我感謝他們的誠意,但心裏卻有說不出的滋味。為什麼會有這種連累別人的顧慮呢?是我的過慮?還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如果回顧香港和台灣關係穩定的時候,香港可以發揮兩岸的「潤滑劑」作用。馬英九當選台北市長之後,曾在2000年訪問香港,就是一例。

這次美俄峰會,普京是大贏家。

香港官場愈來愈多了一種「學問」,名為「厚面學」。

悼念「六四」是市民的意願和權利。忽然聽聞,有人在自己的朋友圈中進行「悼念『六四』智慧大賽」,並表示「有辦法不會犯法」。何解?

台灣也想借助陳同佳案來創造既定事實,就是台灣與香港是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接觸。雙方各有堅持,這就令港台關係跌破冰點了。

早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撰文批評中央政法委微博帳戶嘲笑印度疫情,被一些網民炮轟,還挖出他過去的言論,大肆攻擊。到底這是一個怎樣的文化現象?

港大的行動預示未來的一個結果,就是間接激勵出一些未來的社會活動家。當年的港大學生、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就是被港英政府打壓而加速投向左派陣營的。

飯後在街上閒步,唯一的得着是:這頓飯讓我多了一個可悲的寫作題材!

市民不想跟港府鬥氣,但他們總覺得官方卻經常與主流民意鬥氣,那就你有你鬥,我有我棄(hea)了。這種反應,甚至到了「自動波」的階段,不用其他人鼓勵,市民已經懂得反讀港府的話了。

最近,內地民政部發出文件,推出「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遏制結婚風俗的不正之風。內地網民普遍表示歡迎的支持。不過,中國的事情往往是動機良好,但執行方面卻經常出現偏差。

既然大局已經全在掌握之中,為了創造更好和更有說服力的氣氛,官方何不再來一些範圍更廣的諮詢?

新疆棉其實是優質棉,可以出口賺外匯,現在卻變成中國內部的「塘水滾塘魚」。外國政府雖然也沒有什麼好處,但已掩口而笑。

美國絕對搞不亂香港,香港如果亂,只會是「有權勢的自己人」搞亂而已。

市民不是傻的。大家都學懂了不少內地人的「反讀法」,也懂得用官方的行為來教育自己。張曉明等京官來港「諮詢」、「改善」選舉制度,很多人笑了。

中國政府控制人民,卻把人民的利益輸給自己的控制慾,這不是極荒唐的世界嗎?

拓展民智的同時,也要壯大民氣。因為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走出隧道;所以,必須努力穩住情緒,提高情商,否則只會自亂陣腳。愈困難的時候,就是愈要實行「新三民主義」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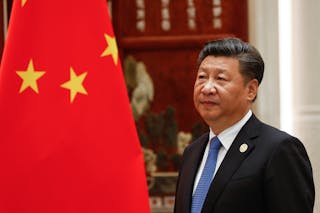
在中國的官場裏,有很多規矩,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逐漸變成一種官場文化,也就是一種常態勢力。

國家安全的範圍很寬,這些錢可以用在收集外國對香港不利的情報,也可以用在打壓官方認為「危害國家安全」的本地正常活動。第一點可以理解,但第二點就令人擔心了。

「借力打力」最終只會變成傷民而不利己的枉費氣力,卻傷不了真正的敵人。

在「左處未算左」的盲動之下,不排除支聯會還會受到更大的壓力,甚至被無理取締。可是,平反「六四」的訴求會因此而消失嗎?

港府已宣布到農曆年前,每日都會封區檢測,市民不是一概抗拒病毒檢測,對封樓封區也不一定有怨言。可是,港府的政策和措施在執行時卻沒有統一的標準,讓市民無所適從。

緬甸發生政變,美國和西方陣營必須分心關注緬甸局勢,將會分散針對中國的壓力。如果形勢發展到西方陣營需要動武的話,中國就更開心了。

最近香港官場出現一個猜謎遊戲,就是在疫情稍為穩定之後,會否有人被拿來「祭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