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金庸夫子自道中,可以見到金庸寫小說,最注重是刻劃人物和人性,着重感情的描述,正合文學追求之旨。

我看過許多死亡個案,也曾在死亡邊緣徘徊。年過60之後,經常猜想,會在什麼場景之下告別人生舞台。溫海的告別場景,也是我其中一個猜想,既然以小說面貌呈現,也少不了許多文學潤筆。

在我成長的階段,30年來遇到的朋友,談起金庸小說,每每滔滔而言,如數家珍。小說中的人物,便如老朋友在身邊一樣的稔熟。但近30年來和人談金庸小說,能接得上口的卻沒有幾人。

開始失憶(阿茲海默症)的房木,「每天都抱着記憶會失去的恐懼和不安」,又要不讓妻子高竹察覺。然而,可以瞞得多久呢?

魯迅的國學根基深厚,除著力唐詩外,還讀《詩經》、《楚辭》、陶潛等詩。祖父算很開通,鼓勵孫輩看小說,魯迅愛讀《西遊記》、《聊齋誌異》、《儒林外史》等。

我們可以說寫作以真實為信仰,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說的「真實是文學的責任」樣,在作家與寫作的信仰和責任中,真實是經驗的魂靈,而真實性則是真實之魂靈。

優秀的小說,反映人性,反映人情,反映社會光怪陸離的現象,是皇皇大道經典所不載,不讀則無所認識。不讀好小說,猶如建華堂而廢園林池沼,啖粱肉而錯失山珍,豈不可惜?

如果一個高中學生,能多讀小說名著,吸收其中學問,當更能體會社會上事物,對待人處事,會搓拿得更準更恰當。即使對一個偏重理科的學生而言,讀小說只會有利而無害,更可以藉此發展更健全的人格。

今日小說需要浴火重生,使社會大眾在享受閱讀的樂趣時,對人生有更深思的感悟和啟發。

昆德拉就是太愛講道理,不管他講的是《小說的藝術》,還是《可笑的愛情》。當他放慢步伐,不再用文字來諷刺人世的不堪,他還有什麼話要說呢?

傳統經典《紅樓夢》中包含很多創意寫作的元素,在立意、煉字、推陳出新、創作方面均有值得細味的地方。香港珠海學院中文系助理教授張惠教授以《紅樓夢》與創意寫作為例,啟迪聽眾如何將經典化為我用。(第三部分)

時代的進步,令文藝創作的要求已默默起變化。電視連續劇已取代了長篇小說,今天極少人再看長篇小說了。小說更好像已死亡,不大受歡迎。但筆者卻沒有這樣悲觀,因為無論電影或電視劇,都要由懂得寫好小說的人動筆。

芥川龍之介筆下有兩篇小說,「蜘蛛之絲」雖富有高度的寫作技巧,卻被牽入抄襲的疑雲;至於「阿富的貞操」,名字有點怪,也惹來很多討論。

劉紹銘1981年在美國寫過一篇文章分析疲憊的靈魂,談論帶着傷痕的文學。

「講笑」最少有300多年歷史了,除粵語外,至少還有福州話、客家話和吳語傳承了「講笑」一詞。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但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家,並沒有放下手中的筆,也沒有停止關注兒童讀者,相反地,是以更大的創作熱情,寫出了與兒童世界息息相關的佳作,成績斐然,令人欣喜。

John Grisham 2022年推出新作,不再是一部長篇小說,如Sooley、The Judge’s List,而是3個中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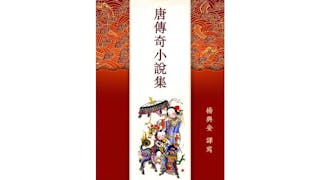
唐代小說何以稱傳奇呢?為什麼時人對唐代傳奇的認識比唐詩貧弱得多?

「師太」亦舒在晚年寫就的「紅色敞篷小跑車」故事,依然可以引發老中青不同代際女性的共鳴,只因那是關於青春的悸動記憶,滿溢着年少時的怦然心動與黯然神傷。

能習文言文,好比學武先學紮馬,馬步穩了才耍功夫,招招得心應手。後兩三輩的文人,文言文讀得較少,根基較弱,沒有「紮馬」功力,功夫便虛浮了。

蔣曉薇(Mei)的文字,仍能捕捉那似幻似真的感覺,可與電影《幻愛》互相對照。

小說作家要「心亂如麻」,心神要像一隻充滿好奇心的猴子,四處亂竄、東摸西摸。不要自我規限想像,落入社會習俗的套路,而要讓自己的心神可以隨世界而翩翩起舞。

清代除了《紅樓夢》、《聊齋誌異》、《儒林外史》等名著外,尚有不少充滿時代特色小說,多是遊歷見聞,使讀者眼界一開。

中國到了明代,既有說書人的話本底稿為創作基礎,時代條件亦催生長篇小說的出現,便是碰上印術普遍流行,讀者可以人手一卷細讀,下述明代四大奇書,各有特色之處。

「小說」一詞,早在二千多年前已見於《莊子》一書。但到唐代,才綻放出燦然華采。1919年「五四」文學運動,受歐洲文學影響,小說被推崇至文學殿堂。時至今日,文人創作中以撰寫小說最受大眾歡迎。

旅美學人夏志清教授曾讚譽白先勇教授為「當代中國短篇小說家中的奇才,五四以來,藝術成就上能與他匹敵的,從魯迅到張愛玲,五、六人而已。」他在台北接受本社專訪,暢談他的文學創作。

修慈悲心:生活裏從不孤獨,只因為有關懷自己的人。

2020年的世界百大長篇小說,中國並沒有缺席,包括「四大名著」和《七俠五義》。

唐代承隋制科舉選士,進士科猶被重視。一般來自本鄉縣舉人在應試之前未為人識,為求當道大員及試官青眼,常把文章投呈求之品鑒。這些文章,最受歡迎的便是短篇小說創作的傳奇了。

劉東山明嘉靖時人,為著名捕快,住在河間交河縣。此人擅於箭術,箭無虛發,且能連珠發箭,從不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