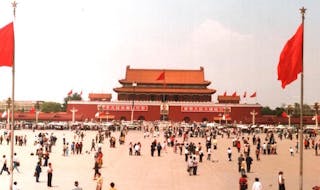其實,香港回歸中國後,中央對香港可以行使生殺大權,根本毋庸置疑。說得極端一點,明天中央廢除《基本法》,取消一國兩制,也是中國行使其內部事務的權力,全世界都無權干預。

民主選舉制度說起來雖然理想,但推行起來卻不是處處行得通,還要視乎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人民的教育程度,文化傳統,以及宗教背景等等。

一帶一路就是要讓美國知道不再爭新大陸,不再講美國的全球化,中國所講的全球化是恢復地位,出發點是以歐亞大陸為世界史的中心。

許章潤不僅精研法學,亦涉獵政治哲學和政治史,更難得的是關注現實政治和民疾,有為民請命的使命感,執著於讀書人的表達自由、獨立思考和良知。

中國新時期面臨怎樣的內外部風險?風險的根源無非來自兩個方面,即內部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外部的修昔底德陷阱,而中等收入陷阱必須通過可持續的發展而加以避免。

國家機關的改革等大事,應該理解支持。但中國的食品藥品監管機構體系的改革,都似乎有點兒戲。

特朗普的貿易戰(不止針對中國)令中國的經濟與金融備受壓力,但實質經濟的影響還未體現。在國際上抑制美國製造的危機便只有中國。

這些藥魔或奶類奸商,是強勢一方,有牢固的官商連結鏈,具「權錢交易」或「權色交易」的魔力;他們利誘一些官員、醫衛人員充當「保護傘」,斂聚不義之財。

我相信,珠海和香港這兩大城市,必將在大橋的帶動下,互相融和、經濟合作、飛躍發展。

疫苗造假事件雖在內地發生,但港人看在眼裏,也會造成心理衝擊。香港正在逐步融入國家發展策略,成為大灣區計劃的一員。選擇在內地工作或居住的港人,很自然會對這些造假惡行有切膚之痛。

到了今天,中國出現了「國家」和「社會」關係了嗎?從實踐層面來說,傳統的「官民」關係已經被改變了嗎?答案並不是很清楚的。

韜光養晦不能成為軟弱無能的遮醜布。 在當前的歷史環境下提韜光養晦,就是投降路線的代名詞。

在我看來,國家藥監局大案的真正教訓,是我們究竟怎樣看待醫藥、醫療體制中的政府地位。

《人民日報》的版面大有學問。《人民日報》每一個細小變化,都顯示政治風向,既要從端倪變化中嗅到味道,又不能過度解讀,很考「功夫」。

馬克思主義的制度發展史觀解釋不了中國制度的演進,更不用說其他西方理論了。

這種違法行為持續8年,是毛澤東式的後延政治株連、迫害。劉霞之夫劉曉波因追求憲政民主、擬草〈 0八憲章〉,被指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判刑11年。他即使是「罪犯」,劉霞不應被株連。

筆者建議在珠江口的桂山島大規模填海。在這接近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住房、創客園地、會展中心,再引進深圳的科技文創產業,讓香港年輕人與祖國的產業、市場、服務完全融合在一起。

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有效中國化,就很難解釋中國的實踐;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解釋中國的實踐,它就只能成為一種純意識形態,會失去其現實生命力。

在劉亞東之前,騰訊主席馬化騰於5月下旬在深圳的演講,說:「新四大發明」,「都是表面的輝煌,仿佛海灘上建樓,一推就倒」。

從「內部三權分工合作」這一新制度的進展,我們可以透視中國改革今天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的制度根源。

中國的想法很簡單:特朗普要徵關稅,旨在減少對華貿赤,現在中國開出一張超級購貨單,特朗普沒有理由拒絕。

兩個巨人對打,問題是誰先倒下,我跟你賭一毛錢,先倒下的不是中國。那就夠了。

我談起張瑞芳在《戲劇藝術》連載的回憶錄。王丹鳳說,今後打算寫回憶錄,給新一代的藝術從業員參考。

反政府遊行的低參與率可能意味着人們已經死心,不再相信他們的聲音能改變什麼。當人們在實現政治變革方面失去希望時,他們的放棄並不是政府的勝利。

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的角色,需要執行國家交付的任務,任何香港特區政府需要付諸實行的政策、任何機構設置以至財政撥款,最終還需要立法會通過,最後還需要在香港原有機制中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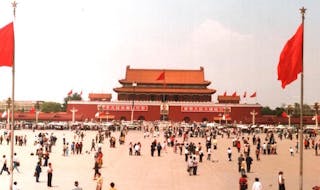
其實至今,連當前的中共領導人都知道,「共產」兩個字與當前的中國政治理念完全背道而馳。但是,又有哪位領導人有這個魄力和膽量,把「共產黨」這個名字改了。可是你不改,顧名思義,貽笑大方。

金耀基在這次訪問中明確指出,一個民主社會能不斷借鏡別人,是成長的關鍵。一種關閉自己、自我成長、甚麼都第一的,要成長是不可能。中國在未來「可以」有大願景,對外要跟開放改革的精神符合。

40年前的「實踐觀」與「兩個凡是」大論戰,形成反極左的政治生態,許多人走出「死神陰影」,電影界人士則「重回舞台」。

改革開放這40年來,大陸真正走出過往混亂、意識形態為主的政治,慢慢走向理性的主義。「作為研究中國現代化的人,看着這個長期發展,基本上是安慰的。」金耀基說。

中國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這可以成為中國版全球化的口號。而之前提出來的一帶一路倡議,又可以成為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