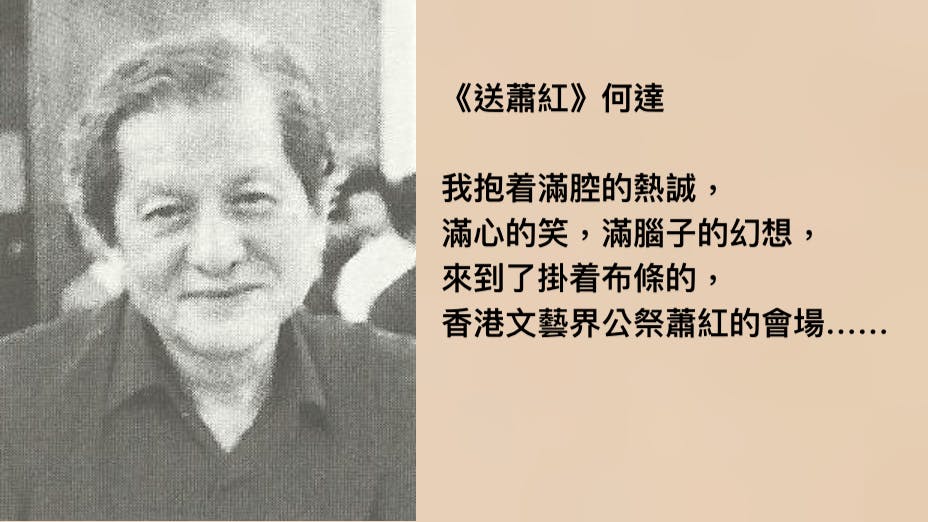最近,由於參加《香港文學大系一一1950至1969》的編寫工作,再次讀到了何達先生的詩作:
《送蕭紅》
……
送一個遠行的人,
到一個使她快樂的地方,
送一個體弱的人,
到一個醫治療養的地方。
送一個寂寞的人,
到一個充滿溫暖的地方;
送一個有才華的人,
到一個施展身手的地方。
我以為會有鮮花、美酒,
我以為會有笑語盈盈 ,
我以為會有歡聲、有鼓掌,
有紅綢彩旗在空中招展。
我以為我可以看到,
我一向喜歡的作家,
我以為我可以向她,
表示一下我的敬仰。
20年前,她站在遠遠的台上,
穿一條藍色的裙子朗誦詩篇;
會場大,人又多,她聲音小,
我在後面瞪着大眼睛也聽不見。
我以為今天可以和她握一下手,
我以為今天可以看清她的臉;
在心中我想好了幾句詩,
有機會我要對她唸一唸。
沒有陽光,也沒有下雨,
這樣的天氣正適合旅行,
要是我能一路坐在她的身邊,
聽一聽她講她自己的作品。
那是沒有疑問的,
她的身體將恢復健康,
那是沒有疑問的,
她的作品將源源不斷。
那是沒有疑問的,
她將回到她的故鄉,
她用血淚刻劃過的生死場,
將是她謳歌讚美的對象。
那是沒有疑問的,
她會寫許多我們想知道的東西,
那是沒有疑問的,
她的筆將給我們無窮的快感。
她的筆,她的心,她的靈感,
她的經驗,她的愛,她的希望,
她的敏銳的感覺毫無疑問地,
會把新人新事寫得閃閃發光。
我抱着滿腔的熱誠,
滿心的笑,滿腦子的幻想,
來到了掛着布條的,
香港文藝界公祭蕭紅的會場……
何達先生的詩作,一如既往,充滿了想像,充滿了感情,漸漸地把我帶進了那久遠的記憶之中去。
我第一次見到何達先生的時候,是在電視的屏幕上。那是80年代初,中國剛剛啟動開放改革的大門,何達被邀請回國,在北京的春節晚會上,他身穿短衣短褲,以一個長跑者的姿態,為一萬聽眾朗誦他的詩作《長跑者之歌》,得到滿堂的鼓掌聲和喝彩聲。據說周恩來總理的遺孀鄧穎超副委員長也受了感動,要何達抄一份詩作送給她。
文學創作的激情
我正是從那時候開始認識了香港的前輩詩人何達先生的,原來,他是我父親的好朋友,不久之後,我們就在家中迎接了遠道而來的何達先生。那一次,何達先生和我的父親久別重逢,彼此都十分激動,談了很久才戀戀不捨地告辭。父親告訴我,何達先生的詩作,一直與大時代有着相關相連的脈動。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何達是西南聯大的學生,(我父親當年也曾在西南聯大工作),思想上受到救亡運動的影響,學術上受到聞一多、朱自清等大師的感染,他執起詩這個武器參加戰鬥行列。他的詩,曾經貼在校園的牆報上,引起了老師朱自清的注意和欣賞。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香港,何達先生都一直保持着文學創作的激情,優秀的作品不斷地發表,他也常常親自朗誦自己寫的詩,感動和激勵着一批又一批的文學青年。
而我更感興趣的是,已經年屆70的何達先生,為什麼還那麼強健,可以在冰天雪地的寒冷天氣下,只穿着短衣短褲?這實在是很驚人的,也特別令人佩服!到機場為何達先生送行的時候,我就忍不住向他發問了。他笑着告訴我,這是他到南華會做體育運動鍛煉和洗桑拿浴的結果。
我結婚以後到了香港工作、生活,參加了香港作家聯會,見到了何達先生,感到非常親切。他送給我一本著作《興高采烈的人生》,我認真地拜讀了,書中收錄的全是閃耀着理想激情的作品,就如同書名一般,在在顯示出作者對生活、對生命的熱愛。自此之後,我更關注何達先生的創作,每一次參加香港作家聯會的活動,都希望能和他見面、請教。我也很喜歡朗誦他的詩,尤其是這一段:
詩是我的笑語
也是我的宣言
詩是我的地圖
也是我的時間
我眼中的樹是詩之樹
我腳下的路是詩之路
過橋的時候橋就是我的詩
過橋的時候詩也在橋下流過
曾經有一段時間,何達先生和我一起在香港作家聯會的理事會工作,令我有更多機會向他學習,感覺很好。可是,他後來不怎麼出席本地和作聯的文學活動了,我覺得似乎是有什麼問題發生,心裏很不安,恰好遇上一位舊朋友,才知道他是和何達先生租住同一個房屋單位的。我便請他帶我上門去看看。
當我們進入那個單位,卻看不見何達先生的身影,他是有事外出了吧。朋友帶我去看何達先生的浴室,裏面有很多雜物,浴缸上堆放着一張張的舊報紙,看來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清理了。朋友又告訴我,何達先生不定時地外出活動,也很少在家裏正正式式地吃一頓飯,只是每隔兩三天,就看到他從外面買回一盒西餅點心,到用餐的時候,馬馬虎虎地吃一些點心就算。看來他是一個不會照顧自己生活的人啊。總之,我在那裏看到的情況,都是令人擔心的。事後,我向作家聯會的秘書反映了何達先生的狀況,希望她再抽時間訪問何達先生,並且留意催促他定期吃飯。結果,秘書欣然答允並實行了。
事後的一次,作家聯會舉行港台作家文學座談活動,何達先生罕有地出現了,我滿懷歡喜地走到他面前,他用茫然的眼光看看我,張開口就問:
「你見到周蜜蜜小姐嗎?她有沒有來?」
我的心中一凜,盡量抑制着情緒,說:
「我就是周蜜蜜啊。何先生,您還好嗎?感覺怎麼樣?」
他的神情卻很不確定,茫然的眼光更加茫然了。
我頓時感到說不出的難過。
過了一些日子,何達先生住進了南朗山的療養院,我和香港作家聯會的朋友去探望他,看見被老年病痛折磨的詩人,一臉的憔悴,雙腳不良於行,令人更加感到心痛……
如今,何達先生已經遠去,可幸是他的詩作依然在我們中間流傳,他那朗誦詩歌的抑揚頓挫之聲,還在我們的耳際不時回響:
對於這個時代
我
是一個「人證」
我的詩
是「證」
在
為生存而奮鬥的人們的面前
我
火一樣地
公開了自己
原刊於《大公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