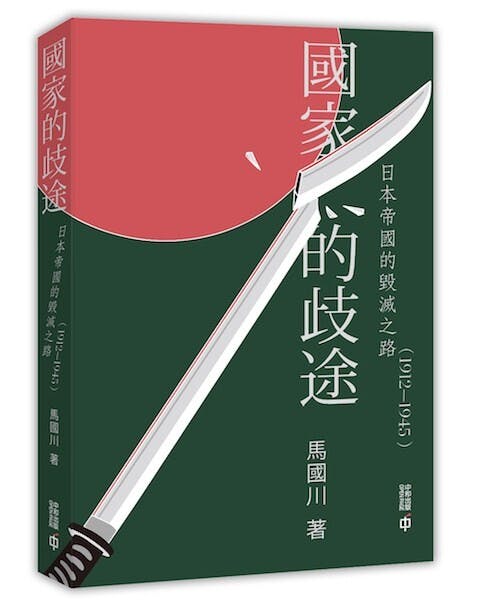馬老師,您現在在寫哪些方面的書?
1912-1945年的日本
哇塞,這段歷史太沉重了
是的,愈寫愈沉重
這是今年5月中旬我和日本朋友小針健一的微信交流。小針是一個20多歲的小夥子,幼時候隨父母由中國東北移民日本。他是明治維新探訪之旅的導遊,中日雙語俱佳,獲得了旅遊團友的好評。
這次文化旅遊是湘財證券創始人陳學榮先生組織的。從4月底到5月上旬,我們一行10多人(著名歷史作家唐浩明老師夫婦也參加了)在東瀛大地上行走。從鹿兒島到長州,從京都到東京,我們追尋明治維新的史跡,探索一個後發國家崛起的秘密。此行的中間點,是位於關門海峽邊上的下關(又名馬關),也就是124年前李鴻章簽署《馬關條約》的所在地。當我參觀日清講和紀念館時,歷史風雲都來眼底,太多感慨湧上心頭,遂口占一首打油詩:
兩百年來世事艱,傷心最是近馬關。
三千里外問國運,青史莫作等閑看。
是的,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近代以來的國運卻如此不同,難道不值得認真思考嗎?
國運如此,夫復何言?
一位我所尊敬的前輩看過《國家的啟蒙》書稿後說,這本書好像沒有寫完,應該寫到日本戰敗。確實,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從1853年黑船來航、日本打開國門,到1945年徹底失敗、無條件投降,是日本第一輪現代化進程的完整過程:開國──追趕──崛起──歧路──毀滅。這是一個以成功始、以失敗終的故事。《國家的啟蒙》雖然多處指出,明治晚期的日本已經出現了歧途,畢竟沒有將故事講完。

在前輩的鼓勵下,我開始追尋明治天皇去世後的日本發展軌跡。就像我和小針健一在微信交流裏說的那樣,這是一段「愈寫愈沉重」的歷史。如果說,明治維新是一首由低沉到高亢的英雄交響曲,那麼從1912年開始的日本歷史則是從充滿希望的歡快節奏開始的,後來愈來愈混亂低迷,至1945年曲終之際,已經絕望哀痛,不忍聽聞。
作為一個新興國家,大正時期的日本充滿了向上的希望:國內建設蒸蒸日上,1910年—1920年經濟增長60%,民主運動不斷發展,政黨制度、議會制度迅速成長;國外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躋身「國聯」四大常任理事國之列,主張人種平等和協調外交,贏得國際社會的讚譽。但是,就在國內發展、國際和平的背後,暗潮湧動,崢嶸時現。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給日本巨大的打擊,右翼勢力開始膨脹,1931年製造九一八事變,此後日本就像一條巨輪突然掉頭,逆流而行。
從這時起的10年時間裏,日本所有的舉措看起來好像都是合情合理的,可是日本人正是在讚同、甚至歡呼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舉措中走向了戰爭深淵。雖然有個別清醒者沒有被極端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潮流沖昏頭腦,但是大部分、包括知識精英都成為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吹鼓手,推波助瀾。許多人(特別是青年軍人)確實不願意假裝看不見社會的不公,不願意假裝聽不見民眾的哭聲,可是他們努力的結果卻將國家推進災難的泥潭。這不是更大的悲劇嗎?!
1941年日本和美國GDP總量比例為1:26,重要戰略物資的生產力比例為77.9:1。國力如此懸殊,為什麼日本愚蠢到要與美國開戰?其結果不但讓世界遭受塗炭,也讓自明治維新以來幾代日本人奮鬥得來的現代化成果毀於一旦。這種瘋狂的「民族切腹」行為是怎麼發生的?我認為,這是20世紀世界史的最大謎團。
更大的悲劇在於,從1931到1945,在長達15年時間裏,日本的最大戰場是在中國,為日本的瘋狂行為付出最大代價的也是中國。本來,中國局勢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平靜下來,此後十年各種建設頗有可觀,但是日本挑起七七事變,中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逆轉了中國的國運。
當我寫作《國家的啟蒙》一書時,常常為中日兩國面對世界衝擊而作出的不同選擇而感慨。當我寫作這本《國家的歧路》的時候,更多的是悲憤。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須臾誤」。 國運如此,夫復何言?有時繞室而走,心意難平。

軍國主義將日本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1915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爾斯坦·凡勃倫訪問日本。
這位以《有閒階級論》而聞名的大學者對這個新興國家頗有好感,他說自己看到了「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間思想上的相似性」以及「心理的相同」。在他看來,科學和工業的推廣導致了相似的文化價值和政治安排的出現,尤其是在像英國和美國這樣的國家。因此他預言,當日本變得更加現代時,日本人將丟棄「舊日本的精神」,擁抱遍及世界先進國家的「理想、道德、價值和原則」。反過來,相近價值觀的建立也會支持與歐洲和北美相似的作為上層建築的政治制度。
一開始好像果真如此。作為一個後發國家,大正時期的日本積極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但是很快,凡勃倫的預言就完全落空,因為狂熱的民族主義愈來愈控制了這個國家。毋庸諱言,對於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新興國家來說,民族主義是一個強有力的推動,但是一旦失去節制,那麼民族主義就會反噬新興國家。恰如德國詩人海涅所說:「沒有比狹隘的民族主義更有害的東西了。」
在大正時代,日本政治多元化、社會多元化,但是進入20世紀30年代,這個國家的氣質發生了變化。彼時的日本人對國家馴服,認為滿足國家的需要是天經地義的,將國家利益置於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才是愛國的表現。強調忠誠於國家和毫不猶豫地為國捐軀,釀成一種盲目的民族主義。
盲目的民族主義可以蒙蔽國民的心靈,也可以蒙蔽國家的雙眼。特別是在遭受世界經濟危機之後,日本沒有審視自己的問題,而是從外面的世界裏尋找敵人。它也如願以償地找到了:西方。日本是傲慢西方的受害者,日本應該從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政治壓制下解放出來,這種輿論成為主流。在明治維新時代被推崇的現代文明價值觀和秩序,而今被輕蔑地貼上「西方」、「資本主義」、「物質主義」等標簽。
盲目的民族主義讓日本拒絕承認普世的價值觀。它自暴自棄地退出「國聯」之後,就成為文明世界的棄兒。日本不但沒有反思,反而進一步鼓吹自己的特色,宣揚自己文化獨特、制度優越,號稱要「近代之超可」(克服現代性)、「超越西方」,彷彿全世界都應該學習日本。於是,政黨政治、議會制度等現代文明被踐踏,天皇制度被吹捧為世界最好政治體制,膽敢懷疑者就會被斥責為「非國民」(日奸),遭受打壓。
法西斯主義思想家北一輝說,一旦將那些外國雜質清除乾凈後,一個復興的日本就注定在民族國家交戰的災難中取勝,將會創建一個「偉大的革命帝國」。他的預言一部分是對的,因為,盲目的民族主義和狂熱的愛國主義的合流,必然導致軍國主義。可是,軍國主義沒有讓日本「取勝」,反而將日本推向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通過明治維新,日本成為躋身世界強國,給其他後發國家以巨大的鼓勵。可是最終它卻自取滅亡,這難道是後發國家追趕現代化的宿命嗎?當然不是。深入歷史現場觀察就會發現,即使是在歷史轉折點上,也並非只有一條道路可走,而是有多種選擇。即使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也完全有避免戰爭的餘地。縱觀日本現代化的過程,這個國家似乎每向前邁進一步,就要立刻再倒退一步、甚至兩步才行,結果以失敗國家告終。現代化是一個充滿荊棘的道路,只有戒慎戒懼,才有可能避免歧途。作為後發國家,尤其要保持理性,不要被盲目的民族主義所左右。這就是近代日本的最大啟示吧。

中國最應該學習和借鑒的是日本
2016年11月9日中午,我在東京日本橋附近的一家中餐館邊吃飯,邊緊張地觀看電視。當特朗普最終以306:232擊敗希拉里、當選第57屆美國總統的結果公布後,我悵然若失。雖然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就已經進入多事之秋,但是我預感到,未來的不確定性陡然增大,世界會更加無序。儘管有心裏準備,但是過去三年時間裏,中國和世界變化之快之大,仍然出乎意料。
全球化遭遇挫折,民族主義湧動,民粹主義上升,威權主義和強人政治回潮,地緣政治競爭加劇,戰爭危險冒頭,甚至有「注定一戰」的輿論公然出現。世界愈來愈令人不安,也讓有識之士對於未來表示擔憂。在這樣的背景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何以自處,如何面對世界?是繼續以改革開放的姿態融入世界,還是召喚民族主義,探索完全不同的現代化道路?這些都是不得不直面的重大問題。
如果說明治時期的中日兩國可以對照而讀,那麽明治之後,它們就像兩條不同道路上奔跑的馬車,漸行漸遠,已經無法比較。因為日本是初步實現現代化(儘管很不完善)後如何融入世界的問題,而中國是如何實現國家獨立、追趕現代化的問題。不過,對於我來說,1912-1945年的日本歷史對於今天的中國似乎更有意義。因為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山重水複,100多年以來穿越無數驚濤駭浪,中國這艘巨輪第一次逼近了「歷史三峽」的出口。但是,如何防止和克服狂熱的民族主義,融入世界文明,完成向現代國家轉型,是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
在全球化時代,如果失去世界視野和歷史眼光,囿於本國,難免重蹈失敗國家的覆轍。縱觀世界近代史,失敗國家不是少數,而且有些國家還會在相同的地方栽跟頭。因此,對於一個處於上升時期的新興國家而言,更有必要以開放的心態,深入學習各國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從中汲取智慧,避免歧路。中國至今仍然處在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歷史延長線上,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還沒有完成。國運可長亦可消,端看是否能夠學習和反思。
在我看來,比起歐美國家來,中國最應該學習和借鑒的是日本。可是,新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後,中國國力不斷增強,歐美發達國家卻籠罩在衰退的陰影裏。於是,驕傲情緒驟起,歐美遭到輕視,遑論「失去20年」的日本?對於這個一衣帶水的近鄰,不管是其現實還是歷史,我們都知之甚少。現在中國正處於發展的關鍵時期,是補上這一課的時候了!
每當我閱讀日本之時,有句話總時時迴蕩在耳邊:日本是中國的鏡子,也是中國的鞭子。以日本為鏡子,中國可以知道自己的進退得失;以日本為鞭子,中國可以讓自己保持警醒。
是為序。
馬國川
2019年11月12日 於北京
新書介紹
書名:《國家的歧途:日本帝國的毀滅之路(1912—1945)》
作者:馬國川
出版社: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