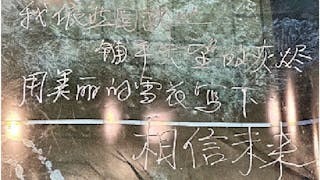唐代金銀器中的同類花紋,究竟表現在多少器物之上,不單是統計學上的問題,也涉及器物學的思想範疇。筆者通過香港古月堂的藏品,印證了若干其時深受歡迎的花紋,均重出於多種器物之內。此一具體發現,不但可推論唐代器物的鏨飾工序進行以前,必參考了各樣既定的圖案,並且為求精準無誤,或預先以圖紙在金屬表面刻出輪廓。此外,由於各時期的圖紋風格相異,帶有相同紋飾的器物便如時代的印記,互證彼此屬於同期的真品。例如在陝西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鴛鴦蓮瓣紋碗,內中鏨刻的六重寶花紋飾,便是極受唐人喜愛的一類。今天介紹古月堂的唐代龍羊紋八瓣型鎏金碗,也同樣具此寶花特徵,大家不妨從鏨紋和其他刻工對象中,找到唐代金銀器的共性,從中一望而知是皇室貴族所專用。
此鎏金碗囗徑12釐米,高度6釐米,底徑6釐米,重253克。(圖 一)從表面輕微的銅氧現象,可斷定此物是銅鎏金的製作方式。全碗的設計布局,集中在八個花瓣的錘揲,因而造成內凹外凸的八個紋飾區域。從內部觀之,各花瓣上寛下窄,形如喇叭,瓣底都作微彎收束,組合出八邊八棱的底部區域。(圖 二)在此區域以內,鏨刻着由圓瓣與梭瓣層層相叠的六重寶花紋飾。(圖 三)驟眼觀之,花型碗微微外反拋光,視線逐漸移至花心,乍見內底的寶花,可謂花中有花,閃爍之中引人入勝。唐代的鎏金碗一般設計嚴整,碗的內壁要做到徹底引光,便須要把金屬面錘揲至碗囗背面,然後預留一釐米的地方作修邊。此碗也不例外,包邊之處寛度平均,由於八條外凹的葉脈紋理清晰,碗囗圍邊至該凹處也經過特别處理,出現八處相應微陷的凹位。



早期君主御用之物
從外壁觀之,八瓣區域呈現了一幅美麗的風景圖。在布滿魚子紋的背景下,它由四龍四羊,夾雜着忍冬花,互相間隔組成。觀察羊區的範圍,忍冬花蔓平均分配於四個角落,中間鏨刻一頭奔跑的壯羊。羊頭向前瞻望,前腿伸張而後腿亦作180度的拉展,顯示着全速奔前之貌。其頸、身、腿處,皆有精細的毛紋鏨飾,小如羊蹄部分,在巧匠的鏨工下也原形畢露。(圖 四)而羊區的左右則由龍形紋區相隔,值得注意的是,牠不是慣常看見的飛龍在天之狀,也不是四足着地的走龍姿態,而是完全展示雙足直立之貌。龍頭向左而視,張口申舌,忍冬花平均地包圍龍身,令龍的本體更為凸顯。此龍作前後腳的站姿,前臂向左右伸爪,龍身的麟甲片片精緻,指爪巨細俱全,氣勢十分威武。(圖 五)


像這樣多區域的鏨刻,並展示密地的魚子和忍冬花紋,明顯是唐前期金銀器作的風格。在中國的長壽故事中,羊代表着吉祥之意,亦只有天子能配享永生的龍形,此物當為唐代早期君主御用之物。或由於它盛過酒水,液體殘留在鎏金表面,出現了較明顯的銅銹。至於碗壁之處,因以外凸的八花瓣作圓底收束,接近碗底之處亦形成八邊棱角,不須任何雕飾亦自成統一的區域。波斯薩珊王朝的金銀器中,常見在碗底邊緣鏨刻聯珠紋,在此碗底部也有同樣發現,裙腳並增加了蓮葉紋的圖案,反映注入更多的中國色彩。(圖 六)凡此可見,胡風與唐風並存的金銀器紋飾,是檢視是否初唐時期的一項重要標記。

從胡化到中國化過程
唐代天子器物,為何以站立之龍形顯示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原因:首先,從中國文化角度而言,龍在九天以外,常人難以觸摸,用今日的術語而言,未免過於「離地」。君主既為地上真龍,以雙肢腳踏實地,完全體現了當世治國權力,展示此為大唐天子的器物。其次,從中亞的外來紋飾而言,動物作站立姿勢者甚多,陝西歷史博物館珍藏的唐代雙獅纏枝銀鎏金碗,所鏨刻的便是一對半站立的獅子,彼此以一隻前肢對掌。筆者認為此等形態,仍未脱中亞器型造像的原型精神,相異之處只在於由獅子移植到龍體身上,出現大膽的結合嘗試。在現時可見的唐代金銀器收藏中,此類龍形造像實屬少見,反映香港古月堂藏品,於論證唐金銀器從胡化到中國化的過程,具備關鍵的參考位置。
此碗底部並無「大唐貞觀」字樣,卻於紋飾中暗示着是唐前期之作。(圖 七)從前述的各種個案可知,寶花紋飾或鏨於內碗底部,或鏨於外碗底部,完全視乎匠人的創作觀點。同様道理,鏨刻貞觀字様與否,在唐初的金銀器中也相當隨意。一些內外已具豐富紋飾的器物,碗底未必再刻年代;一些內部較簡約的蓮瓣紋鎏金碗,其底部會加刻花鳥紋,或以方塊形式鏨刻年代篆體。至於一些重要的金銀禮器,鄭重地刻上貞觀年代,再在框外配以花紋也是常見的做法。我們只能從既知的金銀器中得到此等初步印象,更多關於鳥紋、獸紋、花紋、枝蔓紋的刻工用意,還要不斷從新發現的器物比對中,獲得更客觀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