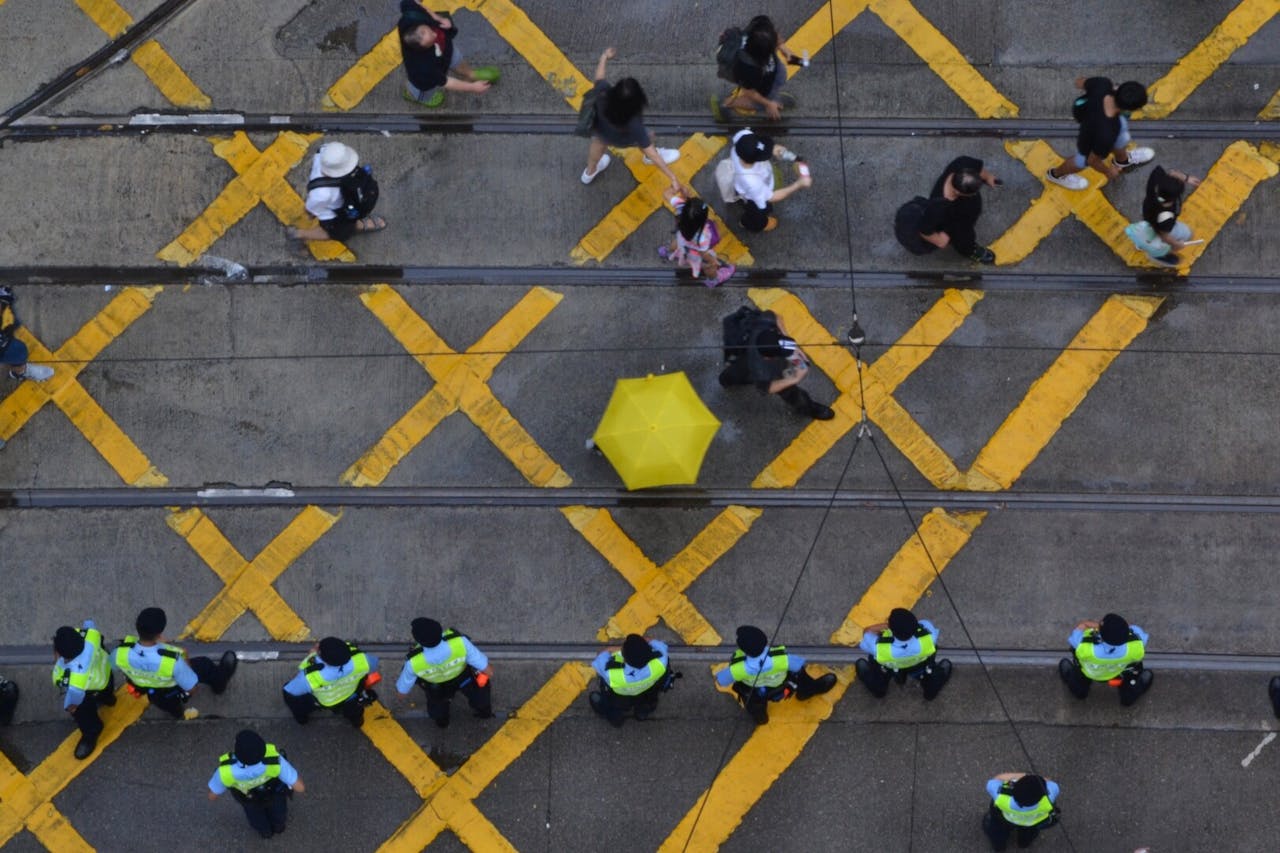我開始相信,或者這是一齣黑色喜劇。
過去20年是香港最需要求變的時候,但社會的主旋律卻是追求不變。而你以為是建制派最不想變(當然,他們確實也不會怎樣思考變革),可是現實卻是連站在對面的反對派也不會認真求變。
在香港,談變是一件相當艱難的事情。
或者就是這個原因,「沒有變過」成為了一種正面的東西。
需否認真想想如何面對轉變的大環境?
近期中央領導人忙着說「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建制中人不知如何插嘴,反而是反對派最有興趣去回應——他們連忙大叫既走樣又變形!我相信他們的意思是,領導人所指「不走樣」之處,正是扭曲最為嚴重的地方。但問題是:他們真的認為回到原型,便什麼問題都沒有嗎?究竟在他們的心目之中,「一國兩制」的問題是出於偏離初衷?還是連初衷也有問題?什麼才是原裝的「一國兩制」?說得直接一點,究竟香港有沒有需要面向未來、放眼長遠,認真想想究竟要如何面對一個不停在轉變的大環境?這一方所說的「沒有變形」,出於為自己辯護;說得白一點,「一國兩制」是政策,不是合約,只要那個「形」尚在,其他由微調到大改,都可以以「全面管治權」之名來操作。那一方所說「走樣」,則其實不知道應該怎樣做(要回去一個回不了的過去?還是衝向更不確定的未來?),總之作個反應、做個姿態,有點交代。
根據香港流行的政治劇本,反對派大罵既走樣也變形,便足以引起中方、建制的不滿,再而惡言攻擊。在舊時的政治環境裏,這樣的你一言我一語,大可成為一個政治議題,參與辯論的雙方均可乘機賺取一些媒介的注意、提高一下政治本錢。不過,今時今日,政治環境早已經歷重大變化,形勢截然不同。罵「一國兩制」走樣變形,不單止不足以爭取年輕一輩的支持(因為這樣的批評還停留在原有的框框之內),甚至反過來會受到包圍和攻擊,批判為「賣港之徒」。
那麼更激進的呢?「歸英派」(在內容上其實毫不激進,他們的特點是「激」,勝在說了一些部分人不會說、不敢說的話)的處境最可憐,連正正經經登台唱戲的機會也沒有。他們的劇本需要英國人的參與;如果沒有英國公開表示有興趣為了香港「不惜一戰」,又或者視港人為其國家公民,打算全數接收,則「歸英派」基本上無「英」可歸。神女(但也不見得是多數)有心,但襄王無夢。有關討論早已自行了斷。
「勇武派」的特點則在於「勇」,基本上與「激進」也扯不上關係(所以,更適合的標籤應是「激動派」)。理論上,「勇武」者之勇武,是以行動來解決問題,不理三七二十一動起來再算。有趣的是究竟他們要解決什麼問題?改變什麼現狀?這從來沒有說清楚。這個沒有說清楚的做法,有其實際意義。事關他們不善於團結,在未有說清楚、含糊過去的情况下,尚且四分五裂;如果說得清清楚楚(於是大家更自覺地跟其他人保持距離),那肯定只會加速瓦解。可是,無論如何含糊、概括,也總要有個立場、位置。問題是這個題目不好討論。
社會無方向地繼續航行
在過去幾年連番激動的行動中,大致上已將一些「左翼」的想法邊緣化。在雨傘運動中,「左翼」思想節節敗退,其實是很有需要好好了解和分析的現象。當然,在議會之內今天仍有自我定位為以推動平等、公義為己任的議員,但在整個社會層面上——尤其是在實體的或非實體的,年輕、好辯的圈子之中——則明顯地是靠向「右」的。在香港,一向都是靠「右」屬於多數,九七前如是,九七後亦一樣。本以為浩浩蕩蕩、波瀾壯闊的雨傘運動也會是一次思想的大轉變,最低限度會帶來新的價值觀,為公平、公義、民主、平等等概念填上豐富的內容,力求香港的社會制度來一次徹底的改變。但兩年多以來,除了小部分的「深耕細作」之外,更多的其實跟「右」的主流沒有太大分別。年輕人口頭上痛恨「老嘢」,但心底裏仍然有着不少老人的牽掛,卻又不敢宣之於口。受到「政治正確性」的壓抑,明明想搞民粹主義,總之好好醜醜將一些當權的(包括沒有什麼權力的反對派政黨中有頭有面的)拉下馬,又或者拆掉一個其實很細小的「大台」,只求「大快人心」、過癮過癮,現在卻要花盡心思,扭來扭去掛個大題目(愈大愈好,要「高不可攀」,太易可以實現反而麻煩),所謂出師有名。如果將他們在什麼聲明、宣言上的虛詞刪除,其實通常都沒有什麼很實在的內容。姿勢總是先於實際。雷聲大雨點小,是新近流行的策略。
更弔詭的是,由於虛張聲勢成為習慣,認識的一些年輕朋友,他們很快地成為自我的反面而不自知。理論上他們痛恨共產黨,但現在搖身一變,自己也開始搞很有「先鋒黨」特色的政治組織。理論上他們反精英,現在一天到晚以喚醒裝睡的人為己任,以為人人皆不知,只有自己最為清醒。
如此這般,恐怕應變的不會變,不應變的卻會改變。整個社會無方向地繼續航行。
原刊於《明報》,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