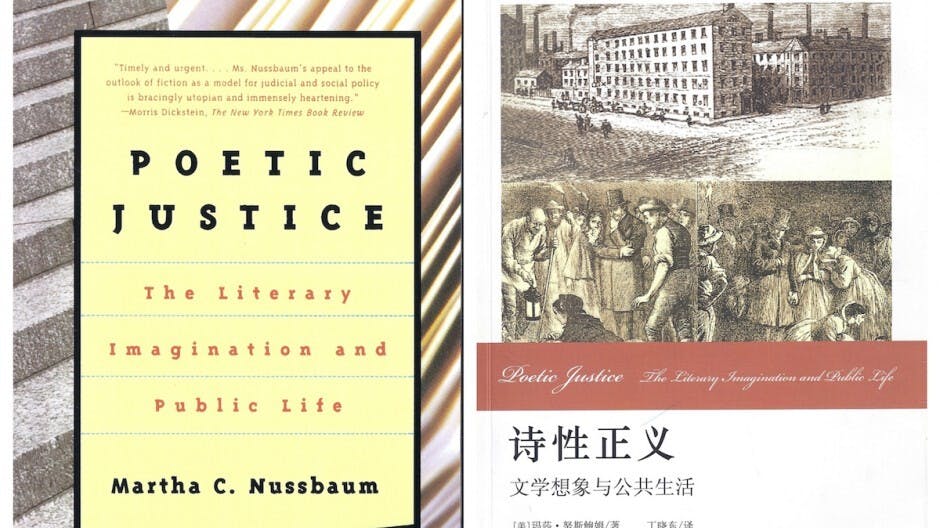佔領是表演性的行動
權威學者王德威曾說,佔領是很有表演性的行動,幾乎有劇場意味,是文學的延伸。「佔領中環肯定比佔領中大有象徵意味。發起者就像導演,參與者就像演員。」他形容這類行動「是短暫的,另類的,介乎容許和不容許之間的,在千百萬白領上班的中環,形成一個暫時的空間聚落,引起你的好奇、想像、恐懼等等,這就是異托邦裏最有創造力的部分。這是行動劇場,帶出的異托邦的力量」。民間佔領運動發展至今並沒有像王德威所說的,發生在白領佔據的中環,卻聚集在施政部門的核心地帶金鐘,而學生發動,又比由學界精英和宗教領袖發動更具象徵意味。可是,他的表演性卻不及掛在獅子山頭的直幡以及沒有正面與法律衝突及生活化的「購物」行動。
文學創作之於自由與公義(justice)的想像和思考,不能完全借力於目前社運聲音的沸沸揚揚來完成。試想,不論泛民或建制者,也鋪天蓋地發動社運式的聯署簽名、舉牌發聲、遊行口號等公民運動的行動,眾聲喧嘩,我們的眼球被媒體混雜的聲音所盤據。一旦帶着企圖,即或沒有私利和控制,最美麗的語言也變成用來宣告、聲明、宣傳、指導的駕馭性語言,最感動人心的語言,是讓人看見人間的醜陋和善良,希望與失望,生和死,愛和恨,促動人有追求自由和公義的決心。缺乏文學薰陶的社會就像是聾子、啞巴和失語症患者組成的社會。
詩性公義是對他者的體味與同情
惠特曼說詩人是「愛的靈魂和火舌」,詩人「發出民主的信號」,他有推動民主的使命──能想像、接納、同情和發聲的使命。通過文學的呈現,使人擴展那種有助於公共生活決策的想像力,對於異於自己的他者的生活有所體味與同情,是一種「詩性公義」。
文學的獨立性在集體回憶猶為重要。它不是什麼瘋傳誤傳的短信和號召,而是以跨越時間與形勢的眼光,擺脫貧瘠僵化的宣言口號,記錄民族文化的沉痛追思與回響。以不同的想像風格,詩化的思考力量,延展成超越年代的共同體。
政制討論各為其主,難免關注某集團或群體的效益性,即或談論選舉公義、程序公義,難免只講法律理性而忽略文學獨立於任何政權政治勢力或意識形態的捆綁,追求恒久的信念和貼近人類心房的情懷。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神學院、哲學系共同聘請的倫理學兼神學教授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C. Nussbaum)在《詩性正義——文學想像與公共生活》(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所提出的「詩性公義/詩意的正義」,強調公眾話語的公正性,必須通過文學所呈現的暢想(fancy)和敍事想像(narrative imagination),而這兩項恰恰是民主社會必然需要的組成部分。充滿暢想、想像的文學不是純粹壓倒意志的盲目感性力量:文學與公義,不是感性和理性,而是詩性和理性的彼此整調。根據作者的講法,文學作為人類美好生活的想像,即使與政治想像結合,也始終保持了與政治實體和策略實踐的某種超越性,從而使之在介入與糾正政治起了更不可或缺的重要使命。事實上,優秀的文學幫助我們學習把別人視同完整的人來看待,在過度昧於經濟角度的安定繁榮和功利主義,所謂理性對話、自我完善的政策改進中,可能正正缺乏這詩性同情而顯得胼手胝足。
文學必須保持一種自由的狀態
文學之追求自由,包括其獨立性及創作性。愈來愈多的集體性聲音,統一性表態;文學語言的獨立性、獨創性精神更為彌足珍貴。
正如諾貝爾獎得主賈西亞・馬奎斯(《百年孤寂》作者)說:「我曾參加過革命,幾乎被捕,可是作為一個作家,我要窮一生的精力,使我的作品證明一個目標,我要使文學與政治、社會,或者革命全然無關。」作家在社會感和政治感隨歷史的環境要求而逐漸加強,反而失去文化感——用現代的眼光對過去文化作獨立的反省和判斷。
在這語言貧乏,溝通能力薄弱的世代,詩是城市的呼吸,靈魂的窗口。真正的詩人之所以能夠沒有溝通的包袱,仍因為他知道人類對自己所設計的語言常常基於個人認知的限制而失焦滑落,詩用異於言表的震撼叫人解除只圖尋求溝通表層的疏懶,而要省思不同思想體系的關注。總得承認,有些文字,承載了我們還未完全可解的世界。所以文學必須保持一種自由自主的狀態,不能全然的社運型,而文學的公義性就在於她超越事件及時間。由是我想,在這個一直把文學邊緣化、甚至世俗化的藝術缺氧年代,特別需要文學的想像和詩性正義的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