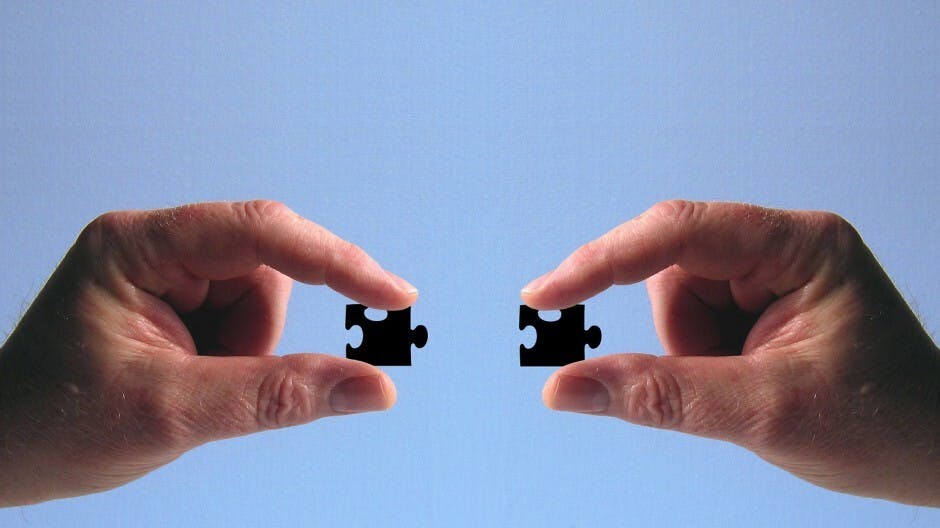歸納亞氏城邦「先於」個人的說法,有兩點值得討論。一是說他把個人「置於」國家之下,也就是說,他用國家壓抑個人。一是說他倡議「國家的有機論」。先說國家與個人。
亞氏有沒有把個人置於國家之下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他固然看國家「重於」個人,那倒不必然是用國家「壓抑」個人。試從目的次序看。假如國家的目的,在使個人能追求自己的目標,她的功能在保護每個人免受其他人傷害,那是把個人置於國家之上了;因為個人的行為,可以與國家無關。邏輯上,那是個人「先於」國家了。反過來說,如果個人活動,在追求集體目標,例如入伍服役,那個人是置於國家之下了。這是兩個極端的例子,還有兩者中間的不少可能。可是,個人可以同時追尋國家的與自己的目標——兩者不必互相排斥的,國家也可以成就個別公民的公眾與私人利益。這麼一來,就不能說誰的目的是「置於」誰之下了。亞氏的理論,正在這中間地帶。他顯然認為,城邦的目的,在全體公民的福樂。在《倫理學》中,他早有教誨:福樂,就是大家能追求智善和德善的生命,尤其在德善。德善牽涉的,是人與他人的關係;但那關係,並不只是公益的,或者說政治的。它可以牽上政治,但它也有家庭,友誼等非政治的層面。那樣的公民,不見得就只服務國家而沒有其他。他當然是生活在國家裡面,但他的生活並不全和政治體制有關。不過,甚麼叫美好的生活,得視乎人生目的是甚麼,又甚麼可滿足那目的:家庭?村落?城邦?人能追求沒有城邦的美好生活嗎?亞氏不是個個人主義者,他覺得大家應共同追求國家有和平,有富足,不是為了個人的福祉——雖然那福祉會因追求成功而來臨,而是為了國家本身。(在〈七卷〉有詳論。)即使如此,也不能就說,他把個人置於國家之下:兩者是互為依賴的。
話雖如此,在亞氏眼中,個人的益處,不及整體益處那麼重要。他的理論,是站在為政者角度發言的。他關注整體的命運,高於他看個別公民的出處,分屬自然。古代希臘的作者,並沒有強調個人自由與人權,也不強調國家有義務尊重每一個公民,因為他們是人。近代哲學使人的地位大大提高。近代思想,是個尊重個人權利的傳統。為了「大我」,希臘人寧可犧牲「小我」。正因為不強調個人,當集體和個人起衝突時,他們不覺得是犧牲了個人的自由、財產、地位等。從這個角度看,你可以說亞氏是把個人置於國家之下的,因為他以公益先行。可那也不是柏氏亞氏的「專制」思想。雅典民主,有放逐制:大家認為不受歡迎的人,可不經審訊就驅逐出境一段時間。這是大眾可以不尊重個人的典型例子。
另一個情況牽涉上的,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問題。如果成就個人目標的所有權力,全握在國家手裡,不讓個人有自由去追求他自己選擇的目標的話,那也是置個人於國家之下了。這近似我們說的集權或家長式統治;在某情況下,亞氏也有同一想法。他認為,要使人人能過美好的生活,要通過大眾在議會公開辯論後的立法,用國家之力去教育人民;這沒有留多少空間給人自己選擇。但就是今天文明社會吧,我們不也做着同樣的事情?全民教育,是國家強制施行的,所以又叫強迫教育。個人沒有權利不送子女上學。在同一事上,我們也沒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是亞氏進步了,還是我們退步了?可見個人/集體問題,在亞氏的理論中,沒有簡單答案。我們要看過整個理論才好下判語,切忌斷章取義來解釋他的哲學。
「國家的有機論」,該是從“Organic Theory of the State”譯過來的;我國傳統政論,並沒有這個叫法。意思是用生物體(或有機體)的運作,來比喻國家,來了解她的組成。亞氏是個生物學家,受過醫學訓練,曾從事海洋生物研究;他的《倫理學》和《政治學》,充斥着生物學的例子。在書中不難看到,他的用語往往「素描」城邦像個生物體,下分不同部分,各部功能互補,使整體活得更好。這不過是說,社會需要某種分工來配合發展;那不只「有機論」,持「機械論」的人,也有同樣見解。這兩類國家論,有時也可比作上文提到的,通體社會與聯組社會之別。亞氏傾向前者,因為他看城邦像個社區,像個緊湊的團體;價值取向是整體的公益,不是個別公民的目標。這樣看,他的學說較近「有機論」。
產物的自然協作和演變
任何有機體,都是自然的產物,都從演變而來。國家,也是一樣。演變,需時,也有步驟。這又有兩類說法。一是認為全面急劇改變是不可能的,因為社會並不是一張白紙,下一步的出現,總留有上一步的「遺產」。人總受到上一步的影響,因而改變的條件也受到限制。強行之,則只會出禍。這是日後貝爾克(E. Burke)給法國大革命下的評語。另一說法也依從這前提,但得出的結論是:一切刻意改變的努力都不好,也徒勞。亞氏的思想偏向「保守」,那是事實。光看他的「法律改革」見解,會給人印象他不贊成改變的。他很清楚知道,教育和傳統,對社會能有多大影響。可他仍然覺得,只要設計得宜,大家還是能夠建立美好的國度的。那是他理想主義的一面,儘管他對烏托邦不感興趣。這樣看,他的學說又不像有機論。
這個問題,也可以有另一個層面。我們說有機的(organic),是指向有機體(organism)的特性;亞氏說的,並不專指這個。在生物學上, organ 是器官;但 organ 有多解,像部門,機構,組織,工具等都是。他用的原字是 organon ,指的是工具。(十七世紀初,培根的名著 The New Organon ,中譯就叫《新工具》。這裡叫作工具的,老子謂之「器」。)工具,是助人達成某目的的。有點像說,器官,是助人體某種功能,配合整個身體的。例如,恰度的財富,是成就美好生活的工具;小刀,是家中的死物工具;奴隸,是家中的生物工具。工具,就受到目的的限制,也就是受到用途的限制。汽車,是馬路上行走的工具;它不可能太大,也不可太小,才能恰當地發揮功能。工具跟動植物一樣,只當有一定大小,好配合本身用來達成的目的。如果說城邦也是個 organ ,她也有同樣的限制。
那麼國家就不是個工具(或器官)了,她不是用來達到本身以外目的的東西。她本身不是工具;但有沒有可能說,她是個系統,包含了不同的工具共同運作,以達到她本身的目的?這樣的概念,倒符合亞氏目的論觀念的,同時也扯上了兩個相關要點:一是剛提到,系統中各不同工具(器官)的互補分工,一是各器官都依賴整個系統配合着運作。從社團角度說,不同部門合作,共同實踐的,是社團(國家)的目的。還有,社團的成員,都得參與在她的活動上,才能有個完全的、自我完成的生命。所以系統,是不可或缺的。合起來,我們說,國家是個系統,由不同部門組成,每個部門都依賴整體,否則生命不能完滿。也等於說,每個人都要依賴國家,才能有完整的生活。這多少可以從日常生活印證。每個人都必須生活在群體中;單獨的人,活在孤島,那「人」的意義就沒有了。所以沒有「星期五」的出現,魯賓遜早就不成故事。固然,你可以活,但那不是完整的生活。不和其他人分工合作,你只能像個隱士,不能是個社會成員,或國家公民。
說人得依賴群體,才能好好的活,大致上可以。但說人要絕對依賴國家而活,就不同了。亞氏用的比喻,是人沒有了國家這個社團,不能自足,好比器官脫離了身體不能獨存。手足就是明例。他是假定了個人對公眾的依賴,與手足對身體的依賴無異。手足之為手足,因為他的活動,他的功能,必須和身體配合,也只能是身體活動的一環。但個人呢?他的活動,必須和國家配合?只能是公眾(政治)活動的一環而無他?我們在後面會見到,他用有機式的生物術語作類比,應用到公民與非公民身上;前者屬於身體的「組成部分」,後者,只是必須具備的「輔助部分」;組成部分的生命,是身體一環;輔助部分,只是條件,並不屬身體的有機器官。組成的組件,像手與足;條件的組件,像血液與骨骼。在政治生活中,組成部分是公民,輔助部分是商人、百工、奴隸等。他的界線分明:犧牲後者(非公民)個人利益,為要追求前者(公民)個人福祉,而那福祉,後者是無從享有的。
那樣的目的論,是把有機論推到一個極端的位置上。社會成員的功能,不只在價值上分等級,更使某些功能成為另一些功能的工具。就放開這個極端的例子吧,亞氏論個人與國家的一些有機觀,也值得檢討;因為,使個人與國家像器官與身體,完全無可分離,那個人只能有公民身份而無其他,只能有政治活動而無其他。那不正是他批評柏氏的?他清楚知道,人有自愛(philautia)的本性,這本性也要表達出來。人除了政治生活外,還有其他層面的生活;在「多元」社會,人隨了屬於國家這個生物體,也屬於其他生物體。假如人只能是個公民而無他,那他在〈三卷〉中判別開「好人」與「好公民」,就毫無意義了。說他強調人的群性則可,說他要除掉人的個性則不可。所以他的理論,並非全面的有機論:他知道國家對個人生活的重要,他沒有使國家淹沒個人。如果認為,國家是個有機體,而有機體的成長,是個自然過程,像現代人說的——不經人手,那也不全符合他的想法。人為的努力,有重要角色。人,固然要與他人共存,但人相互合作、相互依賴,正因為人希望尋求自己的「獨立」:人的自主自足。
(圖片: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