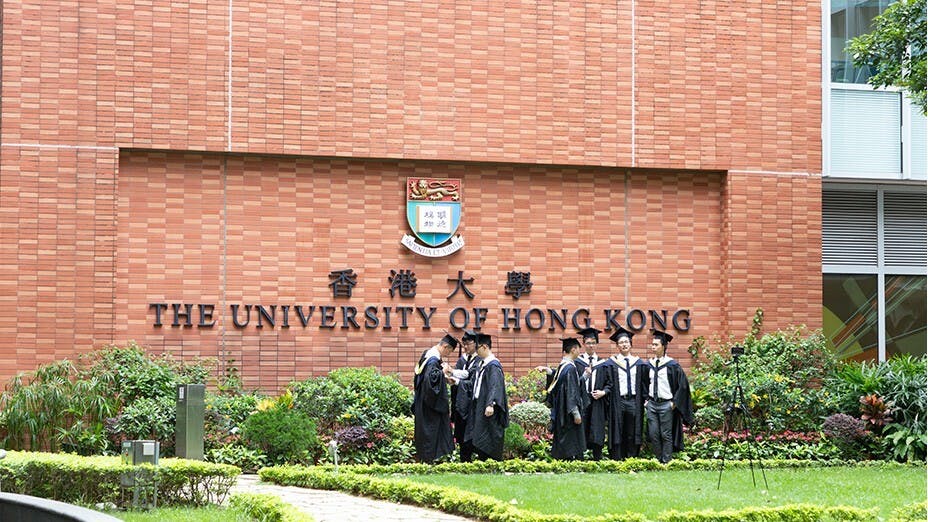上周提到學校對學生的影響,往往是由於學校的氛圍與文化。教師上課,都是經過勤奮的備課,審慎的設計;學生因而獲得課程規定的知識,通過嚴格的公開考試,獲得社會或者大學需要的入場券。對此,學生會感恩學校和教師的努力。但是,課程和考試規定的知識,在進入社會或者大學以後,也許很快就忘記了,有些人甚至拋掉所有用過的課本,告別了。但是學校和教師在學生生命中留下的印記,卻往往在幾十年後仍然深刻。那是教師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學校處事的每一個細節、每一種活動,也許不是非常刻意的,卻都在影響着學生──如何看周圍的事物、如何看周圍的人、如何看社會、如何看自己。所以說,教育所做的,是點亮了學生的生命!
大學空間,一生難再有!
上述主要是講中小學。大學又如何?筆者心裏的概念,大學已經不同中小學,已經是社會的一部分。有些社會還把大學看成是中小學,以為大學也靠規範的過程,在塑造未來的「人才」。這裏暫且不去評論中小學是否過分規範,但是大學的功能基本上是把學生釋放出來,讓他們做好準備,去面對多元燦爛的未來。一向如此。如今面對變幻莫測的前程,更加應該如此。否則,大學就是沒有盡他們的責任。
那麼,我們知道大學是如何影響學生的嗎?筆者曾經和港大的團隊,為港大的90周年校慶,出過一本紀念冊(Growing with Hong Kong,裏面記錄了一千多位港大校友的事跡和照片。這些大致都是事業有成的人物,也可以從側面看到大學的作用。不過,第一,這其實是一本名人錄,不包括港大畢業生的整個光譜;第二,對於每一位人物,只是片言隻語,並沒有說清楚他們走過的生活歷程,因此也沒有記載他們是如何成為成功人士的。

不過,也可以提供不少的啟示,但要聯繫到當年的大學生活。筆者1963年入讀港大,同屆同學之中,其實大都來自中等偏下收入的家庭。當時大學已經有助學金(簡稱bursary)。稍後,1969年開始,有政府大量的助學金與貸款,大學生更多來自中下收入家庭。他們畢業之後,不少成為社會翹楚。王賡武校長說過,那年代,大學就像是科舉,成為社會上升的主要階梯。有一點值得深思:當年除了一年級、三年級(畢業)各考一次試以外,再也沒有考試。二年級是Honeymoon Year(蜜月年),是學生一生難得的一個窗口,課外和校外的活動非常頻繁,參加校內社團、校外社會活動的機會很多。造就了思想開放的香港第一代公民社會,在當時是一種推動社會的積極力量。但又沒有影響學術成就,不少在大學非常活躍的學生,後來成為了世界知名的科學家、學者。而其他行業一些知名人士也是在這種氛圍下成長的。
筆者在1987年至2005年當了18年的舍監。1987年,跨越了「火紅」的1970年代。筆者當舍監的明原堂,正是1970年代學生運動的大本營,「認中關社」的口號,養成了後來分別着重「認中」與「關社」的社會意識派別。不管政治取向如何,他們紛紛成為了社會的領袖人物。對筆者的啟示,大學釋放了學生的潛能,讓他們形成了自己的意識形態;但卻沒有可能控制他們形成怎樣的意識形態。他們形成的各種意識形態正好反映了社會上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他們在許多方面起了先鋒的作用,但也其實是反映了社會前進的現實。
1992年,筆者轉到新成立的利希慎堂當舍監,社會氣候已經很不一樣。沒有了濃郁的政治氣氛。但是仍然保存着很強的傳統──非常認真的「迎新」程式、日以繼夜的各類課外活動。一個372人的宿舍,卻有大大小小大約100個各式組織,包括體育隊伍、音樂藝術組織、其他文化的、宗教的、公益的團體,還有每一層樓(每條村)的內部活動。但是幾乎完全沒有了政治話語;代替的是對於前途的討論、對於自己的認識,反正宿舍的生活很繁忙,不少活動半夜凌晨才剛剛開始,午餐當作早餐。這些授課教師和家長認為大逆不道的,當年的宿生回憶起來,卻是津津樂道。並非故意任性,這些豐富的生活經歷影響着他們一生的走向。沒有這些經歷,他們的一生會很不一樣。然而,在大學的這種經歷,一生中很難再重複。
去年,筆者的舊同事徐詠璇寫了一本《由薄扶林出發:港大新生代50築夢方程式》,算是少有的描述畢業生走過的歷程和心路。雖然都只是成功的青年畢業生,就不只是寫他們的成功,而且有了一個時間的維度,描繪了他們個人演化的過程。記載了在後工業社會,面對變幻多端的社會,年輕大學畢業生多姿多采的生命。這是新時代的寫照。他們不再是在巨型大機構中尋求平步青雲,而是經過頗為艱辛的歷程,經過輾轉曲折的路途,有些經歷了不同的行業,卻築成了自己的夢!

後生可畏,超越上一代!
書中第一位記載的王雷(Bruce),當年是太古學者(Swire Scholar),得到太古集團的助學金,念博士期間,住在大學的學術賓館柏立基學院。筆者在2005年至2015年忝為院長,認識了這一位言語不多的年輕學者。書中有這麼一段話:「住在古色古香的港大柏立基學院,經常有機會跟全球最頂尖的訪問學者,甚至是諾貝爾獎得主交流,聽對方分享做學術、做研究的心得,獲得很多啟發。」
最近有機會與他相聚,他就不斷談到在柏立基學院打開的眼界。這是筆者沒有預計到的。筆者在學院每天早餐,接觸的人都是學術的精英,有些還是每年到訪入住的,沒有想到會對年輕的博士生影響如此之大。而當時的10位太古學者又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博士生,互相在拓寬着各自的世界視野。
他畢業後在大疆研發無人機的電池。後來自己創業,專心研發「閃充」,也就是用最短時間的充電,提供最大能量的儲電。而他專注的是太陽能充電。數年前,應該是他創業初期,他帶了一座流動電能站(Power Station),估計是他「閃充」原型,來訪。他當時正在打開美國市場,露營車用戶是一大市場。但是他心裏想的是,如何用於完全沒有電源的發展中地區,例如非洲沙漠。筆者深為感動。
是看到了那本書,才知道王雷已經登上了儲能專業的頂峰,2017年才創業,但他在世界上已經很有地位。這裏且不去提他得到的財富與獎譽,但他念念不忘的是人們的需要。他的捐贈,包括鄭州的水災、美國得州的風災、日本的地震;而且在疫情期間,公司陷入困境的時候,毫不猶豫地把產品庫存全部捐給了武漢。
最近見到他,是他的領導班子元旦到香港度假。筆者獲邀與他們交流,話題竟是關於孩子們的教育。一家科技公司,都是技術的專業精英,他想到的卻是員工的家庭生活。在悉心鑽研技術的老闆之中,也許不多見。
這裏拿出王雷的例子,是因為他給了筆者非常深刻的啟示。大學教育就是開拓學生的頭腦。在王雷身上,第一當然是專業知識,那是他事業的基礎;第二是廣闊的眼界,找到了創新突破的視窗;第三是關愛的素養,心裏懷着人們的災難與需要。但是更重要的一點:這些知識、眼界、素養,學生不是被動的接受者,他們也在這些方面不斷發展與提升。他們不只是傳承,而是在創造未來,可以遠遠超過我們上一代。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