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瑞典學院把諾貝爾文學獎頒了給一個「小作家」(minor writer)。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Annie Ernaux)的「小」不是指她的才情,而在於她的眼界和視野。不管時代和世界有多大,她關心的只是小小的自我(self)。與其說她的作品自傳色彩濃厚(autobiographical),倒不如說它們自我中心(self-centered)和只關心作者自己(self-interested)。在這個意義上,埃爾諾繼承和發揚光大的傳統是將「看自己的肚臍眼」(naval-gazing,即自我沉溺)提升為一種藝術。
科萊特和杜拉斯的影響
這是法國文學的光輝傳統。這個傳統的「庸俗版」(lowbrow version)代表是莎岡(Francois Sagan),她19歲發表的《日安憂鬱》(Bonjour Tristesse)向全球渴望成名但生活經驗貧乏的寫作人,示範如何以「無病呻吟」和「為賦新詞強說愁」引起共鳴。這本書的巨大成功啟發了30年後的「我一代」(Me Generation)和今日社交媒體的網紅。
「嚴肅版」(highbrow version)的代表是科萊特(Colette)和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科萊特是法國20世紀上半葉的作家,卒於《日安憂鬱》面世之年。她的成名作《切里》(Cheri)極有可能是埃爾諾的兩部小說《簡單的激情》(Simple Passion)與《迷失》(Getting Lost)的啟發甚至參照,3部小說的主題都是女人的「性違法」(sexual transgression)──她們的性行為和性關係如何僭越道德和法律。《切里》的男主角已婚,25歲,與一個49歲的女子離離合合、難捨難分。《簡單的激情》與《迷失》講的是同一類關係、同一類故事:20多年前,年近50的埃爾諾搭上一個30多歲的蘇聯外交官。二人整天整晚做愛,不知人間何世。
杜拉斯對埃爾諾的影響更顯而易見。杜拉斯的《情人》(The Lover)也在年齡差距這個話題上大造文章:15歲的法國窮家女在越南與一個30多歲的中國男人發展不倫關係。杜拉斯對愛情以至生命的悲劇意識(tragic consciousness)是法國文壇的一套「天氣系統」(weather system),當地的作家很少能夠不受影響。《情人》很多刻骨銘心的句子,都陰魂不散地在《迷失》出現。《情人》的讀者怎會忘記「老早已太晚,這是我的人生」(Very early in my life it was too late)這樣價值連城的句子?埃爾諾不是杜拉斯,但「下次相聚的日期就是我的前途」(I have no future, other than the date of our next meeting)也確實令人心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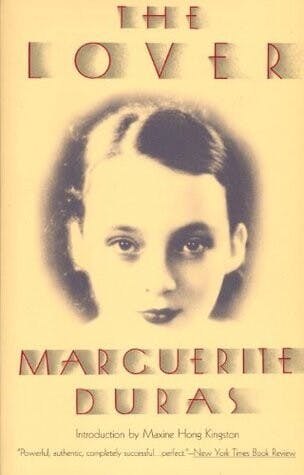
試圖糾正性別不平等
「透過年輕的肉體尋回生趣」(Young flesh as renewal),是男性作家的偏愛和樂此不疲的主題。隨便舉個例,4年前離世的美國小說家羅夫(Philip Roth)生前是個無(少)女不歡的男人,他筆下的男人也總是沒法按捺他們對年輕女人的性幻想和性慾望。對羅夫來說,這等同於對生命的熱情。然而,只要把老少戀中男女的年紀互換,「透過年輕的肉體尋回生趣」馬上變成「透過年輕的肉體摧毀天真」(Young flesh as corrupting innocence)。年長的女性是要吃唐僧肉的妖怪,通俗文化中最著名的例子是電影《畢業生》(The Graduate)的魯賓遜太太(Mrs. Robinson)。她不但像玩木偶一樣把入世未深的男主角弄上床,還千方百計要破壞他與女兒的純潔愛情。
從這個角度看,埃爾諾的小說試圖對文學世界的性別不平等(gender inequality)糾正改錯和撥亂反正。這也許就是她獲瑞典學院垂青的原因:因性侵醜聞曾停辦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急於向世界證明它對性別不平等的「零容忍」。文學創作和欣賞並非在與世隔絕的真空中進行,文學被賦予的價值受到很多文學以外的因素影響。更何況瑞典學院喜歡借得獎者表態,例如今年把和平獎頒予俄烏及白俄人權組織,就是擺明要令俄羅斯總統普京難看。和平獎可以這樣做,文學獎當然也可以,分別只是露骨的程度而已。
這不是說埃爾諾浪得虛名。2004年,同樣善於寫女性出軌的奧地利作家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獲諾貝爾文學獎。若論作品的「嚇人值」(shock value),埃爾諾遠不如耶利內克。耶利內克最多人認識的小說《鋼琴教師》(The Piano Teacher)令衛道之士大發雷霆、紳士淑女面紅耳赤,因為它不僅充斥着性,還是強迫的性、變態的性和沒有一絲感情聯繫的性。女主角不是性解放者,而是性急救者,試圖用性虐待來克服自己病入膏肓的性冷感。於是,綁縛與調教、施虐與受虐(簡稱BDSM)變成醫治奄奄一息的性的「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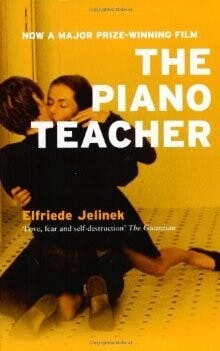
事實的金石聲
埃爾諾的作品有大量的性描寫,但多是熾烈而不露骨(intense but not explicit)。她的新作《迷失》最令人忘不了的,不是跟性有關的種種偏差行為(deviant sex),而是那些發出「事實的金石聲」(the ring of truth,張愛玲譯法)的細節,例如在情人的陽具上找到自己遺失了的隱形眼鏡。埃爾諾是小說家,但她在情感上的誠實(emotional honesty)以及對細節的掌握,令她更勝任做「日記作者」(diarist),《迷失》的「日誌式」結構(diary entry)可以說是讓她盡展所長。
埃爾諾其實有兩個情人,一個會跟她做愛,另一個不會,但永遠不會因她年老色衰而離她而去。埃爾諾這樣寫:「我有點害怕,害怕自己日漸衰老,終有一天會被取消資格,不能再玩做愛這個遊戲。在生命這個荒涼小鎮,做愛是唯一好玩的遊戲,除了寫作。」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一個如此相信寫作的人,總是好事。至少不會是「我本將心寄明月,無奈明月照溝渠」。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