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屆諾貝爾文學獎頒予坦桑尼亞小說家阿卜杜勒拉薩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記者問我的看法。我告訴她,不但沒有讀過此人的作品,連他的名字也是第一次聽到。
這當然是我孤陋寡聞,但文學世界之大,每人必有其未曾踏足之地。更何況最大的文學獎也保證不到文學價值,甚至可以說文學獎根本是個矛盾詞(oxymoron)。”Oxymoron”由古希臘語的「聰明」(oxys)與「笨伯」(moron)構成,本身就是矛盾修辭法的應用示範。
文學與獎是天生的怨偶
文學與獎格格不入,是天生的怨偶。撫慰寂寞人的傷心和傷心人的寂寞,彌補生命的遺憾與充滿遺憾的生命,是文學的初心。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是給在生命中拿不到獎的人(Literature is for those who fail to get the prize in life)。這是文學獎的深層次矛盾,愈是花團錦簇、金堆玉砌的文學獎愈違背文學的初心。
很多人當諾貝爾文學獎是指路明燈,像跟着《米芝蓮指南》尋找美食般閱讀得獎作家的作品。問題是抱這種趨炎附勢、人云亦云和服膺權威的心態接觸文學不但無法親近文學,反而與文學疏遠。書與讀者的關係是私交,也是兩個腦袋和心靈相遇,與他人的喜惡和評價無關。一本書可以改變一個人,這是它可以得到最珍貴的獎項。
新書《文學與蛻變:改寫生命的閱讀經驗》(Literature And Transformation: A narrative study of life-changing reading experiences)讓讀者自述他們深愛的書如何「令其心有所感」(make them feel things)。
這其實是文學的原始功能,「讀書治療」(bibliotherapy)一詞在20世紀初開始使用,但書可養生療傷這概念早已有之。史上首座圖書館由古埃及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Pharaoh Ramses II)下令建造,據說入口有這句提辭:「此乃精神治療之所」(this is the house of healing for the sou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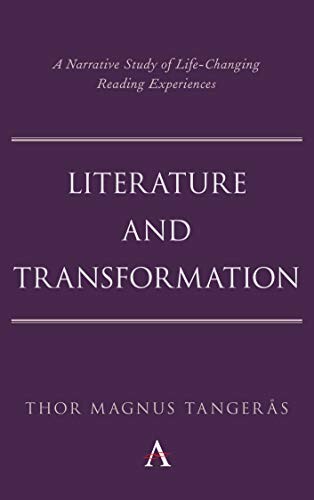
作家偉大,不是因為他們登上文學獎的殿堂,而是因為進入了我們的人生和佔據了我們的心靈。據聞海豹能夠在黑夜游過無邊無際、亦無標記可以辨識的大海,全靠星光引路。偉大的作家放在一起,組成的是一個類似銀河的繁星系統,而讀者就是海豹。那諾貝爾文學獎是什麼?什麼也不是。
最佳者往往不會勝出的遊戲
我一直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毋須太認真看待。這不是故作驚人之語而是常識:不管是諾貝爾還是布克獎(Booker Prize,每年頒予用英文寫成並在英國出版的最佳原創小說),文學獎不是奧林匹克運動會一類優勝劣敗的競技場。最後誰人得獎,我們不應抱「願最佳者勝出」(May the Best Man win)的美好願望。
只要看看歷屆的得獎者名單,就會發現這是「最佳者往往不會勝出」的遊戲。托爾斯泰(Tolstoy)、普魯斯特(Proust)、喬伊斯(Joyce)、納波可夫(Nabokov)、奧登(Auden)和博爾赫斯(Borges)不需要諾貝爾文學獎為他們錦上添花,但口口聲聲說要對偉大作家的終生成就予以表揚的諾貝爾文學獎怎能自圓其說?
近年,它把文學獎先後頒給德國女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ueller)、白俄羅斯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和美國搖滾樂唱作人鮑勃.迪倫(Bob Dylan),已把所餘無幾的公信力糟蹋在自己「與世隔絕」的文學品味。
這也難怪,文學上的最佳並非可驗證的客觀事實(verifiable truth),更何況諾獎的主辦單位瑞典學院不見得真正懂得世界文學。不管是在理論還是創作的層面,瑞典文學只是世界文學的旁枝末流。瑞典文學院諸公要充當世界文學的終審裁判和品味判官,明明力所不及卻要勉為其難,怎能不在水深處沒頂(out of its depth)?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