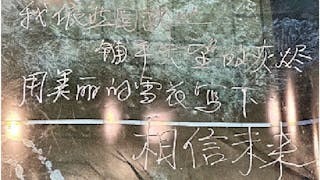序 曲
認識高世章(Leon),當然從他的音樂作品開始。假若你是香港音樂劇迷,對他的名字,應該不會感到陌生。
於我來說,除了音樂劇《四川好人》、《頂頭鎚》、《一屋寶貝》……,最難忘的,竟然是在2010年的「尋香記」,他辦的一個古董香水瓶展覽,那份驚豔,至今縈繞心頭。
料不到,十年之後,我們竟然可以面對面,暢談了五個小時。
最近,他策劃的原創音樂劇音樂會《我們的音樂劇》上演完畢,剛好有一個空檔,可以接受訪問。
微雨中,我打着傘,沿着灣仔告士打道,匆匆走到他的工作室。
我們從他學琴的開始聊起,從流行曲、音樂劇……還談到香水瓶,好愜意!
愛上音樂,6歲那年的夏天
記得當時年紀小,高世章6歲,開始學琴,「那一年的夏天,我們全家人去美國旅行,探望住在加州的舅父。在他們的客廳中,有一座鋼琴,每天都聽到琴音流瀉而出,「是Chopin的waltz,我好喜歡,於是便請表姐教我彈琴,我連樂譜也不懂得看,就逐個音在琴鍵上彈出來……」
那一個夏天,對他非常重要,幾個家庭自駕遊,在美國西岸一帶,暢遊了兩個月。而且,在表姐指導下,他學會看譜。
回港後,他懇求父母添置一部鋼琴,「我上鋼琴課,才可使用家裏的琴練習,平日不能隨意亂碰。」他對每件事的認真和尊重,相信是自小受父母影響。
他愛上彈琴,「不過,我不喜歡彈scale,只想跳過一些基本訓練,彈自己喜歡的樂曲,模仿指法,拚命去練……」高世章坦言,從沒想過將來當鋼琴家,也不想鑽研技巧,因為鋼琴老師建議,才去考取第五級文憑。
「我不想當演奏家,也不愛幕前演出,一來害怕給spotlight照着,也不想別人在背後說三道四。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做演奏家,但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觀眾緣……」他生於演藝世家,母親尤敏是第一屆金馬影后,外祖父是粵劇名伶白玉堂,伯娘是演過《星星、月亮、太陽》的葛蘭。「無論逛街、吃飯,還是坐飛機,總有人走過來say hello,令我感到有點尷尬。」

他在香港華仁念書,成績一向很好,高中時選讀理科,最喜歡化學,「我覺得念理科對我的創作,大有幫助,那是一種思維的訓練,作曲時的計算、結構、組合都用得着。」
「80年代的中後期,香港的年輕人,不是聽粵語流行曲,便是日本歌。音樂無疆界,我什麼歌曲都聽,好奇心特別大,什麼都想認識,反而到現在,不想知道那麼多,因為時間實在太少。」他微微一笑,繼續說下去。
早在1989年,他開始寫流行曲。「黎小田當時在『華星』工作,這個Uncle很好,叫我寫一首歌,『就當寫給甄妮吧!』我非常緊張,幾乎不眠不休……」他第一首作品是《無力再戀》,歌手是譚耀文,也給劉德華寫了三、四首歌,如《末世天使》。
情迷紐約,專攻音樂劇創作
讀完中六後,高世章便飛往芝加哥的西北大學念書,他想讀音樂,父母卻不同意,勸他把音樂視為興趣,「若作為職業,恐怕將來難以維生……」然而,他有自己的堅持。
面對大學新生活,他感到非常雀躍,「在第一年,什麼科目也take,社會學、音樂、電腦、文學、法文……到第二年,才選擇主修音樂,主修作曲,雖然不主修演奏,但鋼琴老師仍然願意收我為學生。」他覺得學琴好重要,直到大學三年級才停下來。
他念的是正統音樂,西北大學也有音樂劇的表演課程,「學校每年都有Variety Show,除了三年級,我每年都寫歌,也曾在音樂劇中彈琴,畢業後還有繼續為母校寫曲。」
大學畢業後,他發現紐約大學設有音樂劇碩士課程,「當時掙扎着,究竟留在芝加哥學指揮?還是赴紐約學音樂劇?」音樂世界浩翰無涯,但他偏對音樂劇情有獨鍾,於是決定趁年輕到紐約闖蕩一番。音樂劇之所以吸引,就是能讓他把學過的一切,無論是古典音樂、歌劇、流行曲……從通俗的到嚴肅的歌曲等,都可共冶一爐。

選讀音樂劇,緣起中學時代,他偶然看了一個Tony Award音樂節目,「當時聽了The Phantom of the Opera(《歌聲魅影》)中的Music Of the Night,它介乎流行音樂與古典音樂之間,我覺得很吸引……」這首歌將他引進音樂劇的世界。
「音樂劇,最初在綜藝表演中出現,慢慢發展成為有劇情、有社會議題的作品,甚至給觀眾帶來衝擊、反思,不單止唱唱歌、跳跳舞便算了。」他拈出《夢斷城西》為例,故事改編自莎士比亞的愛情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內容充滿了現實與諷刺的意味,反映出戰後美國社會隱藏的種種問題,如種族歧視、青少年犯罪、暴力等。
至《歌聲魅影》,已沒有對白,是Sung through。「有些人以為,由頭唱到落尾,才是音樂劇。其實,真正好的作品,不用唱太多歌,在適當的時候才插入歌曲。」恰到好處,才是優秀之作。
「那個年代,人人說的,總離不開The Phantom of the Opera、Cats……生活在香港,大多只看過這幾齣流行作品,全是大製作,他們的市場推廣,實在做得很好。」音樂劇雖然商業化,但有些經典之作,也可留名青史,如Les Misérables(《悲慘世界》)!
高世章到到美國讀音樂之後,才知道世界之大,優秀的作品甚多,其實音樂劇的黃金歲月,是在四、五十年代。那時的Book Musical,既有音樂,也有劇本和歌詞。
當時最著名的組合,莫過於Rodgers and Hammerstein,Richard Rodgers作曲,Oscar Hammerstein寫劇本和歌詞,他們創作的音樂劇如Oklahoma!(1943)、Carousel (1945)、South Pacific(1950),奠定了音樂劇的地位,既富娛樂性,亦非常流行。
「直到我學習寫音樂劇時,才懂得拆骨剝皮,研究箇中技巧。」他強調,如何寫好一齣音樂劇,就要向這幾齣經典學習。他回到香港後,寫了幾個大型歌劇,都是朝着Book Musical的路線而創作的。
Heading East,不同文化的衝擊
紐約可以說是一個音樂劇城市,在百老匯,可以看到所有的演出,好的壞的,式式俱備,可謂大開眼界。
「紐約對個人的刺激很大,我本來沒想過放棄那邊的發展,紐約就是紐約,氛圍很重要。這個城市的節奏,對我的影響很深,我認為節奏對作曲很重要。」高世章在紐約生活了15年,原先也想留在美國發展,在紐約、香港兩邊走,後來才於2008年回流香港,為香港的音樂領域作出貢獻。
家人雖從事演藝事業,他坦言對自己影響不大,「我正式投身這一行,背後沒有甚麼支持,況且他們做幕前,我則寫音樂,是兩碼子的事。」紐約有太多人寫音樂劇,在當地發展,起步有點困難,他像很多年輕人一樣,也曾經歷過迷茫、挫折,但發展尚算平穩。
在NYU畢業後,1998年,他寫了Heading East這個音樂劇,巡迴演出兩年,至2001年,才在紐約獲得”Richard Rodgers Development Award”。
Heading East(1998)是一個慶祝加州成立150周年的音樂劇,「我與同學Robert Lee合作,我作曲、他填詞……」說的是一個加州華人的故事,刻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主角在1848年來到加州,活了150年,在劇中,他自報家門:「我在這裏時,所有亞裔人還未來,其後日本、韓國、菲律賓人都來了,我本來可以揚名立萬,但因為他們,阻礙我的發展……」不同文化的衝擊,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古天農看了Heading East的錄像,便找我合作。」2002年,他為中英劇團的《咖喱盆菜釀薯條》譜寫音樂。故事講述新界一位原居民鄧先生,在錦田經營一所尼泊爾餐廳,在飲食業的低潮中,聯同從英國歸來的兒子,以及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菲律賓和尼泊爾員工,挽救面臨倒閉的餐廳……是個跨文化的原創劇。

《四川好人》,形神俱備示範作
高世章為香港創作的第一個粵語音樂劇是《四川好人》,改編自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同名劇作。2002年,演戲家族的彭鎮南來紐約,找他為音樂劇《四川好人》作曲。
「我剛巧看過原著劇本,再三考慮後,覺得可以嘗試一下。」當時,他仍未認識岑偉宗,但霑叔(黃霑)曾向他推介,說岑偉宗填詞不錯。自此,兩人合作無間,金牌組合因而誕生。

彭鎮南、高世章和岑偉宗先把故事改編為音樂劇,然後由高世章作曲、岑偉宗填詞,為此劇創作了多首動聽的歌曲,導演則為彭鎮南。
《四川好人》於2003年首演,五場座無虛設,並於香港舞台劇獎橫掃六大獎項。其後於2004、2011及2020年重演,亦好評如潮。
鄧正健於2003年觀劇後,稱《四川好人》「形神俱備」,而陳國慧於2011年亦撰文論述,「專攻音樂劇創作的高世章對形式的專業掌握,無疑為本土音樂劇的創作帶來生氣;《四川》儼如『示範之作』」。

闊別八年後,香港話劇團與「演戲家族」合作,去年又以嶄新元素復排這齣經典。「俚語的使用,對原文本的轉移恰如其分,將舞台拉近到觀眾生活之餘,又多了幾分詼諧的亮點。」評論點出了此劇的本土色彩。這個版本,跟多年前的演出已不同。
談起這個音樂劇,高世章說:「在2003年的原版,我已經將自己的所學全部傾注其中。」

他記得黎小田曾提醒他,「千萬不要將所有懂得的東西,全部放在一首作品中。」他皺起眉頭,繼續說下去,「但初出茅廬的人,無論寫流行曲或交響樂,都要『曬冷』,好像這就是自己的statement!《四川好人》多多少少也犯上這個毛病,雖然已經有人勸過我,但我仍然這樣做。」
「每次演出,我當然希望改得更好,不過,除非問題大至無法忍受,我才會大刀闊斧,否則會改得輕手一點。」他聳聳肩笑着說。
「我要考慮整體的音樂風格是什麼,也要研究30年代,在四川這窮鄉僻壤有什麼音樂。劇中有一個主角是飛機師,於是我嘗試放進一點點的Jazz,作為性格描寫。此外,還加入康定情歌、南音……」這齣音樂劇,可謂色彩繽紛。
高世章指出,將布萊希特的劇作,難以改編為音樂劇,他嘗試從劇本的內涵出發,「這個劇講的是正邪,道出好人與壞人之別,故此,音樂以兩種方式呈現,所有音樂都是兩部的,非此即彼……」
論及音樂創作,他說,「其實,『愈簡單的東西,就愈難寫』,黎小田忠告,我銘記於心。」對於這位前輩,他心存感激。

《頂頭鎚》,見證拚搏的精神
2006年,「演戲家族」以音樂劇《白蛇新傳》,揭開香港藝術節的序幕。高世章負責作曲編曲,「要為這個演出找出適當的調子,尤其困難;如何在現今世界中再現白娘子的『音』容,也實在不易……」創作時,他並沒有墨守成規,期待與觀眾分享劇中人峰迴路轉的經歷,此劇又為他帶來「最佳創作音樂」。
同年,他為任白慈善基金會主辦,「雛鳳」演出之粵劇《帝女花》譜寫新序曲及過場音樂。
2007年,他為香港舞蹈團歌舞劇《夢傳說》作曲,跟編劇杜國威合作。
到2008年,香港話劇團的音樂劇《頂頭鎚》公演。藝術總監陳敢權,在劇中重塑1936年一段被遺忘的歷史,講述「一個熱愛足球的小子,人窮志不窮,因緣際會下,被選入國家隊,遠赴柏林參加奧運。」
高世章早已認識陳敢權,但第一個合作的作品,便是《頂頭鎚》。「陳敢權剛好去紐約,將劇本給我看,一個地道的香港故事。」高世章為此劇作曲,讓大家看到踢着波、唱着歌的球員,在綠茵場上追逐理想,見證30年代香港的拚搏精神。
這個作品首演時,獲香港舞台劇獎四大獎項,包括最佳創作音樂。第三次重演是在2017年,與香港舞蹈團聯合製作,並首度配以現場樂隊伴奏。接着,便到北京的天橋藝術中心演出。
新建的天橋藝術中心很漂亮,不過地方比較偏遠。最初是為了交流,將香港的音樂劇介紹到北京,想不到,反響非常正面,評論一面倒讚好:「香港音樂劇,已經做到這個地步,我們有排追……」
「《頂頭鎚》的演員,如劉守正、王維、黃慧慈等,演技都很好,但完全沒有大明星坐鎮的音樂劇,竟得到這麼大迴響,我覺得好有意義。」作為香港人,高世章感到很自豪。
談到今日的舞台劇,有些人覺得廣東話太俗,不能登大雅之堂,「有人曾對我說,如果想攻佔大中華市場,為何不寫普通話?」但他認為廣東話是自己的母語,所以堅持用廣東話寫音樂劇。

「我最初寫的是英文音樂劇,英文無論雅俗,語言相近,中文卻截然不同,有書面語、口語……」合作《四川好人》時,他曾與拍檔岑偉宗討論過這些問題。「岑偉宗對廣東話好執着,我們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如何寫才能突破別人的偏見。」
「我寫音樂劇,角色需要用什麼語言,就用什麼語言,如果角色非常市井,一定不會出口成文。我的職責是寫一些deliverable的角色,如果按照這個方針去做,便不會走上歪路。不過,我會盡量避免粗口,主要是因為個人的美學觀點,而觀眾的反應,也教人莫名其妙,有人聽到粗口,反應好奇怪,大笑、拍手……」這也是他的執着。
《一屋寶貝》,最入心的音樂劇
為了實踐夢想,高世章當年,毅然放下剛起步的紐約事業,回港發展,寫下不少叫好叫座的舞台劇作,還參與多齣電影配樂,例如屢次獲獎的《如果.愛》,還有《老港正傳》、《投名狀》、《大魔術師》、《大上海》等。
「在電影中,音樂只是其中一部分,導演有話事權。當然,電影會令人知名度大增,因為媒介不同,如果我不為電影配樂,便不會贏到台灣金馬獎、香港電影金像獎……能夠得獎,無論是對自己的交代,又或者建立品牌,也是重要的,一個不見經傳的人,怎能讓別人對你有信心?」
對他來說,滿足感一定來自舞台,「音樂劇由我主導,雖然有其他的拍檔,但在音樂方面,沒有人可以告訴我,什麼是對或不對。」他引述岑偉宗說過的,「舞台是我的家;電影是旅行的地方。」旅行的地方,可以很美麗,也可以令人很開心,但是家才是他的歸宿。

在香港辦音樂劇,固然困難重重,但他仍然樂觀。「希望香港能憑着優勢,逐漸做到優質品牌。」
2009年的《一屋寶貝》,高世章再度與「演戲家族」合作,此劇改編自日本作家柳美里的小說《在雨和夢之後》,由彭鎮南導演、岑偉宗作詞、張飛帆編劇。
原著小說十分出色,以鬼故事討論親情,相當引人入勝。「如果不是《一屋寶貝》,沒有人會留意這個故事,真奇怪!直至我們將它發掘出來,大家才發現它如此精彩。」
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首演時,演了五場,高世章還在現場彈琴,台上台下都有交流。「有人認為這個版本最好看,在舞台上設有好多機關,突然之間,『有啲嘢係個窿』爬出來……好嚇人!」
《一屋寶貝》獲獎甚多,亦曾多次重演。在2014年,「演戲家族」與香港小交響樂團合作,在香港大會堂演出《一屋寶貝》,2016年則移師荃灣大會堂。「香港從來沒有一個音樂劇,以這種形式,在台上與真正的樂團合作演出。」在多齣音樂劇中,他自言最喜歡的是《一屋寶貝》,成功感也較多。
「我會嘗試在每一個劇內,注入一些新元素,我不會吝嗇take a risk,放進一些自己唔sure work唔work的東西……」在藝術上,他不想抄襲外國音樂劇用過的技巧。
「我喜歡用自己的方式去做音樂,例如在《四川好人》或《頂頭鎚》中,我放進一些南音。」他喜歡杜煥的南音,但會用自己的方式放在劇中,而不會令人覺得突兀。「南音的旋律,好似Stream of consciousness,只是敘事,無特別的曲式,但在音樂劇中,不可能放入這種的東西……」
於他而言,南音就像西方的Blues,「在《四川好人》中,有一班對生活毫無寄望的人,他們被生活打殘,為了生存,被迫走上歪路,縱使如此,亦可能被社會唾棄,在劇中放進南音,就比較合適。又如《頂頭鎚》,當一班街坊知道將會被迫遷,我也用南音去表達他們的憤懣,將攤檔用的東西,如筷子、菜刀、木枱敲擊,以作伴奏……這個新嘗試,比《四川好人》進化了。」談及音樂,高世章滔滔不絕的說起來。
在《一屋寶貝》,他也有新嘗試,「整體來說,在故事的起承轉合方面,做得比較好,可能因為我對這個故事感受很深,非常『貼肉』,《四川好人》比較疏離,而《一屋寶貝》則比較入心!」

在他心目中,每一齣音樂劇都是獨立的,好像一個新境界。「人家找我做音樂,要視乎題材,我才考慮去做。如果無感覺,未能處理到,我不會接受。搞藝術要有感覺,不是為了賺錢。我會花很多心機去做,費的時間也很長,如果我沒有信心,我未必願意去做。」
「十多廿年來,每寫一個劇,我都感到戰戰兢兢,我不一定知道怎樣做,也不確定怎樣做才最好,但我有信心——應該有辦法做得到。」他細細道出心聲。
本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