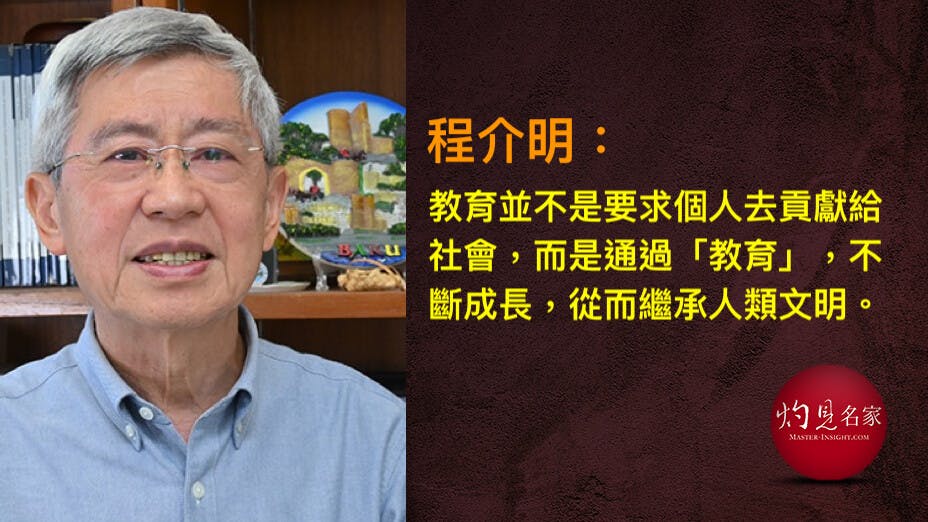上周談到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矛盾,提到1958年在內地的一種說法:「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發生矛盾時,應當服從集體利益;必要時,可以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去維護集體利益」。這種觀點,並非中國獨有。
於日本有深遠影響的明治天皇《教育勅語》(勅,漢語讀「赤」;粵音「斥」),針對當時因為革新而「西化」,教育傾向實用而忽略德育,非常精簡地提出德育的大綱(以後有機會再討論),小學生都要每天朗讀。裏面在日本最有爭議的一句:「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根據當年台灣總督府官定漢譯)「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就是說要犧牲個人利益,維護國家,最終「以扶翼皇運」。這份《教育勅語》,甚至影響到日本的殖民地韓國和台灣。1946年因為被認為是「軍國主義教典」而被終止,但是其中的德育內容仍然被保留。
現代一點,日本近年的教育改革,總的口號是「熱愛生活」(一曰「熱愛生命」,Zest for Life),第一條就是「為社會作出貢獻的實際能力」。是把為社會做出貢獻作為教育的目標,成為個人與社會的結合點。
手頭有一份新加坡大概2000年前後的英文文件,裏面講得很清楚:「基本上,教育是為了培養全面的人。」「但是離開了社會與國家,個人就無法生存。是總體的社會讓他可以通過自己的貢獻,分取他的一份地位與保障。」(筆者根據英文版翻譯)這是社會與個人關係的一種毫不含糊的闡釋。
服從國家 筷子文化
但是隨後的幾十年,可以看到新加坡的教育政策,從純粹的為國家,而逐漸加強個人因素。有研究者認為,新加坡的教育發展,分4個階段:生存(剛獨立國家的求存)、效率(講究篩選)、能力(適應個人能力)、素養(以全面育人為本)。新加坡的「21世紀素養」藍圖(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則教育目標在於培養4種人:Confident Person(自信的個人)、Self-directed Learner(自覺的學習者)、Active Contributor(主動的貢獻者),Concerned Citizen(有心的公民),就是兼顧國家、社會與個人。
而2016年發表的《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近年在中國內地教育界普遍採用的,則包括「自我管理」(學會學習、健康生活、成長規劃)、「文化修習」(人文底蘊、科學精神、審美情趣)、「社會參與」(社會責任、國家認同、國際理解),也是兼顧社會、國家與個人。
可以看到,在這些筷子文化的社會,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始終是教育目標的一個關鍵環節。凡是教育方針、教育目標的文件,都無可避免要把這個關係講清楚。
但這並不是每一個社會必然的。上述新加坡的「21世紀素養」,看來是受了美國「21世紀技能」(21st Century Skills)的啟發。細看之下,美國的「21世紀技能」,是以個人的工作表現作為框架,而與群體略為有關的,只有4C當中的「communication」(溝通能力)與「collaboration」(合作能力)兩項。沒有「向社會貢獻」,「做有心公民」的元素,雖則裏面提到的具體「技能」,新加坡與美國幾乎一樣。所以新加坡把skills改為competencies,一詞之差,絕非純粹的語義差別。是把實用主義的框架,改為人文主義的框架。
人文目標 東亞傳統
後來有機會參加台灣有關的討論,他們決定用「素養」,來演繹competencies。原因是,美國的competencies,都是人的外在表現,而在中華文化之中,教育更重要的是人的內在修養。這與本欄前數周提到的「克己」、「求諸己」、「修身」,是一脈相承的。在2016年同年發表的上述《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北京師範大學課題組)在中國內地引起廣泛的共鳴,其原因是一致的,普遍認為素養包括內涵。相信兩岸沒有經過溝通,可見其共同的文化底蘊。
美國的以個人能力作為教育的目標,其實也是一脈相承。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曾經是美國教育思想的先驅,被譽為「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的鼻祖(雖然他自己曾經表示不承認這樣的稱譽)。杜威1919年到訪中國,在中國逗留兩年多,對於中國自民國初期建立的學校系統,影響深遠。杜威是這樣表述社會與個人的關係:「我相信,所有教育的進展,都是由於個人參與人類的社會覺悟。這個過程幾乎在出生開始就不自覺地發生了,不斷地塑造個人的力量、滿足個人的知識、形成個人的習慣、訓練個人的思想,以及誘發個人的情感……通過這種不自覺的教育,個人逐漸開始分享人類為了成功聚居而(積累的)知識與道德資源。個人也就繼承了文明的豐富財產。」(根據筆者的理解翻譯)
這裏,教育並不是要求個人去貢獻給社會,而是通過「教育」,不斷成長,從而繼承人類文明。可以說,基本上教育是個人的事。本欄曾介紹過多次的美國麻省Sturbridge(過着1936年生活的歷史村落),問教師:「孩子為何要來上學?」答:「不就是為了要到波士頓打工,因此要學讀、寫、算。」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動力,學校就是為了工作需要而設。
雖然,就在這個村落(現在是旅遊點),買到一本《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是教孩子需要遵守的規矩,共108條。例如與大人上街,必須走在行人道的內側;在外面回到家裏,必須把鞋底刷乾淨;聽到老人家不斷重複同樣的故事,不許笑……可以說是如何處理孩子自己與家庭的關係,不涉及社會與國家。

戰略模糊 上下互動
但是美國教育也有她的掙扎。美國有幾次顯著的教育改革高潮。最出名的是1983年的A Nation at Risk。這是第一次把教育與國家連起來,引起了全國教育體系上上下下的反思。另一次是2002年小布殊總統簽署的No Child Left Behind法例(有人譯作「一個都不能少」),把注意力又回到學生身上;實際效果是引起全國的測驗潮。第三次沒有明文,出現在2010年,當中國的上海第一次在國際學生能力比較(PISA)嶄露頭角就獨佔鰲頭,引起美國朝野的震動。可以說,這些改革的浪頭,都是出於「美國不能輸」的不明文價值觀,沒有根本動搖教育的本質,沒有動搖「教育為個人」的基本假設。
倒是2016年,一項不為人注意的動態,可以說是觸及教育的本質。本欄也介紹過:哈佛一位教授,在2015年做的調查,發覺絕大部分的大學生,只關心自己,不知關愛(caring)為何物,因此在2016年倡議”Making Caring Common”,呼籲大學收生的標準,起碼50%應該考慮學生的關愛經歷。當年倡議才發出3個月,就有255所大學響應。這是期望個人關懷別人、社會、國家的教育理念,以往並不多見。
回到中國,除了上周敍述的古代科舉的公與私的融合,現代也能看到。筆者的兩位博士畢業生,阿古智子(現東京大學教授)與丁笑炯(現上海師範大學教授)當年不約而同都研究教育領域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照一般的理論,這就是執行不力,或者是政策沒有貫徹。她們兩人卻選擇尋找背後的文化,因為分明最後政策又產生了影響。阿古智子的論文題目很能畫龍點睛:「戰略性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也就是說,上面下來的政策,總是留有餘地(模糊),給予足夠的空間,讓下面可以根據本地的(本校的)需要與條件,做出最大的發揮。在中國工作過的世界銀行朋友,聞之無不拍案叫絕:「對極了!這就解了我的大疑團!」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