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軍炮轟盧溝橋,中國軍隊奮起還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隨後,北平各高校紛紛南遷。
孤身在岩泉寺完成《國史大綱》
1938年秋後,在雲南,錢穆除了卜居宜良岩泉寺撰寫《國史大綱》外,每周還要坐5個半小時的火車,從宜良去昆明,下車後再坐一個小時的人力車趕到西南聯大為學生上中國通史課。
錢穆卜居宜良期間,有不少西南聯大的同事前來拜訪。有一個寒假,陳寅恪來山中相訪,在岩泉上寺的樓上住了一個晚上,兩人曾在院中石橋上臨池而坐,陳寅恪說:「如此寂靜之境,誠所難遇,兄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病不可。」賀麟、湯用彤到岩泉寺時也有此問:「君一人獨居,能耐得住這寂寞嗎?」錢穆的回答是:「居此正好一心寫吾書,寂寞不耐也得耐。」
《國史大綱》出版之前,錢穆將書中引論發表在昆明的《中央日報》上。文章一經刊布,立刻震動學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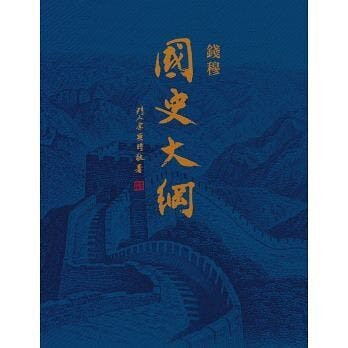
史學家李埏是錢穆在西南聯大時的學生,他回憶說:「大西門外有一個報紙零售攤,未終朝,報紙便被聯大史學系師生搶購一空。一些同學未能買到,只好借來照抄。下午,同學們開始三三兩兩地聚集小茶館裏或宿舍中,討論起來。此後數日,大家都在談論這篇文章。據聞,教授們也議論開了,有的贊許,有的反對,有的贊成某一部分而反對別的部分……聯大自播遷南來,學術討論之熱烈以此為最。」
陳寅恪很欣賞這篇文章,對前來昆明的史學家張其昀說:「最近這裏的報紙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讀。」
自《國史大綱》完成後,錢穆學術研究的重點發生了轉變,由歷史研究轉向文化研究。為中國文化招魂續命,遂成為他一生的學問宗主和志業所在。
抗戰勝利後,北大復校。傅斯年代理校長之職,負責北大接收、復員和北遷事宜。錢穆沒有得到返回北平的邀請。
新亞書院的創立,像乞食團、托鉢僧
1949年,面對時局的動蕩,錢穆焦慮徬徨。此時他收到廣州私立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的一封來信,邀請他到廣州講學。錢穆遂南下廣州。在廣州停留了近兩個月之後,錢穆便隨華僑大學遷往香港。就在這時,錢穆看到了許多從大陸來港的青年失業失學,無依無靠,躑躅街頭,心有感觸。於是萌發了在港創辦學校,為青年提供求學機會的念頭。

1949年秋,錢穆在香港創辦「亞洲文商學院」,期間歷經坎坷與打擊,艱辛難為外人道也。
10月10日,錢穆在亞洲文商學院開學典禮上說道:文化教育是社會事業,是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生命。中國人應真正了解中國文化,並要培養出自家能夠適用的建設人才。我們的開始是艱難的,但我們的文化使命卻是異常重大的。
1950年3月,學校改名為「新亞書院」。在錢穆看來,「新亞」一詞即「新亞洲」之意,即「重新賦予亞洲以新生命」,錢穆希望把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建成一個傳播中國文化、亞洲文化的中心。
「新亞學校」創立時,賀光中負責香港大學中文課務,因見新亞書院教師經濟窘困,多次來訪,勸錢穆到香港大學兼課。1951年夏,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英國學者林仰山,也請錢穆去香港大學任教,錢穆以「新亞在艱苦中,不能離去」相辭。林仰山又請他去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兼課,也為其婉言謝絕。
當時錢穆在新亞書院上課8節,每月收入港幣240元,到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所兼課可獲150美元的研究金,約合港幣900元。但錢穆深恐因自己在外面兼職,會影響新亞書院同仁的工作熱忱,影響了學校的前途,就毅然放棄了這筆為數可觀的額外報酬。
親眼目睹新亞書院創辦全過程的徐復觀在《憂患之文化──壽錢賓四先生》中稱: 「新亞書院之創立,蓋有類於乞食團,托鉢僧」,創辦者「日則講授奔走,夜則借宿於某一中學課室」。

在「手空空,無一物」的艱苦條件下,錢穆硬是憑着一股「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最終把新亞書院辦成了香港一流的大學。余英時、葉時傑、唐端正、孫國棟、何佑森、列航飛等人,即是新亞早期的研究生。
錢穆在新亞書院創辦五周年的一次演講中說道:「新亞這五年來,永遠在艱困中。校舍是如此般局促而簡陋,圖書是如此般稀少而缺乏,教授們永遠沒有正式的薪給,老抱着 一種犧牲的精神來上堂。學生們大多數交不出學費,半工半讀,老掙扎在飢餓線上來校上課,而且是愈來愈窮了。他們憑借這學校幾堂課,來作為他們目前生命唯一的安慰,作為他們將來生命唯一的希望。在此一種極度窮窘困頓之下,不期然而然的,叫出一句口號來,說是新亞精神。所以我常說:新亞精神,老實說,則是一種苦撐苦熬的精神而已。」
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由學者出任大學校長、興辦教育成績卓著者不乏其人,但像錢穆這樣在赤手空拳的情況下,白手起家,憑着 「苦撐苦熬」精神創辦新亞書院,並使其在國際上享譽盛名者卻鮮有其人。就此而言,錢穆不僅是一位著名學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
後來,錢穆等人為在香港弘揚中國文化,希望設立有別於香港大學英語教學的大學,因此,「新亞書院」便成了香港中文大學建校三大書院之一。

自1949年秋在香港創辦亞洲文商學院,到1965年正式辭職離開新亞書院,錢穆居港辦學長達16年之久,他稱這16年是他「生平最忙碌之16年」。
他離開新亞書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要卸下行政擔子,潛心書冊,立志在三五年時間里寫出一部有關朱子學術思想方面的著作。
「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此時,香港「難民潮」驟起,時局不穩,治安惡化,人心惶惶。
1967年,錢穆夫婦接受蔣介石邀請轉駐台灣。蔣介石為其修建別墅「素書樓」。錢穆開始了晚年居台20多年的著述講學生涯。
晚年居台,錢穆用力最多、用心最專的就是研究朱子之學,《朱子新學案》便是他晚年精心撰寫的一部以「尊朱」為一生學術歸宿的鴻篇巨著。國際漢學批評家楊聯升讀《朱子新學案》後,贊嘆不止,說錢穆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並世無能出其右者。」
著名學者杜維明說:「錢穆在闡釋朱熹之學上確實做出了重大貢獻。自從王懋竑的《朱子年譜》在18世紀出版以來,在中文著作中,還沒有哪一部作品對朱熹的思想和學術做出過這樣廣泛深入而且又慎重負責的研究。」
1977年,錢穆83歲,冬天胃痛甚劇,次春雙目失明。雖目力日弱他仍提出新觀點,其著作由其夫人代為整理出版,是為《晚學盲言》。

有一次,他在素書樓家中為學生授課,講課將畢,他環顧學生,脫口說道:「其實我授課的目的並不是教學生,而是要招義勇兵,看看有沒有人自願犧牲要為中國文化獻身!」學生聽後,如受電擊,頓時胸熱目潤,氣湧頂門,心中喊道: 「天啊,也有這樣的老師。」學生明白了,老師上課不是在講書,而是在作戰。作戰是要拼命的,要把所有的力量全部拿出來才行。難怪錢穆講學,直到望九之齡,仍然不厭不倦,富有生命力。
1986年6月9日,92歲高齡的錢穆在台灣自己的寓所素書樓講完最後一課,從此告別杏壇,他給自己的學生留下了最後贈言:「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毫無疑問,錢穆心中的「中國」正是一個有5000年悠久歷史燦爛文明的中國。
錢穆的夫人胡美琦回憶:他(錢穆)73歲大病後,身體尚未完全復原,兩眼也患目疾,醫生不讓他過長時間看書,尤禁晚上看書,所以生活較前輕鬆,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這樣直到他《朱子新學案》一書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願所寄。他自己說:以後我要減少工作時間了。但也仍保持着 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裏喜歡的題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幾年來,有時他對我說這幾天我真開心,寫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寫完,他總會有一場病。

臨終前三個月,由錢穆口授,其夫人整理,錢穆完成了最後一篇文章。
1990年6月1日,由於「素書樓風波」(台北市議會的一些議員抨擊素書樓為「非法佔用公產」),為了避免「享受特權」的誤解,錢穆夫婦毅然搬出居住了20多年之久的素書樓。
兩個月之後,1990年8月30日,在「亞伯」颱風的漫天風雨中,錢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辭世。
錢穆一生以讀書、教書、著書為正業,為後人留下《先秦諸子系年》《劉向歆父子年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朱子新學案》等80餘部、逾1700萬字皇皇巨著。
既有《國史大綱》這樣以30萬字概括中國史全程的宏觀大手筆,也有如《朱子新學案》以百萬言分析朱熹一人的思想和學術發展的極致微觀之作。其學力之深厚,格局之宏大,即便在大師輩出的民國也屬於佼佼者。
學者朱學勤認為,中國上世紀30年代知識分子有三種主要形象,其代表分別是魯迅的社會批判、胡適的自由思想和錢穆的嚴謹學業。
歷史學家嚴耕望曾言:近60年來,中國史壇甚為興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氣磅礡,識力深透,文筆勁悍,幾無可倫比。錢穆一生的傳道授業,是為中國文化招魂,是為中國文化招義勇兵。
漢學家馬悅然說:錢穆在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在錢穆看來,只有做到以下兩件事才能保證中國的未來,即中國人不但具有民族認同的胸襟,並且具有為之奮鬥的意願。
這種文化態度與學術器局,在當今,亦具有深遠的啓示。
原刊於壹學者,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