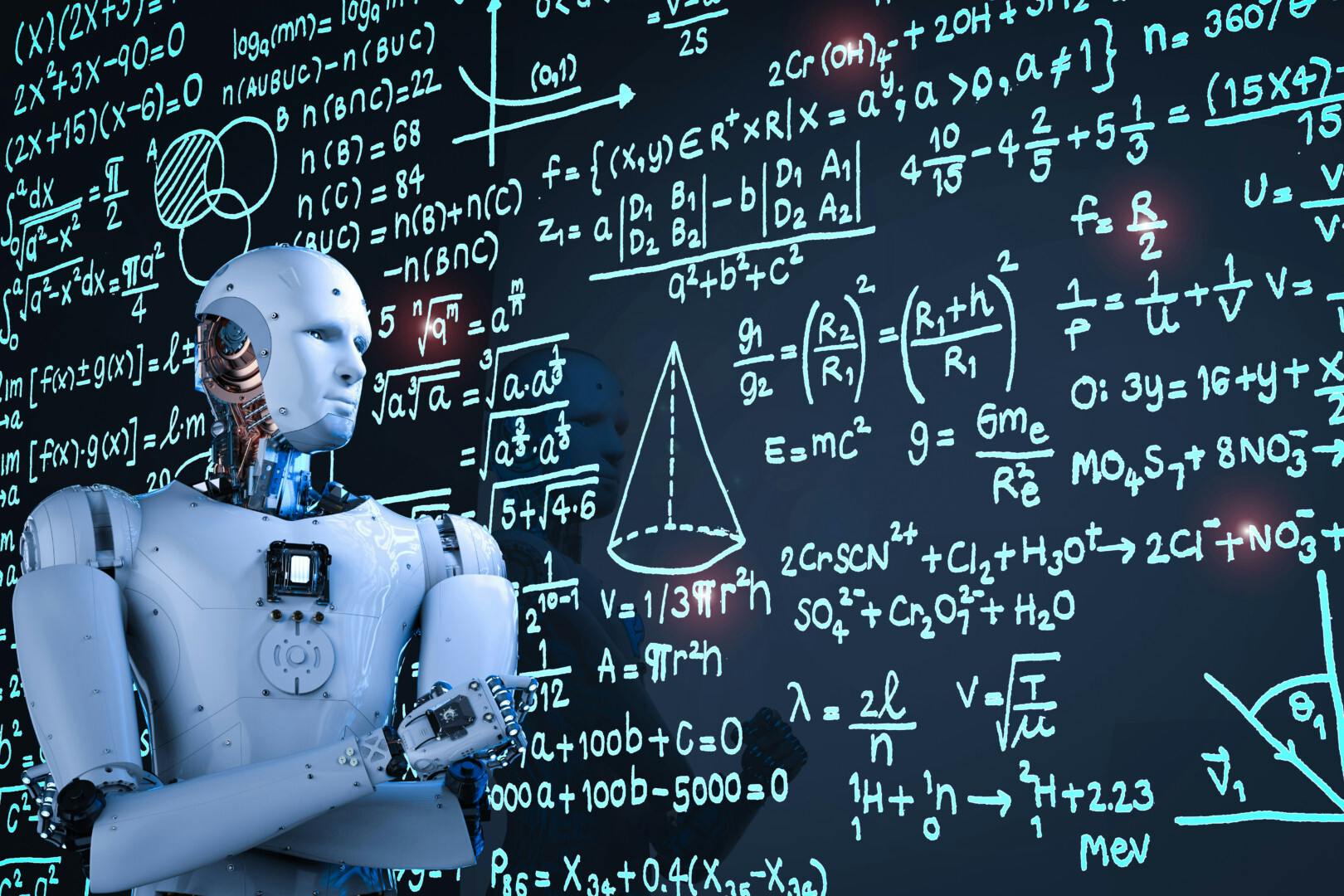本來打算一口氣把學習科學有關的原理連續介紹與探討。不過,過去數天在芬蘭的赫爾辛基參加了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一個小型的會。集中探討AI與教育的關係。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般稱人工智能,根據去年英國帝國學院郭毅可教授的建議,改稱機器智能。覺得應該及時與讀者分享。當然也與學習科學不無關係。
關於AI的討論,由來已久,但是最近幾個月,忽然特別「熱」起來。就筆者知道的國際上可以參加的有關AI的討論,一兩周內,起碼有十幾個,頗為驚人。不過討論AI與教育的,則還是少數。這次OECD的會,是與美國的NCEE合辦。NCEE是美國有關教育比較有持續影響的一個智庫。創立者March Tucker成為美國批判性地評論教育的突出人物。近年則致力於研究全球教育體繫的運行與改革。
這次與OECD合作,設計了一個為時估計2至3年的探索項目,稱為「High Performing Systems for Tomorrow」(可譯為「優秀教育體繫的明天」),所謂High Performing,是根據OECD的PISA(國際學生成就比較研究)成績。這個項目被邀參加的是7個教育體繫:新加坡、香港、芬蘭、南韓、日本、愛沙尼亞、加拿大卑詩省。這是一個內部會議,因此參加的衹有20多人,還包括一些通過遠程方式參加的。
科學猛進與社會發展
雖然主題是AI,聽來是有關科技,但是一大部分時間,探討的是未來社會。大家都感到,雖然科技由來已久──蒸汽機、電報、電話、電視、電腦、智能手機……──大家對於AI和大數據(此兩者似乎很難分開)的到來,都有點忐忑。因為都預感到,AI的到來,會為人類帶來前所未有的變化與衝擊。
筆者認為,AI的到來,不是引起社會的變化,而是配合和加速了社會根本性的變化。重複一下本欄過去描繪過的景象:社會生產過剩,生產不再是為了滿足需求,而是為了營造購買欲望;大量生產,因而讓位於「少而多」(Less of More,少量多款);大型的金字塔式的科層機構,逐步讓位予「一站式」的小、扁、脆的單位。這個社會,正在逐步「碎片化」,或曰「個人化」。
總的來說,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愈來愈趨於個人化。在這種情形下,科技的發展,逐漸把人際關係,尤其是與工作有關的經濟活動,從機構為基礎而變為以虛擬空間為平台。於是,農業社會以土地為根本,工業社會以機構為人們合群的基本,現在(且稱為「後工業社會」)卻變成了平面的共享社會。
這個「共享」,不等於就是財富的均等,而是人們的生活,將會逐漸不再依靠我們常見的中心──餐廳、銀行、商店、交通工具,甚至醫院。其中人們憂慮的,是替代人類將會達到怎樣的程度。有年輕人給我看過一個專供擬寫法律文件的App,號稱它的出現,抹掉了美國55萬個法律職位。
機器智能與人之忐忑
在教育的領域,人們之所以忐忑,大致是3個維度。第一個維度,AI的出現,會為教學帶來什麼影響?是否真的機器就會取代教師?談論之下,大家都同意,機器應該是人類的夥伴,在教學也是如此。本欄去年介紹過上海劉京海的「學程包」,就是以「特級教師」的經驗帶路,與工程師共同研發符合學生學習規律、允許學生個別化選擇、又同時能夠精確紀錄學生學習過程的App,也許可以是一個典範。目前需要注意的是,許多製作學習軟件的,純粹從科目內容的邏輯結構出發,而對學生學習的過程,一無所知。
第二個維度,AI的出現,必然也已經帶來許多操守倫理問題,這是近幾個月許多國際機構有關AI會議不約而同的話題。教育有在這裏可以扮演什麼角色?AI發展的負面影響,會議中討論很多,看來這個討論,正是方興未艾。同事陸慧英,最近在國際場合,提出一個Augmented Intelligence的概念。其優點,是可以涵蓋AI正面和負面影響兩個方面。也可以從這個角度看AI的健康發展。以後有機會再詳細討論。
第三個維度,社會會變成怎麼樣,教育又可以如何為年輕人準備這樣的社會?這成為整個會議討論的最熱烈的。一種想法,是從技術出發,比如說,在課程中引入編程(coding),而認為這是一切新科技的根本。這種想法,逐漸受到一些挑戰。有美國研究,羅列在新興科技行業裏面需要的技術性技能,發覺編程衹是一小部分。而所需又可以輕易在工作中學會。
筆者也認為,邏輯上的確一切科技變化,也許會建基於編程;但是發展科技,即使是機器智能,編程也只是所需技能的一小部分。這有點像筆者在1960年代初在港大學數學,都是從最根本性的幾乎是純粹邏輯性的課程開始,Peano Axiom(講自然數)、Set Theory(集合論)。後來發覺,不是不要懂這些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掌握,在於解決繁多的數學問題的過程之中,「寓學於用」。在小學階段學習編程,也許不至有害,但似乎並非必由之路,更不是捷徑。不過,筆者看過許多小學的「編程」活動、軟件,其實已經是寓編程於遊戲、應用、製作、創造,比較符合學生學習的規律。
迎接未來的課程概念
不過,此次赫爾辛基會議,大家討論的,卻不是這些技術上的準備。「課程應該有些什麼新東西?」大家都沒有很精確的答案。而話題卻往往轉往如何讓學生準備在無法預測的環境中生活與工作,以及如何讓學生在社會性和情感性的方面更加成熟。
會議還請來了4位愛沙尼亞的青年創業者,分別在做智能酒保、與UBER競爭的汽車接載、教育性的諮詢,其中一位還是國家的Digital Adviser。他們的說話,很多都是發人深省的精句。
「在創業過程中所學,比在商學院要快十倍!」
「現在學校裏面所學的,起碼30%是沒有必要在學校學的。」
「現在的畢業生,初來上班,還以為來學校上課,等着老師告訴他們做什麼。」
大家都覺得,課程當然不斷會有新東西。但是應該對「課程」有個新概念,或者說重新定義什麼叫做「課程」。應該讓學生的學習不要困在傳統的「科目」概念裏面,讓他們盡早有社會和工作的現實經歷,而不是在科目的增加或者較少上面兜圈。
這與香港現在的「大教育」現象與理念不謀而合。也就是讓學生在在學的時候(而不是畢業之後),就接觸社會的實際。而這些可以稱為「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的經歷,需要全社會的支持和配合。
在香港,幾千個社會上的種種機構,正在勤懇地、然而愉快地,為中小學生提供現實的體驗。既不需要有政府強制性的政策,也沒有額外的金錢回報,外國人聽說,無不動容。那也的確是香港人足以引以自豪的。
值得一提的是,會議中許多人提出的社會性與情感性學習(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筆者近日發覺,這在香港也正在遍地開花。筆者活動範圍有限,但是接觸到在做這方面的結構和團體,已是難以勝數。
有專門設立的機構(如GEMS),有基金作為回報社會的方嚮(如北山堂基金),有個別教師在一所學校發源的連鎖運動(如順德聯誼會李金小學的葉碧君),有少數青年人組成的新興事業(如Just Feel),有宗教機構成立的專業性學院(如慈山寺)。其中「正向教育」似乎在百花齊放之中,正在形成一個香港模式。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