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著名作家余華,生於1960年,1983年開始發表小說,代表作有《十八歲出門遠行》、《兄弟》、《許三觀賣血記》、《活着》、《在細雨中呼喊》等。當中《活着》和《許三觀賣血記》獲選為90年代最有影響的10部作品。《兄弟》被《瑞士時報》評選為2000年至2010年全球最重要的15部小說之一,作品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在歐美和亞洲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他於7月22日(周六)來港參與書展講座,受到熱烈歡迎,逾1萬人報名,大會臨時安排了兩場講座。本社整理了余華兩場演講及與觀眾答問的完整內容,以饗讀者。
余:余華 施:施志咏(主持,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師)
寫作永遠不知道下一步
施:今天的主題叫「文學自由談」,文學源於生活,我們就多談談余華老師個人。今天這個場面,我認為你絕對堪稱一名文學明星,此刻心情如何?
余:謝謝你們,我感覺黑壓壓一片,自己成了查爾斯·狄更斯了。據說,當年狄更斯在英國報紙上連載的小說完結後,他坐船回到波士頓,結果碼頭上有好幾千人等着他,然後異口同聲地問「小奈兒死了沒有」,就是這種感覺,太幽默了。
施:余華老師曾經說,自己的創作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成名階段,《十八歲出遠門》是你的成名作,當初創作這部小說時,有什麼念想嗎?
余:寫作其實跟一個人的經歷是一樣的,你永遠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當年11月我要去北京參加筆會。那時候我還沒出名,天天想出名,但是還沒出名,就想帶一篇小說去,希望趁機發表。當時坐在書桌前不知道寫什麼,然後看到杭州的《錢江晚報》裏有一條新聞,說嵊縣附近有一輛裝滿蘋果的貨車出了車禍,車上的蘋果都被人搶光了,一下子找到感覺了,開頭第一句話就寫成「柏油馬路起伏不止,馬路像是貼在海浪上」,印象很深,很順利的寫完了。拿到北京以後,遇到了我的一個貴人──李陀。他看完之後對我鼓勵說,「你現在已經走在中國文學最前面了」。從那刻開始,我突然發現自己走在最前面。現在回過頭一看,我確實不能說最前面,也是最前面之一,所以叫「先鋒文學」。

每天都有靈感 關鍵在於準備
施:可以說文學源於生活,因為一則新聞,就出了你的《十八歲出遠門》。到了第二階段,大家最熟悉的莫過於被拍成影視劇的《活着》,創作過程好像也有一些瓶頸,可否分享一下?
余:《活着》已經準備很長時間了。我一直想寫一個人和其命運的關係,但不知道從何入手。來港前,有記者問靈感是怎麼產生的,我說靈感其實每天都會出現,但問題是否準備好了。如果沒有準備好的話,靈感出現以後,它又會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但是準備好了,靈感才真的算是靈感。當時,我一直在想《活着》的內容,甚至部分細節都有了,卻不知道從何入手。結果,一天中午睡個午覺醒來以後,突然腦子裏面出現「活着」兩個字,馬上就來了感覺,就很順利地在北京寫完。然後我跳上火車,直接送到《收穫》編輯部。
《收穫》是我年輕時接觸過的文學雜誌裏最大方的,無論著名與否,收到作品以後都是一視同仁的。要是我在其他雜誌發小說的話,每簽字可能是10元人民幣,王某的話就是30元,但在《收穫》一律都是30元。而且我住旅館的費用可以報銷。當時陳永新是我的編輯,他帶着我吃遍了《收穫》周邊的小餐館,吃了一次又一次,都是可以報銷的。他很歡迎我跟蘇童到上海去。

施:大家有沒有發現,余華老師說的每一句話都非常淺白,當他調侃自己識字不多,卻能製造優美的意向和比喻,包括描寫死亡。例如《活着》裏有一幕,主角的兒子死了,他看着兒子每天上學經過的那條小路。你是怎樣形容那條路的?
余:《活着》的語言是最樸實的,有兩個原因。一是主角雖然上過3年私塾,但他還是一個農民,講述自己的故事時不能用深奧的詞匯。當時我記得先鋒文學時期的一些中短篇裏有過一個比喻,我就想偷換概念來形容月光下的道路,像一條河流一樣,泛着蒼白的光芒。但這用在一個剛剛失去兒子的父親上是不負責任、不恰當的。
然後又找到「鹽」這個意象。因為鹽是白色的,而且鹽對一個農民來說肯定很熟悉。另外,鹽和傷口的關係大家也是知道的。讀過《活着》的朋友肯定知道,主角兒子有慶每天都要割羊草,時間來不及了就要跑步去學校,母親給他縫的布鞋跑沒幾次就跑壞了。後來被父親、主角福貴罵了後,每次都會赤腳往學校跑。前面這樣一個鋪墊,所以當福貴把兒子埋了以後,他再看那條小路時,我覺得一定要形容月光照下來像是灑滿了鹽的這種感覺。

《兄弟》是命運的安排
施:你的第三個創作階段的代表作是《兄弟》,分成上、下兩部。《兄弟》的時代背景濃縮了從文化大革命到改革開放這個很重要的時代。談談當初為什麼寫這個時代?
余:1997年的時候我就已經開始動手寫《兄弟》,因為當時我已經感覺到中國出現了很大的變化,但是我當時沒寫完,我覺得是命運對我的安排。
一直到了2003年,我重新開始寫《兄弟》,上部和下部分別在2005年和2006年完成,因為到了2004年、2005年的時候,就覺得1997年的變化根本不大。所以我覺得我命好,讓我在2003年才開始真正去寫它,而不是1997年就完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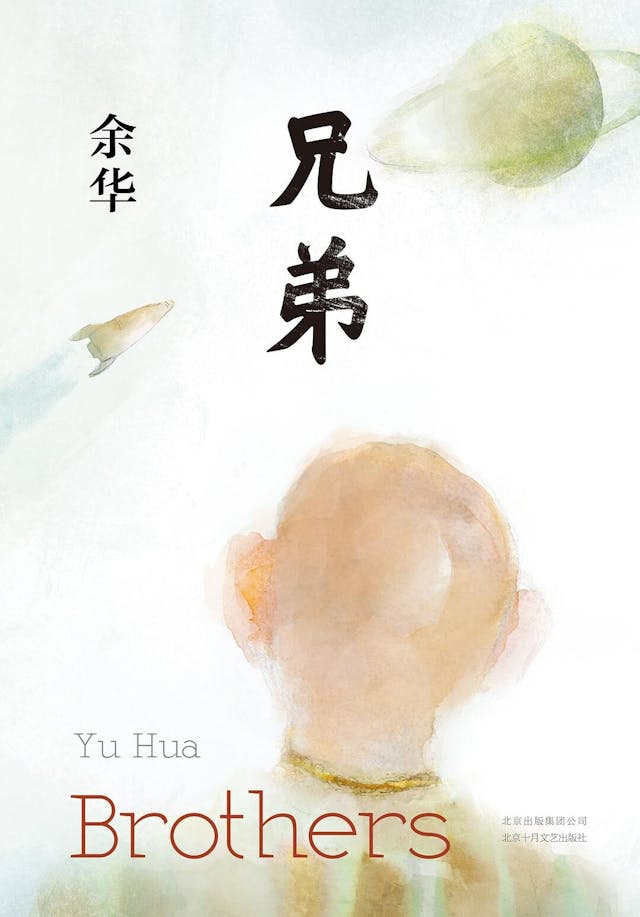
施:其實你的一部作品,有時候由構思到完成也拖了很長的時間,例如近期的《文城》也拖了21年。我記得你有一個很精彩的比喻,說莫言寫小說就像打籃球投籃,轉眼就中了。你則像踢足球,一個多小時還是0:0,《文城》算是0:0的成果嗎?
余:莫言的一場籃球比賽下來,就像NBA比賽48分鐘,兩隊加起來200多分。 我是一場足球比賽,時間比他長,常常0:0。確實莫言寫作非常快,他經常背個包回高密,兩個月後回來,包裏面塞了很厚的稿子,讓人很羨慕。這是寫作方法不一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寫的慢,斷斷續續的在寫。寫完《許三關賣血記》以後準備想寫《文城》,後來變成寫《兄弟》了,寫完又回來寫《文城》,寫着寫着又放棄了。因為新冠疫情來了,要隔離,所以一咬牙終於把它寫完了。封城的時候,我當時以為會有一堆作家都能產出長篇小說,結果沒有。
施:你把創作作品分成三個階段,《文城》跟你之前的作品風格不一樣,會不會代表你第四個階段?
余:我對寫作的要求其實很簡單,第一是不要重複自己的作品。第二,我給自己的長篇小說拉出一個質量平均線,自我感覺達到水平才可以出版,如果達不到的話繼續擱在那裏,所以21年才完成《文城》。

時代奠定風格
施:余華老師心目中的男性形象好像特別完美,《兄弟》裏那位繼父宋凡平是其中之一。你可以介紹他有些什麼功績做一個好男人?《文城》裏的主角也有一個好男人形象,你是不是刻意想美化男性?
余:我可能是無意之間美化。宋凡平跟林祥福還是不一樣,他剛好出現在小說裏那個時間段,將人性美好的一面顯示出來,我沒有篇幅或者機會去寫他的缺點。他不可能沒有毛病的。其實,福貴、林祥福、許三觀也是很完美的男人。
施:宋凡平對繼子和兒子一視同仁,尤其是在文革的時候,宋還樂觀的告訴孩子沒事。另外,當他被關在倉庫裏拷打時,仍每天寫信給在上海治病的妻子李蘭,請她安心養病,這太偉大了吧。你說沒有時間寫他的缺點,真的嗎?
余:從技術上來說確實沒有。另外必須要說清楚,文革的時代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樣,由於外部環境很壓抑,家庭內部團結是非常關鍵。從小直到文革結束,我就沒聽說過鎮上有人離婚的。但十多年前開始,我絕對不問幾年沒見的朋友,對方配偶的關係,以免對方離了婚而感到尷尬,這是我一個經驗。
當時《活着》和《許三觀》兩部小說要推銷到美國時,在不同出版社兜兜轉轉,常遇到沒有理由的退稿,只有一位編輯提出質疑,為什麼小說裏面的人物只承擔家庭的責任,而不承擔社會的責任?我覺得這是文化差異,回答說,中國3000年以來都是一個封建社會,大部分人在社會生活中沒有地位的,他只有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屬找到位置。中國長期以來的社會紐帶在家庭和家庭之間,不像美國,在個人和個人之間。當然,中國在90年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你不敢輕易問一個人的配偶最近好不好的時候,那就意味着我們變成個人和個人連接了。寫作也必須與時並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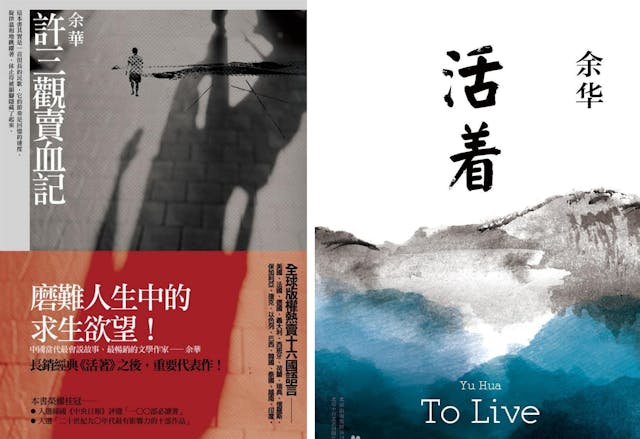
人物描寫 套入個人經驗
讀者:請問余華老師的作品中有多少靈感來自於個人生活體驗?
余: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比如說《兄弟》出版以後,他們說那個余拔牙是我。我說不是,要是的話我肯定把他寫成英雄人物了。但確實我擁有拔牙技術,當年我是赤腳醫生(按:鄉村中沒有納入國家編制的非正式醫生),中學畢業後直接被分配到牙科醫院,上班第一天就要拔牙,拔了5年。後來讓我去衛校學了一下,讀人體解剖學,真的要我命了。
當時寫到最後,余拔牙沒有病人,躺在椅子上背誦肌肉、血管、神經,孩子說「真他媽的缺德啊,長那麼多肌肉血管神經幹嘛,背都背不過來」,也是因為現實中文革已經過去,進入改革開放了。江湖上的中醫、牙醫都要參加考試,合格才給你發行醫執照。

我們的生活 不屬於別人
讀者:請問在創作《活着》的過程中,刻畫主人公悲慘的遭遇,更多是源於自身生活還是來自想像?
余:因為我經歷過那個極其貧困的時代,知道貧窮是什麼滋味。《活着》對我來說意義重大,一方面是寫作的轉型,另一方面就是讓我對人物理解更多。
我最早寫《活着》的時候是用第三人稱、旁觀者的視角,延續了《在細雨中呼喊》比較優美的語言方式。《在細雨中》的孫廣才、孫光林都是農民,要是用第三人稱就寫不下去,後來用了第一人稱之後就很順利地就寫完了。你要是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看福貴的話,他除了苦難沒有別的,但讓他來講述自己的生活時,他認為自己是很幸福的。
很多人說是福貴是一個悲劇人物,我就一直不同意。他覺得自己有過世界上最好的妻子,有過兩個最好的孩子,有過最好的父母。最後在晚年回憶起來,覺得自己一生無悔,沒有任何責任。即使是家珍死的時候,村裏沒有一個人說他壞話的。我覺得,生活是屬於自己感受的,不屬於別人的看法。
福貴的母親安慰他說,「只要活得快樂,窮也沒關係」,這是我寫出來的,但我覺得這個福貴母親說的,這是她的名言。
作者也是讀者
讀者:你會因為自己筆下人物悲慘的遭遇而難過嗎?
余:《活着》也好,《兄弟》也好,我在寫初稿的時候感覺不那麼強烈。為什麼呢?因為那一段讓我很難受的,不是一口氣寫完的,可能是分成好幾天寫完的。最難過的是修改的時候,你是整段看下來的。印象中《兄弟》上部寫到最後的時候,一把鼻涕一把淚,桌子邊上擦眼淚的紙,堆成一個小山。
施:我也很同意,哭的最厲害的情節就是宋凡平從倉庫逃出去,要去車站接他的妻子李蘭,結果被人用棍子毒打至死。你當初是怎麼設想的?要賺我們的眼淚嗎?
余:沒有。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是沒法考慮讀者。在座的朋友經歷有相似之處,但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凡是有寫作經驗的人,都擁有作者和讀者的雙重身份,往前寫的時候是作者,覺得有地方要修改的時候就是讀者,寫作是兩種身份的工作。
讀者:請問你如何看待百度說,你是一名優秀的牙醫,蘇童是一名出色的作家?你又認為文學成就是可以比較的嗎?
余:我和蘇童旗鼓相當,但她有一點不如我,就是不會拔牙。但她會當編輯,這一點我不如他。有一次我們要給自己的一本書寫一個簡介,去法國出版。我不知道怎麼寫,卻發現蘇童寫得很好。那是因為當年小說要三審通過以後,才有可能在雜誌上發表。當蘇童發現一個無名作家的一篇好小說時,就要把介紹寫得很好,才能吸引上司閱讀那篇小說。所以編輯很重要,相當於作家的伯樂了。
讀者:余華老師如何看待「把痛苦留給讀者,快樂留給自己」的說法?
余:這個我今年在澳門就已經更正了,我沒那麼缺德,我說是把痛苦留給虛構,把快樂留給現實。把痛苦的情感,全部在虛構的世界裏邊表現出來以後,在現實裏,只剩下歡樂了。
余華文學自由談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