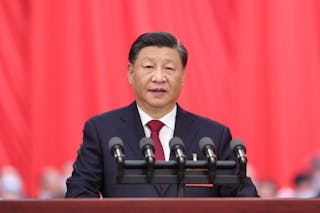香港的裙帶資本主義積重難返,長久以來對社會已經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吞噬了一切創新與進步。以前香港還有本錢說句「不進則退」,但現在一些關鍵領域已落後於人,逐漸危及香港的作用和地位。

在中國與歐美國家關係陰晴不定之際,香港特區政府力推與東盟及中東等地經貿關係,此舉除了緊貼和配合中央政策之外,也有以備日後香港可能與歐美脫鈎的用意。脫離了歐美的香港,肯定將日漸褪色,不再是昔日的香港。

2019至2020年的政治風波後,香港不少人遭逢到一種絕對價值的崩塌,陷入了虛無主義的狀態。後真相時代的出現,令人們只能在虛無主義中不斷輪迴,無法解脫。

中共在經濟和外交上確實皆陷入困境,不得不放低身段,挽回外界信心,並減緩來自美國的壓力。

如今以資本主義和西方思想改造中國之路,已徹底被堵死,打破了自近代起中國從西方引進思想的範式,令中國可能面臨自近代以來的一次歷史總結算和範式轉移,足以將歷史引領到一個難以挽回的方向與軌跡上。

現在北京放棄了重視軟實力的做法,改以市場和金錢作為誘餌、經濟脅迫作為手段,執着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意識形態鬥爭,令最終能夠輸出「中國模式」、扭轉西方的體制壟斷的機會,愈見渺茫。

烏克蘭戰爭的失利,已令俄羅斯逐漸淪為中國的「從屬國」,令位處邊緣地帶的陸權強國掌控/入主心臟地帶的可能重新出現,只是這次入主心臟地帶的陸權強國來自歐亞大陸的東方(中國)而非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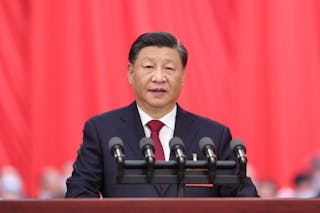
面對着中共回歸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告終,以及習近平對市場經濟的懷疑與戒心,香港和一國兩制的地位早已亮起了紅燈──即使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在習近平眼中可能也是不值一顧。

由於習近平自身的意識形態、國內的政治角力,以及與美國的鬥爭等關係,我們目睹中國正逐步回歸列寧主義,「中國夢」亦慢慢變成了「列寧夢」。

香港新一屆政府上任百日,對於放寬入境檢疫,特首李家超強調任何措施都要有序及穩妥,不可帶來混亂,否則會適得其反,欲速而不達。這究竟是閃爍其詞,抑或是按部就班,很快便有分曉。

香港正被write off,已經給人家「踩到上心口」,對手們「先勝而後求戰」,香港則「未戰先敗」。事到如今,11月的國際七人欖球賽和金融峰會的成敗,或許已不再重要。

2019至2020年的風波令北京意識到香港已非「為我所用」,而是「為外國所用」,因而以「我認為怎麼做最好」為出發點,重新制訂香港的制度與政策。結果就在期望香港可以幫國家一把的時候,卻發現香港快不成了。

中概股需從美國退市,不少中概股計劃由美國轉到香港上市,或把在港第二上市地位轉為雙重主要上市,北京禁不起失去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不少民調皆顯示政治氣候已經開始好轉,港人對國家和一國兩制的印象有顯著改善,而中央亦釋出不少信號,明顯有開新局的意味。

目前香港最棘手的地方,是幾乎所有範疇的走勢都是見頂回落。筆者相信現在中央也感受到香港的國際地位開始動搖,特區政府及各界人士須在安全與穩定的前提下,保住香港獨特地位和優勢。

香港必須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否則將無以提供足夠經濟誘因以影響身分認同、帶動人心回歸。

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刻劃着中華民族變法圖強、洗刷百年國恥的嘗試與苦難,本質上是為了令國家擺脫明清時代的厄運,以達至民族復興。可是,現在國家卻有可能在重蹈明清時代的覆轍,這無疑是對歷史的一個極大諷刺。

這次疫情本來是推動線上終身學習、遠距醫療、數碼政府等新舉措的絕佳機會,也是將香港進化成知識型經濟的重要契機,但政府就這樣白白浪費一場「好的危機」。但面對政府能力低下,其實還未至於一切皆休。

5月3日,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出席立法會簡報工作重點,罕有回應香港有可能被牽涉入歐美制裁之中,特別是有機會被移出SWIFT(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折射出北京的考量與評估。

現在中央用李家超或武官治港,背後的潛台詞就是執行與服從,並將矛頭直指公務員團隊。李家超在政綱中提到強化政府治理能力,一定程度上等於劉備在未站穩陣腳之下,貿然把徐州防務交給了張飛。

拜登政府為了不讓俄烏戰爭發展成「無限戰爭」,只給予了烏克蘭「有限責任」的承諾,並且不讓美國全面介入這場戰爭──這對於慣以軍事行動為主要手段、窮兵黷武的美國來說,無疑是一大突破及睿智的表現。

現在香港凡事都要靠「阿爺」開腔維穩,令本已過時的港府行政系統之上,疊加了多層且混亂、非制度化的決策系統,令香港淪為了「殭屍城市」,這樣對香港應對風險社會的問題與災難非常不利。

在這次俄烏戰爭中,拜登政府所運用的正是這種「拜占庭模式」:不拘泥於軍事行動,以外交戰和經濟戰為主導,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從多方面確實地削弱俄羅斯的實力,這才是真正凌駕硬實力和軟實力的巧實力。

無論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役中成功與否,世界都會進入「假戰」或新冷戰階段:以前是宣而不戰,現在變成不宣不戰。西方亦意識到再不能以他國的代價換取暫時的和平,現在只待西方政府與民眾重新認清事實、調整心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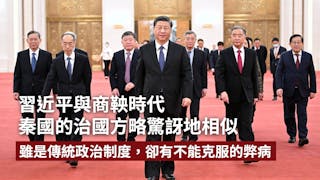
現在習近平重新將中國引領到法家治國的路上,使中國社會與人民再一次暴露於這種周期性震盪與系統性危機之中,究竟是否有必要和值得?

香港這邊雖然也在實施清零政策,但與內地最關鍵的分別是,香港已在採用mRNA疫苗,令香港實質上有條件測試在mRNA疫苗的保護下,如何可控地逐步對外開放,可作為日後內地重新對外開放的重要參考。

新冠病毒非得以效力更高的mRNA 疫苗來應對不可,只要是本土自主研發就可以了;「政治病毒」非得以「民主」來應對不可,只要是中國式民主就可以了——這亦成為了北京消滅新冠病毒及「政治病毒」的新指導原則。

香港政制發展的走向,則由邁向西方民主的政制改革,變成中國式的政治改造──通向西方民主的大門已被關上,未來政制發展將會是「完善選舉制度」與中國式民主的對接,基本概念已寫在剛出爐的香港民主白皮書裏。

表面上中央掌握治港的所有權力,但新的政治設計以至最新政治發展卻隱見一種權力分散的趨勢,社會亦漸漸呈現外強中乾之象,中央顯然在治港方略上須多加微調。

從哪個角度看也好,拜登、習近平會談的直接結果是兩國變相「休戰」一年,暫時將所有爭議「 凍結」起來,直至找出解決之道或局勢出現顯著變化,可幸的是,是次會談得以延續所謂「兩國元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