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市有點像香港。初開埠時,香港只有港島,九龍和新界是日後發展起來的。

曼儀表示希望有一個溫室,我於是為她設計了一個,加在我的書房外。

哈市臨海,街道高低蜿蜒,多樹,入秋紅黃棕綠紛陳,叫人目不暇給。

1994年6月30日,我懷着悵惘的心情,向香港道別,到加拿大生活。

遊覽團的原定行程如下:乘火車去廣州、乘飛機往蘭州、乘旅遊車至敦煌、乘飛機回蘭州、乘飛機到廣州、乘火車返港。

開車前往大峽谷時,我注意到油箱只有四分一滿,於是請她們留意,見到油站就提我加油。不料沿途的油站都偃旗息鼓,停止營業。

我曾應美國政府邀請,前往美國各地學習和遊覽六周,旨在了解當地的歷史和文化。我跟十餘名團友建立了友誼,有些維持了數年,有些十餘年,有一位至今仍然時通魚雁。

回眸細看,發現在中英聯合公報發表前後,香港成立了不少各式各樣的會,有自發的,大概也有奉命行事的,其中有些恐怕不無政治目的。有人成功了,搶得一席位;有人失敗了,消聲更匿跡。這時,香港出現了「有人辭官去外國,有人趁機趕科場」的現象。

清晨、黃昏,平滑如鏡的淺海上,都會有三數隻海鷗在天空飛翔、或在水上起舞。農曆月頭、月中的晚上,都有漁人划了一艘掛着大光燈的小艇前來捕魚。漁夫作業時,為了把魚兒趕進網內,不斷用木條敲打木板,發出很有節奏的「恪恪」聲。

兩年後,我們搬到同座向南的4C 單位。這單位的主睡房向西,對正明原堂,下面是一道原本是小溪的水渠,經年流水潺潺,聲如天籟。可是,正是這悅耳的音樂逼使戶主搬家,因為她神經衰弱,忍受不了那聲響。

他們認為,搞課外活動主要是為了提高學生的知識和技能。我對這觀點有很大的保留。我們可以嘗試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一下這個問題。英文有一句諺語: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學生?

經過八年的運作,協會已趨於成熟,它應該可以作進一步的發展了。於是我請幹事會考慮向小學進軍。次年,協會成立小學支部,開始招收小學會員。再過一年,協會在九龍童軍總會的酒店舉行十周年慶祝會,由李越挺、何子樑和我主禮。半年後,我便離開了香港。

課外活動統籌主任協會終於在1984年1月21日成立了。典禮假葛量洪教育學院舉行,由副教育署長梁文建主持。散會後,獲選幹事隨即召開第一次會議,互選職員及討論協會未來工作大綱。結果,代表培正中學的陳德恆當選為第一任主席。因為這是一個中學教師組織,我一直隱身幕後,以顧問身份參與他們的工作,直至退休。

會議期間,陽光普照,春風拂面。這個會,人和、地利、天時,一應俱全,預兆着它將會取得預期的效果。

順帶一提,麥理浩上任不久,便約見司徒華了。這是1971年的事,是司徒華自己告訴我的,那時「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尚未發生。次年,明原堂一位宿生走來告訴我,說收到麥理浩的邀請,與幾位港大同學一起跟他共晉午膳,並問我知否背後的理由。我怎會知道?但可以猜到多少。

香港中學的地理課程一向都不太重視中國。1997年之前,課程綱要雖然提及中一要學鄰近地區的地理,但實際上只觸及皮毛。

1998年2月,做了一次大手術,身體又好起來了。隨後兩年,中大教育學院趁我回港探親之便,請我參與教學視導工作。這兩年,我跑遍港九新界,聽了不少地理教師的課。 記得八十年代任教地理教學法時,我非常留意地理室的設備及其運用。沙盤是中學地理室的標準設備之一,但三十年來,我只見過一位教師上課時利用它來教學。我深信,如獲善用,這個沙盤會帶來極佳的教學效果。很可惜,一直以來,這設備只是備而不用,甚至備而不能用!我見過不少學校把它放在牆角封塵。它的木蓋本來是可以整個搬走,以便師生在沙盆堆砌各種地形的,但有些只有一邊可以開合、另一邊卻是密封的! 遊戲之上品 也許因為這兩年視導的不是自己教出來的學生,他們有所顧忌,在教學設計上和施教時,態度比較保守,以致沒有一位教師利用地理遊戲進行教學,而上課時讓學生分組討論的也絕無僅有。當年我非常鼓勵教師用這兩個方法教學,也常常跟他們討論地理遊戲的設計問題。我指出,下象棋和擲骰子是遊戲的兩極:前者只講技術,後者全憑運氣,兩者都不是遊戲的上品。好的遊戲應該介乎兩者之間,既講技術,也靠運氣。我個人不愛搓麻將,偏好下象棋,但不能不承認,作為一種遊戲,麻將是上乘之選。設計地理遊戲時,必須認真向麻將學習。 我又常向學生推薦方太,說她教學一流,要多多向她學習。方太是著名的廚藝教師。她教燒菜,好在哪裡?好在簡單、明瞭。她最成功的地方是使觀眾覺得燒菜不是難事,誰都可以做得好。為此,有一年的畢業生特地送了一條圍裙給我。對我來說,這的確是一份上佳禮物。多年來,我每天都用它一兩次。 許冠傑那句「最緊要好玩」也是我的座右銘。1999年,我協助中大教育學院視導了超過30位教師的課。有好幾次不但我覺得非常「好玩」,上課的教師和學生也覺得「好玩」。這真是少有的皆大歡喜的經驗。其中一次的過程如下。 接受視導的是一位初出道的女教師,任教於一所主收「第五組別」學生的中學,教的是中一成績最差的一班,課題是「城鄉的人口遷移」。在上課前的討論裡,她說: 「這是一班非常頑劣的學生,不但學習能力低,態度也差。既不聽講,也不作答。非答不可時,不是說不懂,便是胡說一通。」她的教案是先解釋何謂推力和拉力,然後分析各種推力和拉力的作用,再舉例說明鄉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如何導致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 我問她有沒有膽量臨時修改教案。她毫不猶疑地說:「可以試試。」我於是建議她用提問的方式開展該課的教學活動,先問:「如果你可以選擇,你會選擇在觀塘 (工業區) 還是在錦田 (鄉村) 居住?」然後跟進:「為什麼作這樣的選擇?」我又對她說:「如果學生不主動作答,就隨意請其中一位作答。因為是選擇題,問的又是很簡單的個人意見,他們大概不會拒絕作答。問完一個學生之後問第二個、第三個,直至你認為足夠為止。每次都把他們的答案分門別類地寫在黑板上。可以分四組:(一)鄉村的推力、(二)鄉村的拉力、(三)城市的推力和 (四) 城市的拉力。之後,你作總結時,解釋何謂推力和拉力,並補上他們沒有提及的理由。如果有時間,還可以再舉例作進一步的說明。」 結果,上課時,學生踴躍發言,三十餘分鐘內絕無冷場。下課後,她說:「想不到這班學生也可以那麼熱烈地投入。」 中二地理教師在講授比例尺的運用時,一般都是先向學生講解表示比例尺的三種不同方式,即說明式、模範分數式和圖尺式,然後教導學生如何運用各種方式的比例尺去量度地圖上兩點之間的實際距離,再講解三者之間的換算方法。最後是做練習。 看了這樣的教案之後,我通常都會說:「教這個課題時,教師不必講得太多。應多讓學生做,讓他們從做中學。」跟着問他們有沒有膽量臨時修改教案。有膽量的,我便建議他一開始就讓學生量度地圖上兩點之間的距離,並根據地圖上所提供的比例尺 (不管是什麼方式的比例尺),去算出這兩點在地面上的實際距離。我說:「這是很簡單的運算,小學生也會做。所以,不必講太多,越講得多,他們就越糊塗。讓他們用不同方式的比例尺做若干次練習之後,再由教師總結一下就行了。三者之間的換算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懂得運用任何一種方式的比例尺去找出地圖上兩點之間的實際距離。這類換算其實也不艱難,懂得運用比例尺自然就懂得換算。」 有膽量的,如我所言去做,都發現學生在比例尺的運用上,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十分鐘的練習之後,他們作一小結,跟着講解如何換算,再讓學生做一些練習,包括換算練習。從學生的表現看,他們並沒有給換算難倒。 反之,按原定教案授課的教師,往往要花15至20分鐘的時間才講完各式比例尺的運用。到解釋如何換算時,學生很快便給各種公式弄糊塗了、嚇怕了,各種問題於是隨即接踵而來。這教節餘下的時間就糾纏在各種公式的重複講解中。在三十多分鐘裡,學生從未做過任何練習。下課了,學生和教師都有點茫然。 (封面圖片:Pixab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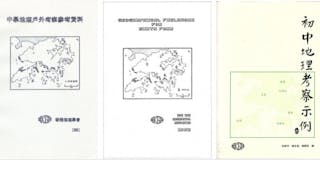
……這類活動給陷入財政困境的學會帶來了生機:會員回來了,財政也開始好轉了。

80年代下半葉,我不僅活躍於國內的地理教育界,也經常出外參加國際研討會,也曾參與「地理教育國際憲章」的定稿會議,並獲委為中文本的譯者。

我到格致中學觀了一節課。授課的是一位年輕教師。他準備充足、態度誠懇、聲線明亮、講解清楚,可說是一節上佳的課。美中不足的是:臨近尾聲的時候,有學生多次舉手,但他視若無睹。事後我問他是否沒有注意到舉手的學生,他說不是,只是恐怕擔誤了時間,不能如期完成教案。

我覺得當時悉尼的評卷方法,比香港的好。香港採取的是「標準答案」模式:標準答案列出所有要點,每點若干分,一般來說,答中八成就可得滿分。閱卷時,不少評卷員只看要點,不管文理,導致教師以填鴨的方式施教,學生以「囫圇吞棗」的態度學習,並以「和盤托出」的方法答卷,以致香港的學生不少患上「思維失調」症。

對外是一個中心,內裏則是兩個隊伍。後來,我也因為一直都沒有一個妥當的辦公室而遷出。

這兩年我的確沒有做「學術研究」,因為這不是當務之急。那時最急切要做的是:教好書、做好教學實習的安排、協助搞好學院的行政、提倡課外活動等。

1993年的研討會是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周年校慶活動的一部份,議題是《東南亞地區華人社會的課程改革: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得偉倫基金會、九龍樂善堂、英國文化協會和牛津大學出版社贊助。

大學要求同事多做研究、多在有份量的國際學報發表論文。這要求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但執行起來卻大有問題。

中大早有計劃逐步改建崇基學院,這計劃到80年代開始落實了。新的教育學院是80年代上半頁開始籌劃的,位於學生飯堂舊址。80年代中,圖則初稿出了之後,院長才公布消息和徵求意見。

談到著作,我想起了兩件令人感到遺憾的事。第一件發生於1980年代初。在鴻基的推動下,教育學院的院長徵得校長的同意,組成了一個跨院系的「中文教材籌委會」,準備出版一系列的中學中文教科書。我是執行委員之一,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開了不下十次會,但每次都是「得個講字」,結果一事無成,計劃也因此無疾而終。這經驗使我有點心灰意冷,也加深了我對中大的疏離感……

我和鴻基的關係本來是不錯的,自此便出現了變化。再過一年,鴻基對我的誤會更進一步深化,起因是某同事的聘任。到80年代中,他看清楚這位同事的面目和我對院長的態度之後,我們才和好如初。

中大教育學院的教務會議一般都很冗長,動輒半天,有時一天,經常為芝麻綠豆的事情爭論不休。

學生對他的不滿包括遲到和早退,甚至「冇到」。另一位同事也受到學生類似的批評。他偶然遲到、極少早退、從沒「冇到」,但多次觀課時打瞌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