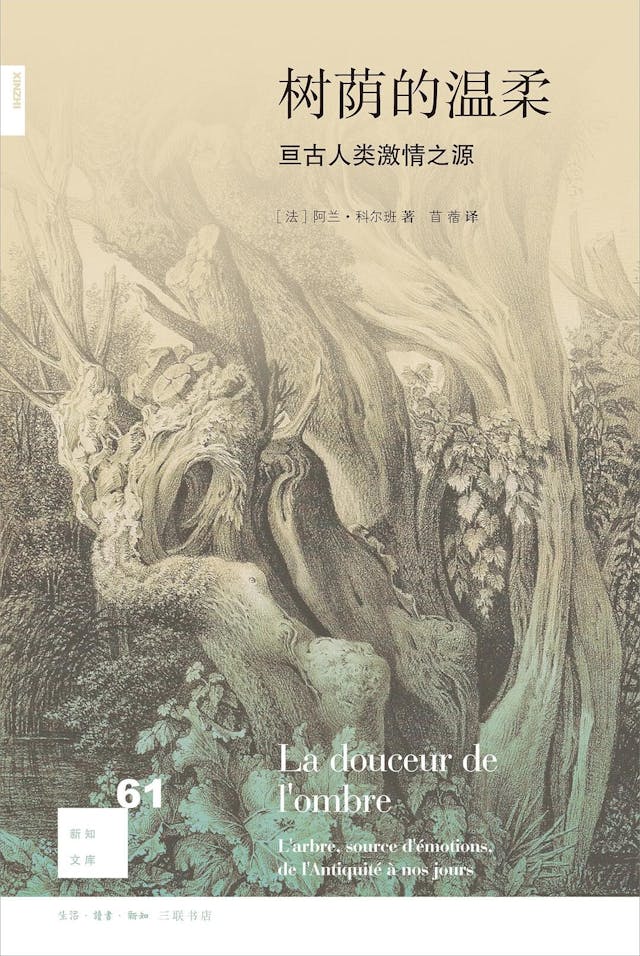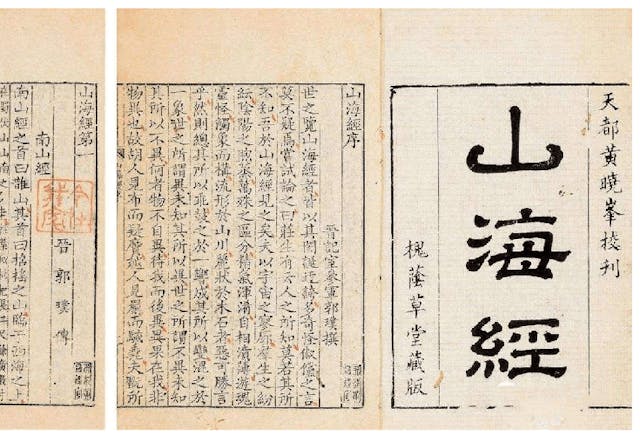近年英國成為港人的移民熱點,看着相關新聞,我不禁想起了倫敦的海德公園,特別是那兒的參天大樹。
海德公園 (Hyde Park)位於倫敦市中心,面積並不太大,但因毗鄰肯辛頓花園(Kensington Garden),兩者互通款曲,融合為一,那就有2.5平方公里,等於13個維多利亞公園。網上資料說海德公園毗鄰白金漢宮,那還要看從哪個位置出發。
有位旅遊達人曾說他的台灣朋友在海德公園逛了4個多小時,好奇問道,「你們這麼喜歡公園嗎?」對方無奈地說,「不是啦,我們是找不到出口才在公園裏兜圈圈。」
這就是海德公園。
海德公園的樹
海德公園是典型的英式自然園林,處處詩情畫意,但其中最令我悠然神往的,就是那裏的大樹。我們每次都在湖邊附近的大樹下,鋪上天藍色的墊子,過上一個慵懶的下午。
倫敦之夏甚是醉人,天朗氣清,綠草如茵,翠綠柔軟的小草好像一大片綠毯,散發出陣陣的青草香味;仰望樹冠,葉影婆娑,枝條伸展,枝椏隨風擺動,發出「沙沙」的摩擦聲,仿如來自天籟的音樂。
大樹下,既是童話中精靈的住所,也是現實中孩子的天堂。她一會兒收集樹枝,一會兒搭起小帳篷,或追尋松鼠,或爬上樹頭,也可和友伴捉捉迷藏。她最喜歡在湖邊餵水鳥,我索性給她一張小凳子,讓她好好享受百鳥朝拜、有鳳來儀的滋味。
孩子有自己的世界,我也有了自己的空間。海德公園的樹真是壯觀,天寬地闊,伸展枝幹,幾百年屹立不搖,日日回饋新鮮空氣,也年年慣看冬去春來。
公園裏的常見樹木共有4種,包括英國梧桐、橡木、山毛櫸和歐洲七葉樹,以英國梧桐數量最多。這種樹高達40多米,葉大呈亮綠色,樹皮時而脫落,露出光滑軀幹。坐在樹下仰望大樹,真是氣勢磅礴,莊嚴肅穆,卻又有親近安詳之感,令我等浮動之心,得以平靜。
對於樹,我很有感情。十多年前的機緣,我突然發現樹木是有感情,是可以溝通的,它擁有巨大的襟懷,能夠包容很多的複雜和世情。一旦靜下心來,獨自面對一棵年代久遠的大樹,就像是面對一位閲盡滄桑,慈祥和藹,但保持靜默的老人。他看過的比你多,知道的也比你多,經歷得更多。你不用説什麽,他都明白你的心緒和境遇。
「他」是可以溝通的,也可以依靠的。
西方樹木之神聖
法國現代史學家阿蘭·科爾班(Alain Corbin)在《樹蔭的溫柔》這本書中,不斷探求一個問題──「對人來説,樹木到底意味着什麽?」他發現在17世紀的理性時代之前,樹木的意涵相當廣闊,具有神聖感。
在許多傳統文化中,樹是生命的起源。宇宙中心往往有一顆巨大的神樹,神靈守護着代表永生的力量──通常就是它的果子。樹根紮根大地,不斷生長,具有永不止竭的生命力,例如北歐神話中的神奇大樹──Yggdrasil。
故此,在17世紀前(啟蒙運動前),樹的涵義相當豐富。它是生命棲居的世界,是個小宇宙;對教徒而言,樹允諾了生命和拯救;墓地旁植樹,可以令現實世界的人們,與地下的亡者進行溝通;在未有廟宇之前,人類就把森林當作廟宇,進行祭神(英文Temple一字原意就是樹木);森林在許多文化中都是神聖場所,和神殿、寺院一起被視為國家權力也不能介入的聖地領域。
《樹蔭的溫柔》主要聚焦於法國的樹木,但在歐洲,也有不同的樹木/森林文化,譬如德國和東歐那毫無人煙的浩瀚森林,代表着一種深沉、內省而又令人戰慄的力量,或者是各種妖魔鬼怪的棲身之所。故此,在發源於德語區的精神分析學派中,森林常被視為無意識的象徵,是心理深層的黑暗和未知。
樹木具有善惡二元性由來已久,源自《創世紀》之開篇,「在天堂的中央,豎立着天堂之樹,就是亞當和夏娃食用它的果實,才開啓繁衍人類旅程的那顆樹」。這棵樹具有神性,果實卻是禁果,説明了樹的神性中帶着恐怖、墮落和誘惑的氣息。而在《神曲》第3篇《地獄》中,描繪了枝丫歪斜,扭曲多結,不結果實,卻長滿有毒和刺的「哀號樹」。這都是《聖經》所賦予樹的二元本性。
中國樹木之詩意
《樹蔭的溫柔》並未放眼東方,但如果將「樹木對於人到底意味着什麽?」這個問題放在東方中國,答案就很不一樣。最不同的是,中國文化很早就淡化了樹的神聖,從而走向詩意的存在。
在遠古時代,我們也有將樹木視爲神或具有神力的記載。在中國神話裏,象徵整個世界,位於宇宙中心的神聖大樹,就是《山海經》裏的「建木」。它是具有天梯性質,可以貫通人間和上蒼的宇宙樹;我們的先人也曾把樹木視爲大地生命力的象徵,例如「昔盤古氏之死也,頭為四岳,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髮為草木」,成語「不毛之地」即來源於此;我們對家族繁衍和血緣意識的隱喻,如「世」、「本」等字均取自樹木。
這說明了中西早期文化,都具有神性化的共同特徵,後來才分道揚鑣,各自演變,各自精彩。
我們不妨舉桑樹作爲例子,相當有趣。扶桑(桑樹)是上古神話中的神樹,桑林是祭典所在的聖地,蘊含着生殖的重要涵義。故此,桑林成了祈求繁衍的神聖之所。到了《詩經》時代,桑林之神性逐漸淡薄,神聖之地的初衷被懸置一邊,而演變成男女之間情愛的象徵,甚至是歡好野合之地。民間即使仍有樹木崇拜,但與西方的一神教有本質上之不同。
西方「你我不同」,中國「你我相融」
中西文化分道揚鑣之後,西方的樹木依然神聖,中國的樹木則褪去了神性。那麽,兩者有何具體不同呢?簡單說,西方是「你我不同」,中國是「你我相融」。
西方文化中既然有神,那就有人,兩者界限清晰,壁壘分明,如此也直接影響了西方文化的觀物特徵,將外在事物當作一個待觀察、測量、描畫的客體。這種主客二元的觀察法,放在樹木上,就是表明樹是一個客體,不需要依賴人這個主體而存在。就好像人之不在,甚至世界寂滅,但神依然存在。
《樹蔭的溫柔》的扉頁,引用了法國著名詩人伊夫·伯納富瓦(Yves Bonnefoy)的話,相當傳神,很能夠說明這一點,這位法國大詩人説道,「無我樹亦存在。這種生命形式,毫不主觀、毫無投射地講,就是純粹的我。在樹面前,我的幸運就是直接與陌生者,與非我接觸」。

說得真好,可以歸納為──「我在或不在,樹也必然存在」。這就和中國文化相當不同。
中國文化中的觀念是 「無我則樹不存在」,外物被視為人心之體現,被賦予人文意義,故此並不存在一棵純粹獨立的「樹」。只有在人心衍生移情作用,樹才會「存在」和「出現」。《詩經》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詩人將樹視為與自我無甚差別的同類,人與樹彼此感知,互相呼應。朱光潛先生將移情現象稱之爲「宇宙的人情化」,是很有道理的。
這種比擬在中國文化長河中俯拾皆是,最典型就是杜甫的「感時花濺淚,恨時鳥驚心」;王陽明也如此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人的感情投射到大自然的物事中,物我相融,產生呼應,予以寄情和抒發。在此心緒下,將植物擬人化,諸如松柏象徵堅貞,勇敢,長壽;竹子象徵氣節;梅花象徵正氣和堅強等等。
「你我不同」和「你我相融」亦呈現於中西方之盆景觀。西方式的盆景設計,就是將植物剪裁妥當,放置盆中,予以欣賞,其中別無他物;而中國式的盆景布局,往往在植物旁放置亭台樓閣和小橋流水,再放入漁樵耕讀之小人偶。如此布局,令自己也仿似置身其中,漫遊其中,亦寄托着自己的志趣。可以說,西方是側重冷靜和客觀的,而中國偏向是動情和主觀的。
這就是中國人獨特的思想與創造力。故此,中國文化中的樹,是一種你我相融,具有詩性的樹。
西方的神聖之樹,在17世紀後的演變如何?中國的詩性之樹,在近代又經歷了如何滄桑和變遷?下文將會繼續探討。
中西樹木之別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