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一直在生態理論方面甚為活躍的法國思想界顯示出更為強勁的勢頭,各種思考論述不斷湧現。在老一代學人如人類學家、法蘭西學院院士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哲學家、科學社會學的領軍人物拉圖爾(Bruno Latour)等人的帶領與推動下,一批新的生態思想者破繭而出。其中有來自哲學領域的如艾克斯大學講師莫裏佐(Baptiste Morizot),以研究氣候與社會間關聯受到普遍關注的年輕學者夏爾波尼(Pierre Charbonnier)等,但更多的是來自人類學界如師承德斯科拉研究白令海峽兩岸族群的馬丁(Nastassja Martin),以香港、台灣及新加坡為田野調查對象研究疫情傳播而知名的科克(Frédéric Keck)等。從一定意義上,新冠病毒的流行為這些思想者提供了在世界範圍內審視人與自然關係的難得機會,使他們獲得了身臨其境的體驗。在他們看來,地球上各種全新的病毒的出現正是人與另類生物關係失衡的有力例證。鑒於他們觀點的前瞻性,法國《世界報》將這一群學術新近譽為「新世界」的思想者。
早在2020年5月,德斯科拉教授在對《世界報》的一次採訪中就針對新冠病毒的肆虐表示:「我們已經成為地球的病毒」。不過,這個「我們」所指的並非整個人類,而是現代人類創造出來的資本主義制度。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病毒也像流行病一樣傳播,但不同的是,這一社會病毒並不直接致死資本主義的實踐者,而是毀掉地球上所有居民賴以生存的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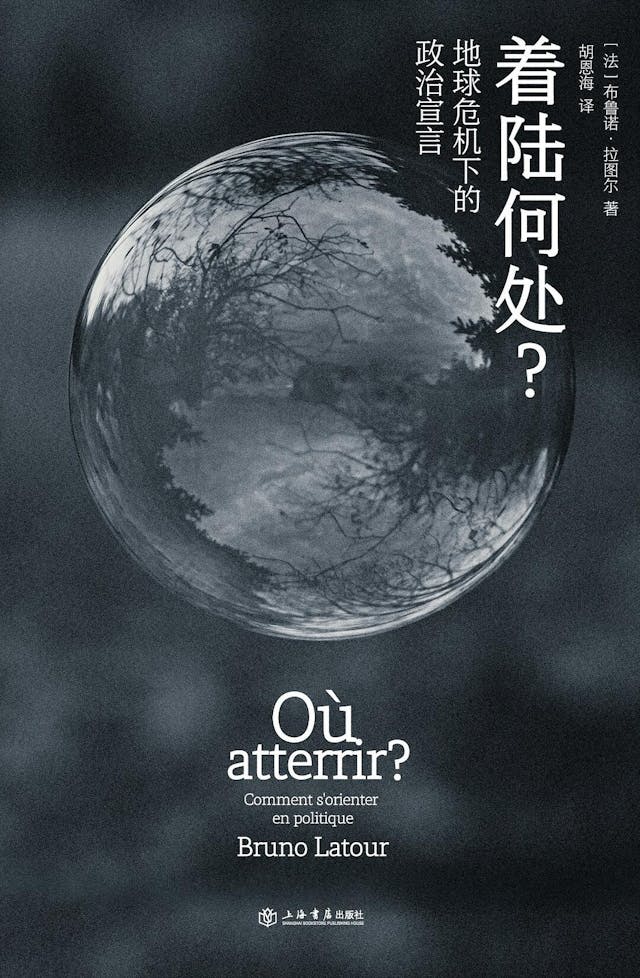
如何從認知層面上走出二元論思維
從生態思想譜系上講,德斯科拉屬於社會生態學一派,在總體上承認人類是今天生態惡化的禍首的前提下,將批判的重點放在資本主義制度上,提倡對資本主義進行變革,以達到緩解生態危機的目的。科學哲學家拉圖爾相對說來則屬於另一思路。拉圖爾研究的重點是自然與人類而非自然與社會或自然與政治的關係。因此他的批判重點並非某種社會制度,而是人類整體。在2021年1月出版的《我在哪裏?》的新著中,拉圖爾首次提出了「攫取者」(extracteurs)和「修復者」(ravaudeurs)兩個概念。在他看來,地球危機之下,傳統的基於生產而劃分階級的模式已不再適用於今天的世界,而應代之於基於地球的劃分方法。他因此提出「攫取者 」和「修復者」的概念,前者攫取地球資源,後者則試圖修復之。此書是拉圖爾繼2017年《何處着陸?》一書之後,經過新冠疫情衝擊之後的又一力作。以攫取與修復的對立來定位今天世界的基本衝突,具有重要的理論前瞻意義。
法國生態思想界可以劃分出制度批判如德斯科拉和人類批判如拉圖爾兩種不同的思路,但在對待今天地球危機的思想源頭上,大多將生態危機的根源追溯至西方根深蒂固的對人與物、文化與自然、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因此如何從認知層面上走出二元論思維就成為大家共同關注的論題。
德斯科拉以連續(continuité)與間斷(discontinuité)兩個概念來取代傳統的二元論,他認為自然其實也是人類社會的產物。他在《超越自然與文化》一書中提出四種觀察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連續和間斷的本體論方法:圖騰主義、萬物有靈論、自然主義、類比主義而奠定了他的學術地位。拉圖爾則提出人類與非人類的概念取代人與自然的二元論。在《何處着陸?》一書中,拉圖爾將人類與非人類統稱為「地球生物」(terrestre),強調人與地球其他生命體之間的聯繫和互相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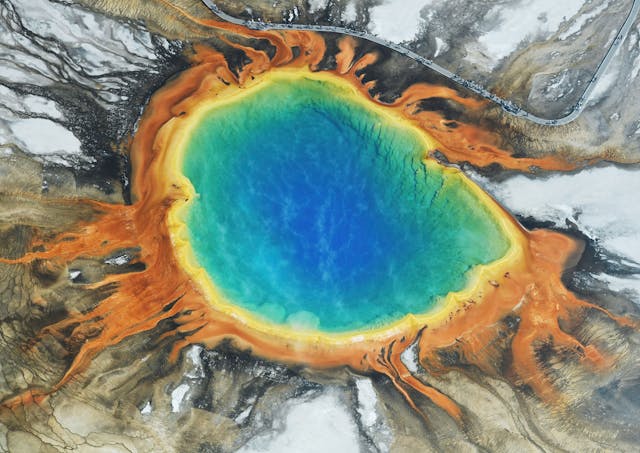
新生代思想者提出生命體概念
從這一思路出發,法國生態思想界的後起之秀們在強調人與其他生物之間的聯繫和互賴上呈現出趨同的態勢。而生命體(le vivant)正在成為一個獲得共識的概念。
何謂生命體?生命體包括人類、動物、植物及一切生物。凡皆具有呼吸、成長與繁衍能力的物體都屬於生命體。從這個意義上講,生命體實質上是一個地球生命共同體的概念,因為任何生命體都不能離開其生存環境和孤立存在。生命不僅依賴地球上所有生命體組成的網路而生存,同時也反作用於這個生命之網。換句話說,每一個生命體都為生命共同體的演化貢獻自己的力量。因之,生命共同體也是一個不斷演化和相互作用共同演化的進程。埃克斯大學莫裏佐是目前在生命體概念上着墨較多的思想家。他於2020一年內出版了兩部關於生命體的着作,對生命體的內涵和意義給予了詳細的詮釋。他認為,生態危機實質上是我們與地球上所有生物之間關係的危機。生命體強調所有生物之間相互依存的意義是使人類能夠更好地維護自身與整個生態系統的共同福祉,而不是把人類的利益強加於自然之上。
綜上所述,反觀上述由德斯科拉代表的制度批判論和由拉圖爾代表的人類整體批判論兩種思路,實際上異曲同工,相輔相成。拉圖爾的思路是「人類世」的思路,即人類在近二百年來通過前所未有的工業生產活動,改變了人類長期與地球家園共存共生的關係,使人類成為地球的駕馭者和毀害者,拉圖爾稱為「攫取者」。如果不從整體上反思,人類不可能應對地球生態的系統危機。同時,我們也很難設想,應對地球生態危機,可以罔顧政治參與與社會平等。生態變革必然伴隨着政治變革,沒有政治變革生態變革不可能成功,甚至根本不可能有效展開。受一個民間生態組織的行動的啟發,莫里佐最近撰文提出將鬥爭文化與生命共同體文化匯合起來,否則難以推動生態變革,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想法。不過,這裏的鬥爭文化卻不能與我們常用的鬥爭哲學同日而語。他說的鬥爭文化是為了推動生態變革起而反對來自各方阻擋變革的力量,包括來自資本和政府的阻力。從中文語境看,那種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鬥爭哲學則是生態變革必須拋棄的。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