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挪威作家喬恩·弗斯(Jon Olav Fosse)小說Det er Ales翻譯成英文的Aliss At The Fire,說不得不把Ales譯成Aliss:「Ales是一隻啤酒名。作為小說名,很容易會引起讀者誤會。譯改成Alice也不好,因為已有Alice in Wonderland這部小說了。」
不過,弗斯其後所寫的小說,都愛用Ales來稱呼他創作出的女性。他的曾曾祖母就叫Ales。「她還懂醫術(差點被視為巫術?),為村民治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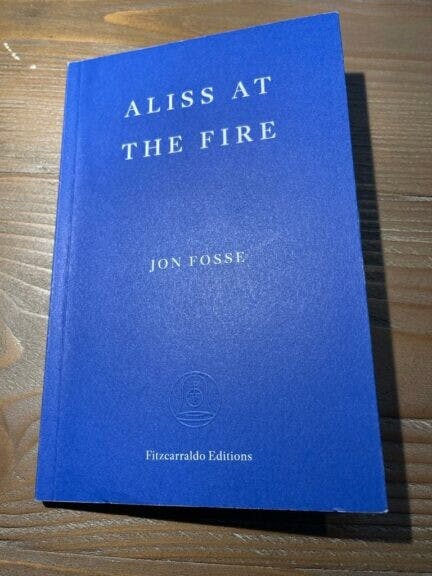
文字的力量
用同一個名Ales,在不同小說出現,會為讀者帶來更多想像,原來Ales在作者筆下,可以有不同面貌的。
弗斯的Aliss At The Fire像實驗小說,亦像首萬言詩。作者說了一個簡單的故事:太太在等丈夫回來,一等就是二十年。站在窗口望出去,漆黑一片,什麼都看不見。但站在窗口的人,已換了幾代人,他/她們都在等一個沒有結果的「悲劇」,有已經發生了(上一代有人溺斃),有仍未發生的。
有書評人說202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弗斯與愛爾蘭作家的Samuel Beckett極為相似,探討人的命運筆觸相近。Beckett的《等待果陀》,說的可就是一個「沒有結果的等待」故事。這與弗斯筆下的女主角等待奇蹟出現,一去不返的丈夫,或許仍會回來。
用讀者都看得懂的文字,一次又一次描述同一場景,很有舞台劇效果(作者是出色舞台劇劇作家)。看下去,舞台效果有了,但震撼力欠奉。作者把同一句話說了又說,是讓我們知道,語言一如文字,會有蒼白無力一天。
「他站在窗前,她看見他站在那裏,與黑暗沒法分得開。她看見他黑色的頭髮……」
每個字我們都看得清楚明白,我們不明白的,是女主角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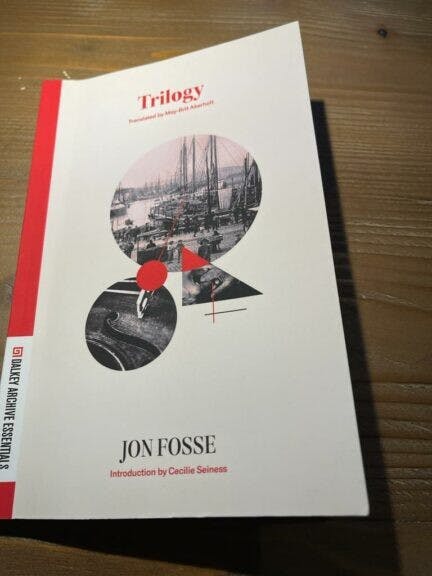
延續篇
弗斯的,說是人生三部曲,卻不是在同一時期完成的作品。第一部說的是夫妻兩人的故事,那時候他/她還年輕,面對的人生困境、難題,「the short time in which we are an eye in the storm」、「ups and downs in life」,就像潮水的漲退,那是人生的節奏,有高潮也有低潮。
弗斯說:「writing should be as simple and incomprehensible as life itself」,生命一如寫作,該是簡單,卻不易理解。
在弗斯第一部作品中出現的男女主角,來到小說結尾,有了定案,故事可以就在那裏結束(很多小說不也是來到最後一章、最後一句,打上完滿句號,到此為止)。
隔了那些年,作者忍不住在想:他/她們的往後日子過得怎樣了?只要他拿起筆來,就可以把他/她「復活」,繼續寫下去。
弗斯喜歡詩意寫作(Poetic Writing):「那不是記者的紀實寫法,也不是哲學家的想法,有點像演戲,那不是音樂,但接近那境界。」
Trilogy不是一部長篇小說,把三個中篇放在一起,人物看似是相同的,卻又可以分開來看。第二部曲的男女主角姓名一樣,但他們的處身為人,與第一部曲已有所不同。只看第二、三部,那是男女主角另一時期的生活,與第一部已沒有什麼關係的了。
有一次在敍舊活動,見到多年不見的中學同學,我們的共同話題:數說從前種種趣事(那是我們回憶中的好時光),我們成長的第一部曲。
來到第二、第三部曲,大家沒有見面,沒法分享那段人生體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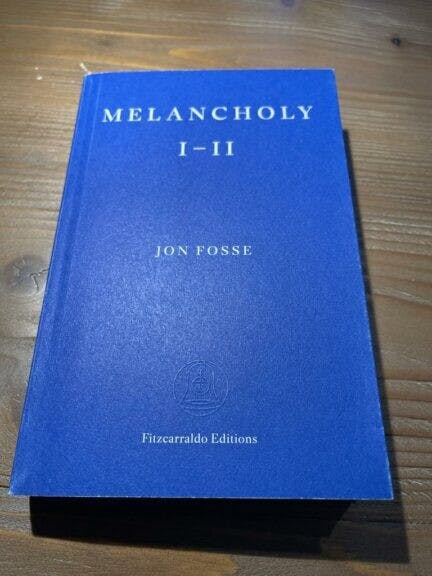
推門
離家出走這樣的故事,不一定只發生在虛構小說,由小說家書寫出來,現實生活也有類似情況出現。
多年前一位定居加拿大多年女性朋友瑪嘉烈,某天給我電話,說他的丈夫西蒙(我也算是認識的)一天早上吃過早餐,說是去上班了,卻沒有返回辦公室,問西蒙有沒有打電話給我。我說沒有,說西蒙是個「有交帶」之人,一定會有電話給她的。
到了晚上,接到西蒙的電話,他說:「這個早上我離開住所後,不想返工,不想再去同一個地方工作了,又不想再返回居所,我想出走,去過另一種生活。」
其後得知瑪嘉烈與西蒙分開了。往後的日子,他們怎樣過,我是一無所知。
就像弗斯的小說Aliss At The Fire:「他們之間沒有問題。一切都好,他們關係密切,從不吵架,不會用言語傷害對方。」
「當他推門離去,他去散步而已。他想找到自己的步伐,那感覺是好的。」他的生命好像變得不一樣了。「It’s as though the heaviness that otherwise fills his life gets a little lighter」。弗斯這樣形容男主角的心情。當年西蒙離家出走,心情是否與小說主角一樣呢?
弗斯說:「為什麼一定要找出一個原因呢?」主角離開住了一輩子的大宅(他的曾祖父母、祖父母在此住過,他與父母、兄弟姊妹在同一屋簷下生活過,然後輪到他與妻子留下來)。人要離開,需要解釋麼?
當他回過頭來,看見妻子站在前,看着他。每次他出外散步,到河邊走走,都是一個人去的。只是這一次回過頭來,最後一次看見他的妻子,站在窗前看着他。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綜合轉載,題為編輯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