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政治學學者、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研院院士與世界科學院院士朱雲漢在家中離世,享年67歲。作為朱雲漢教授的好友,鄭永年教授節選其為朱雲漢教授於2021年出版的《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一書撰寫的序言,以悼逝者為學界作出的傑出貢獻。
朱雲漢的3個學術階段
真正的送別沒有長亭古道,就是在和平時一樣的一天,有的人就永遠留在了昨天。昨天( 2月5日 ) 晚間,得知雲漢教授去世的消息,非常震驚。雲漢大我幾歲,學術正當年,怎可能悄然離開?但消息是從雲漢哥哥雲鵬的社交媒體上獲得的,並且我也和雲鵬熟,不得不信。悲痛之餘,一夕千念。我和雲漢相識數十年,又在同一個領域,交流和合作甚多;平常做研究時,即使不在同一個城市,總是感覺就在身邊。現在失去了一位亦師亦友的優秀學者,感覺到人生的失落感。落月屋樑,想寫點文字以寄思念,千頭萬緒竟不知從何說起。思考良久,就把去年為他的大作《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所作的序言拿出來,暫且作為紀念。
雲漢不僅是頂尖學者,更是當代亞洲罕見的思想家。在其學術生涯中,他經過了3個階段,做了3件事情。在其學術早期,他研究和比較西方政治和亞洲政治,推動對亞洲的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之後,他開始批評性地反思西方民主和內部轉型。再之後,在反思西方基礎之上,開始呼籲和踐行建構基於亞洲經驗之上的亞洲社會科學體系。在這3方面,雲漢已經形成不少文字成果。但我猜想,如果他的生命不是如此戛然而止,那麼他還會把這3個方面的思考和知識融匯一體,成為其原創的知識體系。
正如蘇格拉底所說,在死亡的門前,我們要思量的不是生命的空虛,而是它的重要性。雲漢的逝世對學界和思想界是一個巨大的損失,但他對亞洲原創性學術研究的呼籲和踐行將不斷在亞洲大地上蔓延開來。(編按:以下為序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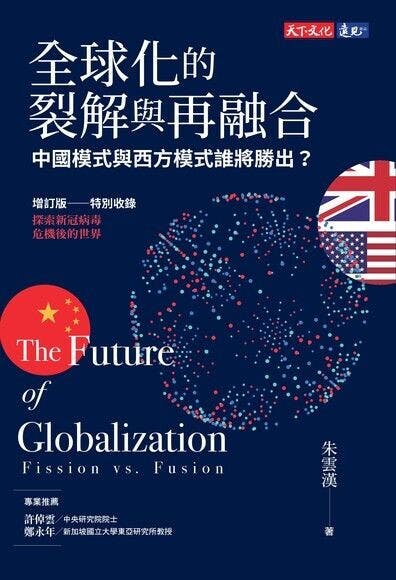
朱雲漢教授來新加坡參加會議時,提到他的新著《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即將出版,我向他祝賀,同時也很期待。這些年來,雲漢教授筆耕不輟,對當今世界所發生的事務有非常深刻的思考,寫了不少有洞見的文字。但每次讀後,總感覺到雲漢教授還沒有說完,因此就有了新的期待。和他交換了一些看法之後,雲漢問我是否可以為他的新書寫一個短序。我欣然答應,但同時告訴他,我答應寫序主要是向他學習。我們都是從美國留學回來的,雲漢長我幾歲,對他的作品,我都是抱着學習的態度,看他的文字的確獲益匪淺,也影響了我自己的研究。所以,我這裏的這些文字與其說是序言,倒不如說是讀書心得。
雲漢的新著不長,文字也不多,但這本書不是一般的學術研究,而是雲漢多年來深刻思考的文字表達,加上深厚的知識背景,讀者需要花很多時間來思考、消化,最終才會有所感悟。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此書涉及的「西方」和「中國」這兩個原本只是地域性的概念,現在已經成為高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物件。近年來,人們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和西方(尤其是美國)所發生的變遷,感性太多,理性過少。讚歎、懷疑、恐懼等情緒充滿輿論空間,但缺失了基於理性思考上的分析。
在這裏,我並不是要讚揚或評判雲漢的觀點,而是藉着學習雲漢的論述,圍繞他所思考的問題,也談一些我的看法,既作為對雲漢作品的悟,也作為對其觀點的延伸。
西方制度面臨困局
在全球化下西方和中國所發生的巨變的確令人深思。記得20世紀90年代初,日裔美籍學者福山發表了其所謂的「歷史終結論」,認為西方自由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也是人類最後一種政治制度。一方面是因為其符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為東歐劇變,這一理論廣為流傳,名噪一時。但是好景不長,西方自由民主體制內部開始發生巨大危機,並深刻影響到作為西方內部秩序外延的「自由國際秩序」。
今天,西方內外部危機互相交織、日益惡化,人們看不到內外危機如何緩和、解決,出路在何方。與此同時,也正是在這段不長的時間裏,中國實現了快速和可持續的崛起,不僅催生了內部新制度的誕生,而且開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在劇烈變化的國際事務中扮演着愈來愈重要的角色。世界歷史不僅沒有為西方的自由民主所終結,相反地,中國的崛起開啟了新的世界歷史。
曾經創造輝煌的西方制度為什麼會在今天面臨這樣的困局?簡單地說,西方制度為根深柢固的既得利益所懷抱,不能與時俱進,適應新的環境,到今天形成了「政治之惡」、「資本之惡」和「社會之惡」三惡並舉的局面。儘管人們對此深感可惜,但也無可奈何。應當指出的是,這裏的惡並不是一種道德上的判斷,而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即各種角色的自私行為。

今天人們所見到的西方制度是近代變革的產物。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看,可以說西方政治制度起於暴力,終於民主。在近代民族國家產生之前,西方所經歷的政治體制要不就是非常地方化的體制,包括部落和歐洲式的小王國(Kingdom),要不就是龐大的帝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歐洲的政治歷史就是由地方化的小王國到帝國、帝國解體再分裂成小王國、再由小王國到帝國的迴圈往複。直到近代,歐洲才形成了統一的民族國家。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對近代民族國家形式的推崇到了迷信的程度,直接宣稱近代民族國家為「歷史的終結」,認為它就是人類最好的國家形式,也是最後的。
但是現實中,民族國家並沒有當時的人們想像得那麼美好。儘管基於近代絕對主權理論之上建立的主權國家推進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但並不能保障國家之間的和平。近代歐洲國家之間戰爭頻發,至一戰和二戰達到了頂峰。二戰結束後,西方諸國內部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的繁榮。在國際層面,在英美主導下,西方也形成了西方人一直為之驕傲的所謂的自由世界秩序。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儘管蘇聯解體有其複雜而深刻的內在因素,但在西方看來,這完全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功勞,是那裏的人民拋棄了自己的制度,而選擇了西方制度。這也就是歷史終結論的背景。
那麼,西方政治制度到底發生了怎樣的危機?這就要看西方政治制度的「初心」及其演變。
一句話,西方政治制度需要解決的是「權力之惡」問題。西方國家起源於暴力,即戰爭和征服。在理論上,從意大利的馬琪雅維利到英國的霍布斯,人們已經為通過暴力(包括戰爭)而建設國家的路徑提供了最有力的合理性論證。霍布斯的《利維坦》假定人類的原始狀態是一個「無政府的戰爭狀態」,而他人就是敵人,人與人一直處於戰爭狀態。為了求生存,就要結束這種不安全狀態。因此,人們「讓渡權力」給主權國家,並且和國家簽署「契約」,讓民眾保存一部分不可讓渡的「權利」。在實踐層面,歐洲近代國家在戰火中誕生,絕對專制是所有近代歐洲國家的最主要特色。只有在近代專制國家形成之後,歐洲才開始了「軟化」和「馴服」權力的過程,也就是後來被稱為「民主化」的過程。洛克的自由主義理論開始「軟化」政治的專制性質,而阿克頓勳爵的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則使歐洲政治制度的設計目標昭然若揭,那就是「權力制衡」。
西方通過一系列的制度設計來達成「權力制衡」的目標,包括憲政、三權(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法治、多黨制、自由媒體和多元主義等。到了美國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那裏,就連經濟力量也是對政治力量的有效制衡,即政治和經濟權力的分離是西方民主的前提條件。必須指出的一點就是,所有這些制度設計都是當時西方諸國社會力量的反映。
且不說所有這些「制衡」是否有效及其制衡的結果,西方政治制度的設計既忽視了「資本之惡」的問題,也忽視了「社會之惡」的問題,不過這種忽視是很容易理解的。西方近代國家的產生本來就和資本不可分離,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國家本來就是「資本的代理人」。在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那裏,「惡」(追求私利)是一種積極的要素,他相信人們的「自私」行為可以自動導致公共品的出現。但其他人從中發現了「資本之惡」的惡果。對「資本之惡」,馬克思進行了充分的理論揭示,法國作家雨果和英國作家狄更斯等做了文學描述。近代以來,各國通過共產主義運動,對「資本之惡」有了一定的制衡。在這個過程中,民主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馬克思描述的原始資本主義階段,西方議會裏都是傳統貴族或新生權貴(商人和資本家),但隨着民主的擴張,愈來愈多的人進入議會和政治過程,西方政府權力的基礎逐漸從資本轉移到選票。

但是,當代全球化已經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面,資本再次坐大。「資本之惡」可以被民主所制衡的條件就是資本具有主權性(在國家政權的範圍內),無論是政治還是社會,可以對資本產生影響。然而,全球化意味着資本可以輕易與主權「脫鈎」。資本沒有國界,也就是說,資本沒有主權。一旦資本與主權「脫鈎」,資本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無論是全球化還是技術進步,無一不演變成獨享經濟,而非往日的分享經濟。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為人類創造了巨額的財富,但財富則流向了極少數人手中,大多數人並不能分享。這是今天西方收入差距加大、社會分化加深的最主要根源,也使得各種社會衝突浮上枱面。
在任何地方,與政治和經濟相比較,社會似乎永遠處於弱勢狀態。無論是在宗教時代,還是在世俗政權下的帝國或地方性政權,社會永遠是「被統治者」。近代民主產生以來,社會力量的地位儘管有所改善,但仍然改變不了其弱勢的局面。儘管「社會之惡」基本上是其弱勢地位的反映,但仍有效制約着西方政治體制的運作。今天的西方,社會一方面追求自己的權利,但同時也在濫用權利。福利制度就是明顯的例子,民主經常演變成福利的「拍賣會」。儘管「一人一票」的民主保障了人們可以得到「一人一份」,但並沒有任何機制來保證「一人貢獻一份」。而如果沒有「一人一份」的貢獻,就很難保障福利社會的可持續性。資本自然被要求多付「幾份」,即政府通過高稅收政策來追求社會公平。顯然,一旦資本可以自由流動,那麼就可以逃避本國的高稅收。實際上,避稅也是西方資本全球化的強大動機之一。進而,隨着社會愈來愈不平等,西方社會各種激進主義、極端主義及其所導致的暴力行為橫行,影響了社會的正常運作。
中國創造性探索 適應時代的新體制
今天的西方,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就是:政治上愈來愈崇尚民主,經濟上則愈來愈不民主;政治上已經充分實現了「一人一票」制度,但經濟上則愈來愈不平等。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有所作為,因為政府代表着社會的整體利益。但現實是殘酷的,西方政府不僅無能為力,反而趨惡,其表現為政治精英之間難以形成共識,黨爭不止,治國理政被荒廢。更為嚴重的是,黨爭往往與形式繁多的民粹主義甚至政治極端主義聯繫在一起,造成了更進一步的社會分化。近代以來的代議民主已經失效,因為一些政治人物已經失去了政治責任感,導致了「有代議、無責任」的局面。民主成為各種社會衝突的根源。政黨政治成為意識形態之間、階級之間、宗教之間、民族之間、公民與移民之間等種種衝突的直接根源,並且對這些衝突推波助瀾。
無論是民主還是福利,其邏輯就是:一旦擁有,再不能失去。儘管危機愈來愈深刻,但人們看不到出路。很顯然,在政治、資本和社會所有群體都成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沒有任何一個群體可以站在既得利益之上的時候,誰來解決問題呢?因此,這個新時代呼籲一種新體制的出現,這種體制既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內部的制衡,又可以形成政治、資本和社會三者之間的制衡,從而實現雙重的均衡及其在此基礎上的穩定發展。而中國經過數十年的創造性探索而造就的一整套新體制,正是適應了這個時代的需要。

1949年之前,毛澤東那一代解決了革命與國家的問題,通過革命建設了一個統一的國家,結束了近代以來內部積貧積弱、外部受人欺辱的局面。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對新中國的基本制度建設做了很多探索。不可否認,新中國的基本國家政治制度都是在毛澤東時代得到確立的。毛澤東時代之後的中國被稱為「改革開放」的時代,顧名思義,「改革」就是改進、改善、改良和修正等,而非革命和推倒重來。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一代解決了經濟發展問題。在短短的40年時間裏,中國書寫了世界經濟史上的最大奇跡,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發展成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即使就人均國民收入來說,也已經接近了高收入經濟體。不過,更大的奇跡在於促成了近8億人口脫離貧困。從歷史角度看,任何社會都有致富的方式,但不是任何社會都能夠找到脫貧方式。在脫貧方面,中國無疑是獨一無二的。
儘管中國的經濟奇跡為人們所稱道,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並不能僅僅以各種經濟指標來衡量。無論是中國歷史上的輝煌,還是近代西方國家崛起的經驗,都表明了一個道理:無論是國家的崛起還是民族的復興,最主要的標誌便是一整套新制度的確立和其所產生的外在影響力,即外部的崛起僅僅是內部制度崛起的一個外延。僅有經濟總量,但沒有制度建設,這樣的崛起是不牢靠的。中國近代歷史充分地說明了這個道理。例如1820年,中國經濟總量雖然佔世界經濟總量的30%以上,但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被英國打敗。
制度是決定性因素。若看不到中國的制度優勢,不僅難以解釋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也難以保障已經取得的成果,更難以實現未來的可持續發展。這些道理很多人都明白,但同時制度建設也是最難的。近代以來,直到今天,很多人一直期待着會從「天」上掉下來一套好制度,一些人更迷信西方制度,以西方為「天」,以為移植了西方制度,國家就可以輕易強大,但恰恰這一點早已被證明是失敗的。二戰後,很多發展中國家簡單地選擇了西方制度,把西方制度機械地移植到自己的國家。儘管從理論上說,憲政、多黨制、自由媒體等什麼都不缺,但在實際運作層面什麼也沒有發生,不僅沒有促成當地社會經濟的變化,反而阻礙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自主的制度建設和改進正是中國數十年以來的要務。如果說黨的十八大之前,一些人對中國自己的體制還缺乏信心,不僅不敢正視自己體制的優勢,反而認為自己的體制是必須被改革的,那麼十八大以來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相互配合、相互強化,造就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一整套制度體系。
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中國已經形成了「混合經濟制度」。具體來說,就是3層「資本構造」,即頂端的國有資本、基層以大量中小型企業為主體的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和大型民間資本互動的中間層。這個經濟制度可以同時在最大程度上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各種經濟要素互相競爭和合作,造就了中國經濟的成功,同時它們之間也存在着互相制衡的局面。因為三層資本結構一旦失衡、經濟就會出現問題,人們就必須在3層資本之間尋找到一個均衡點。而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中國的哲學中,發展和管理經濟永遠是政府最重要的責任之一。政府承擔着提供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應對危機、提供公共服務、平准市場等責任,而民間資本提供得更多的則是創新活力。過去數十年,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歷史的奇跡,又克服了亞洲金融危機(1997年)和全球金融危機(2008年)的影響,與這個經濟體制密不可分。
在政治領域,西方的三權分立體系為黨爭提供了無限的空間,導致了今天政府無能的局面。相反,中國在十八大以來,以制度建設為核心,通過改革融合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基本制度和傳統制度因素,形成了以黨領政之下的三權分工合作體系制度,即決策權、執行權和監察權。傳統上,三權分工合作體系自漢至晚清,存在了2000多年,並沒有受王朝興衰更替的影響。今天,通過創新和轉型,中國重新確立了三權分工合作體系,為建設穩定、高效、清廉的治理制度奠定了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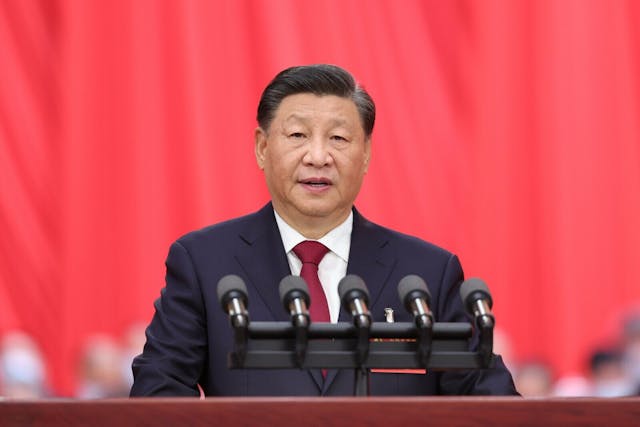
儘管三層資本體系和三權分工合作體系仍然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但它們已經構成了中國最為根本的制度。經驗表明,經濟形式決定社會形式,而社會形式又決定政治形式。三層資本形式塑造著今天中國的社會結構。同時,中國的政治過程又是開放的,不同資本和社會形式都可以進入這一開放的政治過程,參與政治過程,有序地主導和影響著國家的進程。
中國的制度模式不僅促成了中國成功的故事,也為那些既要爭取自身的政治獨立又要爭取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提供另一個制度選擇。中國的經驗表明,制度建設不能放棄自己的文明,但需要開放,對自己的文明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凡是文明的才是可持續的。只有找到了適合自己文明、文化的制度形式,人們才可以建設一套行之有效和可持續的制度體系。虛心學習他國經驗很重要,但學習的目的不是把自己變成他國,而是要把自己變得更好、更像自己。這是普世真理,中國成功了,其他國家也能成功。
這些是我讀朱雲漢這本新書的一點感悟。應當強調的是,能夠把西方、中國、全球化這些當今世界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進行壓縮性討論,很少有學者能夠像雲漢教授那樣勝任。我自己覺得,讀者不必要求自己從雲漢的這本書中得到任何肯定性結論,但這本書肯定會成為讀者思考問題的起點。
原刊於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大灣區評論」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