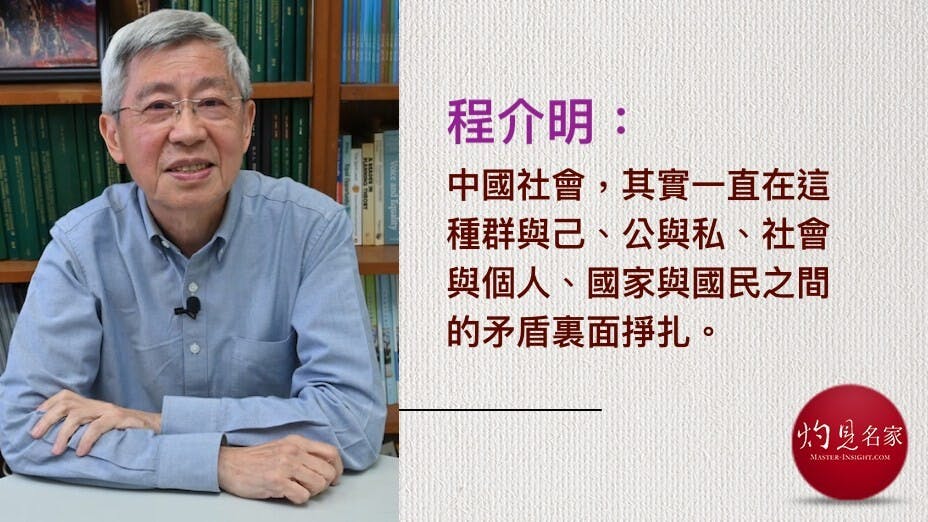上周曾經提到許烺光,有些讀者不認識,但是若說是Francis Hsu,那認識的人就多了。他從人類學的角度,分析各地的文化與心理,與後來比較成熟的文化心理學(Cultural Psychology),息息相關。他的「大我」與「小我」之間的關係,也可以說是對於文化探索一個最核心的課題。
把「大我」與「小我」放大與縮小到極端,變為「社會」(全社會、全個城市、整個國家)與「個人」的關係。為了討論方便,不妨把社會稱為「國家」,把個人稱為「國民」。可以看到有兩種價值觀。一種是,國民先於國家:國民(小我)好,國家(大我)才算好;因此,國家要做的,首先是滿足國民。另一種是,國家先於國民:國家(大我)好了,國民(小我)自然好;因此,首先是要讓國家強起來。當然,誰都知道,國家與國民,即社會與個人,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循環關係。但是具體來說,先有社會,還是先有個人;國家與國民,孰輕孰重,往往是社會制度的核心價值。
一個口罩 窺見文化
眼前的例子,目前的全球疫情,對每一個國家的國民,都是一種考驗。光譜的一端,一些地方,民眾認為戴口罩是危害個人自由,堅決不戴。理由是「我沒有病」,「也不怕人家傳染給我」,也許潛台詞是「傳染了也是我個人的事,別人管不了」。說到底,認為不戴口罩是一種權利,戴口罩是侵犯了個人的權利。
這種觀點,在美國甚囂塵上;在某些州,甚至幾乎成為主流。在他們的文化裏面,個人是獨立的個體,周圍的人群,與自己關係不大。
光譜的另一端,則認為戴口罩是一種義務,「人人戴口罩,才可以遏制病毒的擴散」,「大家都不戴口罩,結果疫情會愈來愈嚴重。」不一定是什麼偉大的犧牲,因為最終疫情若是嚴重,也會危及自己。於是,戴口罩便成了一種不明言的義務:「不戴口罩,沒有公德心」。香港社會大概屬於這一類,即使沒有「口罩令」,街上戴口罩的,幾近100%。即使是抱着「也保護自己」的想法,也是心中想着周圍的人,承認自己是在群體的包圍之下生活的。
需要什麼 想要什麼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歐美,戴口罩變成了一個社會和政策大議題;而東亞這一帶的「筷子社會」,戴口罩卻似乎順理成章。有人認為這裏面也有是否尊重科學的問題;筆者認為,概有之矣;但是一個社會,當個人的權利成為最高的考慮,科學也會變得與己無關;又或者說,大社會發生的事,個人甚少需要去關心;人們也許覺得,戴口罩是有關感染,是社會的事;我個人是否得病,那是另外一回事。其他文化的人,就很難理解。

回到教育,筆者最初進入學術圈子,1980年代初,那時候流行教育規劃,而最熱門的課題,是「人力需求」(manpower requirement)與「社會需要」(social demand)的矛盾。所謂人力需求,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各類各級人力,後來稱為「人力資源」。而所謂社會需要,其實是講社會上個人的期望。當年香港教育當局的負責人李越挺,也是國外公認的教育規劃泰斗,曾經簡潔地歸納為”What is needed?”與”What is wanted?”——社會需要什麼?人們想要什麼?
用自由市場的經濟觀點:社會需要什麼,會轉化為人力市場的需求,轉而表現在人力市場的工資,而工資將會指揮人們就業的取向。於是社會需要的,與人們想要的,兩者之間的矛盾,會通過市場的調節而化解。那時候教育經濟學一個常見的課題,是教育的回報率(rate-of-return)。政府因為教育的社會回報(GDP增長)而樂意投資教育,個人因為教育的私人回報(收入增長)而樂意接受教育。
當然,現實並沒有按照經濟學的如意算盤發生。筆者念碩士時的同學、香港輔導教師協會的元老范浩泉【註1】,他的論文(1983)就發現,年輕人選擇職業,有兩種傾向:一、根據個人興趣,二、根據工資、聲譽、地位(其中也有文化因素,以後再談)。前者就不按經濟回報來就業。
調和社會與個人,「群」與「己」的矛盾,其實中國古代的科舉,已經是一種可以說是非常有效的機制。科舉,是把「社會」的治國、平天下,與「個人」的功名、利祿、榮華、富貴,巧妙地統一起來。本欄一貫認為,科舉其實是選拔官員的機制,並非教育;但是因為科舉着重讀書,也是當時人們讀書的唯一目的,於是後人把它當成是教育。但是卻形成了「群」與「己」的融合平台。「克己」,十年寒窗,歷盡艱辛,懸樑、刺股、借光,期望一朝成名,就會拜為宰相,招為駙馬,衣錦榮歸。社稷的興盛與個人的利益,同時降臨。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這是達到這種公私「雙贏」目的是唯一途徑。其政治意義,遠遠超過讀書(教育)。
社會個人 孰重孰輕
中國的科舉於1905年結束。在民國初期,一直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知識分子基本的思潮,是反「禮教」;把推翻帝制的政治革命,延伸到文化領域。現在回顧,反「禮教」的實質,是希望結束結構性的社會關係,釋放個人,向西方的主流文化價值觀看齊。實質上是想創出一種新的「群己關係」。中國社會,其實一直在這種群與己、公與私、社會與個人、國家與國民之間的矛盾裏面掙扎。

1949年,在人民共和國開國最初的幾年,深受「蘇聯老大哥」的影響,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需要行業、生產單位、各式機構,都按國家的五年計劃從事。在學校而言,就是要服從國家分配,進什麼學校、選什麼專業、將來從事什麼工作,都由國家替你安排。相應的意識形態,就是要樹立個人服從國家的價值觀。
筆者手頭有一本1958年出版的《青少年修養》,裏面很完整地提出對青少年生活各個方面的基本價值觀。其中有一章,專門討論「個人和集體」,裏面提到「……集體主義,才是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關係的唯一正確原理。集體主義原則要求我們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發生矛盾時,應當服從集體利益;必要時,可以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犧牲個人的性命,去維護集體利益。」
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打倒的最高領導人,是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劉少奇。關鍵的「罪狀」,是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39),被批鬥的關鍵,是書中的「公私融化論」,就是主張要把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融合來考慮。這是他嘗試把「社會」與「個人」的矛盾,在概念上統一起來。簡單來說,就是考慮為國家而奮鬥的時候,不等於就是犧牲個人的利益。與上述的集體第一,是唱反調。
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滲入到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大學生的畢業分配也在1996開始完全退出歷史舞台。很容易又變為相反的意識形態,即個人利益置於集體利益之上。但是這種情形似乎沒有出現。
一個例子,可以看到在這方面的掙扎。筆者一位博士生田玲(現居美國),她在念博士的前後,都是北京大學的教師。她的論文(2000),就是研究北大的文化【註2】。四百多頁的論文,總括一句,就是北大人都在個人理想與國家前途之間,同時謀求兩者的最大化(大意)。注意,這裏不是說兩者的平衡,而是兩者的最大化!這可以說是「北大人」出眾的地方,但可以說是群與己掙扎的最高點。
註1: Fan, P.H.C. (1983) The management of careers education programmes : challenges for school administrators in time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HKU MEd dissertation.
註2: Tian, L. (2000)The habitus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its students’ lives. HKU PhD Thesis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