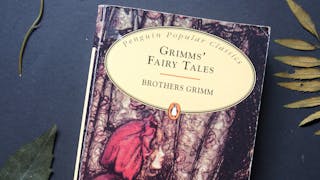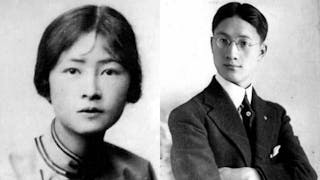編按:《紅樓人物‧性格與命運》一書,原稿12篇,由管喬中(筆名彥山)及其同學黃志鴻二人,於1981年至1982年間在《韓山師專學報》前總編輯吳穎老師指導下執筆完成,分別討論了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王熙鳯等12位小說人物形象,其中多篇曾在《韓山師專學報》、《汕頭大學學報》、《花城》等期刊上發表。本文節錄自書中首篇〈賈寶玉〉,原文保留上世紀80年代文學評論的風貌,小題則為本社編輯所加。
前文提要:賈寶玉在大觀園裏,用中國傳統的人道主義精神作武器,與吃人的封建禮教拚搏,這是一種雖朦朧而卻是真正的人性解放的覺醒。
大觀園裏,有一個少女,她「閒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第三回)她像是沉浸在一種美麗神秘的憂鬱中──「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淚光點點的含情的眼睛。她的神情,顯露出聰明穎慧,才華橫溢,卻又孤高脫俗,傲岸不羈。她就是林黛玉,寶玉精神生活境界中的女王。如果說寶黛愛情的基因是自然的情,而反封建禮教思想是培養這種基因的營養液,那麼,《西廂記》、《牡丹亭》的妙詞豔曲便是促進它生長的催化劑,而大觀園則是溫度適宜的試管。這樣的譬喻,也剛好說明他們的愛情不含雜質,是那樣的純潔。
寶黛邂逅 精神共鳴
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感情關係,總是從他們最早的那一次相識就開始了。寶玉與黛玉初次見面的時候,就發生了神奇的心靈感應。黛玉想:「好生奇怪,倒像在那裏見過一般……」寶玉則說:「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又說:「我看着面善,心裏就算是舊相識。」(第三回)所謂前世姻緣,「木石前盟」,不過是人們無法解釋的解釋。寶黛這種心理反應,其實是對方的形態氣質的投影射入自己的心鏡而引起心膜共振,精神共鳴;也是一種潛在意識的認同感。寶玉對黛玉之愛,並不是建立在「淚債」的宿命上──那不過是一層神話之霧;他們心靈相通,思想一致,互相交心,彼此尊重對方的人格意志。如果說他們為情而生,倒不如說是為愛而死。人性解放的覺醒在現在看來似乎是普通的事,但對於負擔着二三千年沉重歷史的古代人來說,卻不亞於原始人類火的發明。這種覺醒與對封建禮教的反叛,既是寶黛愛情的基石,又是他們愛情的墓誌銘。

泛愛基礎 心靈善美
寶玉首先是泛愛的,他那作為「多所愛者」的出發點,是「天地靈淑之氣只鐘於女子」。他愛的鏡頭是對準美,所以,寶釵、湘雲、寶琴,以至平兒、香菱、五兒都使他一時動過心。他鑒別選擇男性朋友,首先也同樣由美的外表引起,如秦鐘、琪官這些人。但是,他愛的焦點是美的心靈、美的情操、美的思想意識。金釧與晴雯都是丫頭,或枉或屈被逼害致死。寶玉在鳳姐生日全家準備取樂熱鬧那天,自己背着眾人到荒郊井臺,默默無言,潸潸淚下,祭奠金釧兒。茗煙跟隨寶玉多年,雖不知前因後果,卻猜中寶玉的心事,說:「這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極聰明極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第四十三回)寶玉又在大觀園設供寫誄追悼晴雯,誄文中用最美好的詞語來描寫她:「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月不足喻其精;其為貌則花月不足喻其色。姐妹悉慕媖嫻,嫗媼威仰惠德。」(第七十八回)《芙蓉女兒誄》這篇用血淚寫成的美的頌歌,人性的頌歌,歌頌的是晴雯等少女的美的心靈,而對扼殺美的統治者表示憤怒和憎恨。
在寶玉心目中,寶釵也是美的,那「臉若銀盆,眼似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第二十八回)這外表美也常惹寶玉發呆。但是,寶釵美麗的外表包裹着庸俗虛偽的靈魂,她的思維方程嚴格按照封建大家閨秀的公式。她對寶玉說了許多「仕途經濟」的混帳話,寶玉理所當然對這個冷美人冷淡了。寶玉與寶釵之間,兩種不同本質的思想性格的衝突,使「金玉良緣」沒產生真正的愛情,到後來「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從這裏可以看出,寶玉的泛愛還是有明確的着眼點,愛的基礎是真和美,心靈的真和美更是愛的核心。
黃金易得 知心難求
泛愛與專一的愛情貌似矛盾,其實統一。寶玉對愛情從不堅定到十分堅定,他是在泛愛的基礎上產生專一的愛情,而專一的愛情一經產生,他的泛愛就更加純真。第三十六回「識分定情悟梨香院」,寶玉看到齡官情愛的執着和深沉,「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他自己愛的聚光點就愈來愈顯現了。紫鵑謊說黛玉要南歸故里,用情辭試探寶玉,遂使寶玉精神失常,發作狂病。紫鵑見他如此真情實意。對黛玉感歎說,「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寶玉所難得者,也正是「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第五十七回)紫鵑的這個冷眼的評價,是很有份量的。前人曾說:「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而適寶玉為林黛玉心中目中、意中念中、談笑中、哭泣中、幽思夢魂中、生生死死中悱惻纏綿固結莫解之情,此為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這話是說得滿不錯的。
可以說,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在無邊的黑暗中,寶玉的「多所愛」和對黛玉專一的愛情,不但代表人類希望的光明,而且如劃破夜空的彗星,照出黑暗土地的卑污惡濁,照出另一類人心靈的肮髒。賈璉、賈珍、賈蓉、賈赦、薛蟠玩弄女性,「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這都不過是「皮膚淫濫之蠢物」。(第五回)與此相對照,寶玉的「多所愛」及其愛情,顯得高尚、純潔、可貴。馬克思說:「拿婦女當作共同的淫樂犧牲品和婢女來對待,這表現了人在對待自身方面的無限的退化,因為這種關係的秘密在男人對婦女的關係上……毫不含糊地、確鑿無疑地,明顯地、露骨地表現出來了。人和人之間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關係是男女之間的關係。」賈璉之流「拿婦女當作共同淫樂的犧牲品」,在這方面正是成為「人」自身退化的恥辱標記。而寶玉在「男人對待婦女的關係上」,閃耀着人性的光輝。他用真情換來女孩子們的誠意,而他自己的靈魂也獻給聖潔的花神。
金玉良緣 不啻騙局
然而,在黑暗的峽谷,人類希望之花不能結成果實,彗星殞落了,寶玉的叛逆與愛。也只是星星的碎片,迸發出幾個閃灼的光點,散落在幾百年來渴望光明的心田裏。封建統治者又一次取得暫時的勝利,扼殺了愛,扼殺了美,扼殺了純真善良的人性……
所謂「金玉姻緣」,一開始就是一個騙局。「比通靈」時金鶯微露意,寶釵就是這場戲的主要演員。機敏的黛玉早就看出真中之假,他笑寶玉的憨直:「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第十九回)而薛姨媽已明確向王夫人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第二十八回)賈寶玉可以否定這種「天意」,卻難以否認賈元春的「旨意」。賈貴妃在賞端午節的禮物時,寶玉與寶釵一樣多,黛玉與迎、探、惜一樣少。這是「遙控」賈府的統治者的表態,這一細節具有象徵意義,不管寶玉多麼愛黛玉,但黛玉在賈母、王夫人眼裏已褪了顏色。黛玉「人品才情為《紅樓夢》最」(塗瀛語),卻不符合封建禮教的閨範。如果說賈母看到寶玉熱戀黛玉以致一時失去常態,她用咒「林家的人都死絕了」來安慰寶玉,表明對黛玉的厭棄和不耐煩,那麼王夫人說晴雯的「眉眼兒有些像林妹妹」,又罵晴雯「妖精似的東西」,則是指桑駡槐式的公開對黛玉攻擊和非議。在賈母、王夫人看來,聯姻不但是政治行為,是經濟的連結,而且是禮教的光大發揚,是神靈與統治者的意志的集中表現。

高鶚續書 不落俗套
有愛的不能愛,不愛的硬要他們在一起。人們稱道高鶚續書的成就在於寫完成寶黛的最後悲劇。其實,那種讓寶玉發瘋黛玉變傻的戲劇化手法,簡化了人物性格的矛盾衝突,用情節的離奇來沖淡人物形象的豐滿而快速過場,無疑是與曹雪芹原意有很大出入的。但是,高鶚總算沒處理成那些庸俗不堪的大團圓結局。在「林黛玉焚稿斷癡情」、「魂歸離恨天」時,那邊鼓樂齊鳴,「薛寶釵出閨成大禮」。賈寶玉沒法實踐自己的意志,而鳳姐的「掉包兒」計大功告成,在陰謀與愛情中,陰謀勝利了,愛情死亡了,林黛玉死去了。但是,死去的愛情多少仍活在寶玉心中。這些,證明高鶚的續書,比起那一大堆「佛頭着糞」式的續書,還是有明顯的不同的。
連串悲劇 最終決裂
寶玉對封建家族的疏離感,並不是如同那塊玉一樣從娘胎帶來的。他看見了許多死亡,許多真善美的破滅。雖然愛比恨更有力量,但恨也因愛的喪失而滋生。從金釧的悲劇到尤氏姐妹的悲劇,引起寶玉感情上的震盪和思想上進一層的思考。「寶玉因冷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連連接接,閒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癡,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疾。」(第七十回)這時,寶玉雖有不滿,但還沒有形成對封建制度和家族的怨恨。到了繡春囊事件發生,大觀園抄檢,司棋被逐,晴雯以「莫須有」罪名被攆,悲憤交集熬煎而亡,王夫人已讓自己的殘忍扯破那「慈善人」的面紗。這一切,才使寶玉大為震驚,開始對封建家族產生怨憤和憎恨;同時他也警惕起來,覺悟到花襲人原來是個配合王善保家的構陷晴雯的「耳報神」。正是一連串的悲劇,一連串急遽的突變,一連串慘痛的教訓,才使寶玉的叛逆思想性格發展到空前高度。因此,爾後的黛玉之死,當然會使寶玉由痛苦,憤懣,絕望,直到徹底斬斷對家族的眷戀,走上決裂的道路,以「崖懸撒手」來抹去他身上的粉漬脂痕。
據脂評所透露的後三十回(?)佚稿的情節,黛玉之死前後,有一場風雨驟至的大變故,寶玉與黛玉的精神面貌,本來應該在這驚心動魄的一幕中,表現出雷雨閃電照亮的奪目光彩。遺憾的是,原稿後三十回散失了,續作者雖然也寫了榮國府發生急遽的變化,賈貴妃夭逝,史家衰敗,王子騰暴卒,又發生了把賈府拋入絕境的「查抄」。但是,續作者過分強調這個大變故的「外因」,不大符合全書情節的發展規律,還改變了原作者初衷,導演了「沐皇恩賈家延世澤」的喜劇,使變故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逢凶化吉,「蘭桂齊芳」。雖然,續書中寶玉似乎還是在叛逆的道路上前進,但留下的兩行腳印卻是忽進忽退,一深一淺;而且,他的腳印並不是生活的合乎規律的答案,而只是一連串令人「詫異」(魯迅語)的問號。
逃避現實 追求夢境
什麼是人生?從何處來?到何處去?寶玉一直總是想參透這個啞謎,但一直參不透。這是寶玉的苦惱和迷惘,也使整部作品彌漫着一層「無常」的迷霧,通靈寶玉因此也蒙上憂鬱的神秘色彩。寶玉在現實碰壁後,總想逃避現實,尋求精神的解脫。續《南華經》要師莊子,占偈填詞要求解悟,正是希望能猜破人生之謎。在「煩惱」中,他看到「絕聖棄智」之論,便「浮藻聯翩」地想到「焚花散麝……」,聽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曲文,就以為大徹大悟,找到了出路。(第二十一至二十二回)但是,寶玉畢竟不是「無牽掛」的人,他本來的情性就是「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愁」。所以,即使想到死,他也還希望死後飄浮在女孩子們眼淚流成的大河,「送到了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鴉雀可以不到,但他所愛的人的靈魂卻是要到的,他與黛玉要活在一起,死在一起,永遠在一起。這就是寶玉想像自己的美妙天地和夢境。他確定自己的美夢,因此,他逃避現實其實也是為了追求想像中的美好的「現實」。
在背叛封建道統的路上,「歸返自然」和「全性保真」的帶有道家佛家色彩的思想,成了寶玉一種推進器;也成了他否定封建道統秩序,謀取個性解放的精神武器。寶玉不同於惜春,也不同於妙玉,他的宗教觀點倒是與近代藝術大師羅丹有點相似。在羅丹看來,「宗教是對世界上一切未曾解釋的,而且毫無疑問不能解釋的事物的感情;是維護宇宙的法則,保存萬物的不可知的力量的崇拜;是對自然中我們的官能不能感覺到的,我們的肉眼甚至靈眼無法得見的廣泛事物的疑惑;又是我們的心靈的飛躍,向着無限、永恆,向着知識與無盡的愛──雖然這也是空幻的諾言使我們的思想躍躍欲動,好像長着翅膀一樣」。然而,寶玉又不是羅丹,道家佛家的某些精神不是一對翅膀,而只是寶玉人生道路上的一對拐杖。這對拐杖又將他引向虛無的實在世界。作為武器,它又如澳洲土人的「飛來器」,發出去,回來又傷了自己。寶玉確是「富貴閒人」,卻又是現實的囚徒;他是精神的闖將,卻又是行動上的「無事忙」者。憂煩與想望是他精神的兩個極端。一方面,他比常人更敏銳感應到封建末世的罪與惡,以及由此造成的生與死的煩擾。正如魯迅說:「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也屢與『無常』見面……。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另一方面,他比常人更渴望真愛至美。寶玉的生活充滿矛盾,因為面對罪惡,他無能為力,只能在憂煩中折磨自己。這也更使他憧憬那美好而不可得到又不知道在哪裏的夢境。於是,作為《紅樓夢》中活着的藝術性格典型,他就只能以見證者的角度,迸出內心的呼喊。
懸崖撒手 出家為僧
寶玉終於「懸崖撒手」──出家當和尚去了,他的結局使人想起《羅丹藝術論》中引用過的詩句,「如同鳥兒飛時彎折了樹枝,他的靈魂摧壞了自己的身軀」!在高鶚續書中,許多人物的性格和命運有相當的歪曲。續書一開始就搞什麼「奉嚴詞兩番入家墊」,後來又讓寶玉「中鄉魁」,使衰敗了的賈府「沐皇恩」、「延世澤」;在封建殭屍上注射廉價樂觀的「復興」激素。最後,又讓當了和尚的寶玉披上大紅猩猩氈斗蓬來拜見父親,以示盡「孝」;把叛逆的出家塗上封建合法的色彩,還讓皇帝賜他為「文妙真人」。這實在有背於曹雪芹原意。不過從「懸崖撒手」這一點說來,寶玉的命運,正如魯迅所說,也「只能是如此」,同樣是「早在冊子裏一一註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
從來處來,又到去處去,不能補封建社會之天的頑石,因為最後未能參透、悟徹,所以只能「歸彼大荒」,回到青埂峰,作為歷史、社會、人生與愛情的見證者,記下了奇傳,記下了他掙扎的痕印。

作者讓寶玉的命運從神話傳說、從非現實主義開始,是為了使我們對產生寶玉思想性格的現實土壤發生興趣;他的逃避現實的歸宿,更使我們以現實主義的態度了解那個扼殺人的思想感情的時代,那個扼殺人的理想的社會。了解過去,是為了更好理解現在和未來。從野獸、神和鬼、朦朧的「人」到現在覺醒的「人」,到將來共產主義的大寫的「人」,這是「人」的歷史發展。馬克思說:「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又說「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的、自覺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賈寶玉這不自覺的第一步,是歷史漫長過程中的一個小環節,但卻是不能省去的環節。這是我們現在評價寶玉形象的歷史內容和思想意義的一根汞柱。
黛玉曾笑說:「寶玉,我問你,至貴者是『寶』,至堅者是『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第二十二回)寶玉不能回答。這是他自己的歷史局限。我們說,所貴者,他是「不肖」地企圖掙脫封建精神禁錮的、具有「人」的初步覺醒的新人,是五四時代魯迅所塑造的「狂人」的先驅;所堅者,是完整地熔鑄着一個初步覺醒的人的命運,啟示着人們永不休止地去追求真善美的理想那樣一個晶瑩透明的不朽的藝術性格典型。
當然,對於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人民來說,寶玉的時代過去了。他那個時代,那個幽深的峽谷沒有太陽;但多少雙期待的眼睛一直在瞭望着那遙遠的地平線,等待着歷史的曙光。而現在,我們已經舉起雙手,正在迎接從東方冉冉升起的「人」的太陽,通向共產主義新紀元的「人」的太陽!
(論賈寶‧下)
本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