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法國100名知識人簽署公開信呼籲反對伊斯蘭分裂主義,並聲稱這一分裂主義實際是一種新的伊斯蘭全能主義。一些法國文化界重量級人物如法蘭西研究院院士芬基爾考特(Alain Finkielkraut),曾任文化部長的哲學家費利(Luc Ferry),人道主義活動家庫士內(Bernard Kouchner)等在公開信上簽了名。公開信提出了當下社會普遍關注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及其思想基礎的大問題,十分引人關注。不過,筆者在此並不準備對此公開信作具體評述,而是希望就此談談法國近年有關知識分子的著述及知識分子的歷史功用及其現代轉型,因為此次公開信作為一個集體簽名行動,使得知識分子重新顯現於公共輿論的前台。
難得的創新思維著作
近兩年來,法國有關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史方面的書籍連連問世,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有大部頭的《法國知識生態史──法國革命後至當今法國》,《法國知識分子的消失》(La fin de l’intellectuel français)等。兩卷本《法國知識生態史》(La vie intellectuelle en France) ,第一卷從法國革命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卷從1914直到今天,總頁碼接近1,600頁,由巴黎一大歷史學教授查理(Christophe Charles)和巴黎八大政治學教授讓皮耶爾(Laurent Jeanpierre)主編,集130位學界專家共同撰寫,僅從撰寫規模和涉及範圍來講,此書已堪稱有關法國知識分子專著之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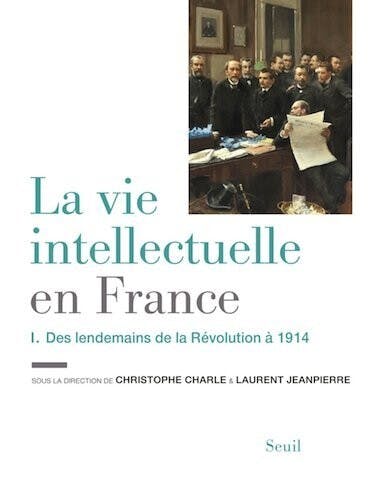
正如該書主編所指出,此書並非一般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史,以大大小小的批判性的思想家,公共輿論的前台人物為主要敘述對象,也非法國思想演變史,以法國思想交鋒、思想與政治互動為敘述主線,儘管此二者確實是法國知識思想史上蔚為壯觀的經典敘述。此書將思想辯論,知識分子對政治、政權、宗教等的批判,圍繞歷史事件(如著名的屈里弗斯事件)的公共討論等歷史植入法國政治、社會、法律、文化土壤之中,不僅試圖突顯出法國思想空間的建構與演變,也試圖勾勒知識人的教育、工作體制環境,知識生產所必須的傳播載體、機制及其傳播工具嬗變的歷史。
同時,僅僅從思想與知識的角度,本書也顯示了其難得的創新思維。科學、文學、藝術、考古、醫學等等均被納入敘述範疇,審視其對公共空間與思想發展的作用。本書編者認為,此書將思想史與社會史聯系起來,填補了法國思想史著述上的一個空白。不過筆者倒是覺得與其說這一嘗試是填補了一項空白,不如說是開創了思想史敘述的一種新方式。而這一新方式正體現了當代大眾媒體、網絡媒體主導社會輿論的時代要求。
知識分子的演變歷程
相對於《法國知識生態史》,《法國知識分子的消失》一書則大異其趣。此書出於以色列著名歷史學者桑德(Shlomo Sand)之手,敘述從屈里弗斯事件至今百年來法國知識分子的演變歷程。此書的副題為《從左拉到維勒貝克》,實際上已經點出作者從知識人物入手建構其歷史敘事,仍然遵循傳統的知識分子史的脈路。比較有意思的是本書書題所示,作者認為法國知識分子已經沒落或者正在沒落。作者對從左拉以來的典型的法國知識分子如薩特、加繆、布迪厄等十分崇敬,但又惋惜如今好景不再,法國知識圈不僅缺少可以與當年先賢比肩的知識分子,甚至充斥着各種右翼保守甚至有種族傾向的作家和文化人,如備受爭議的作家維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保守並被廣泛質疑為種族主義傾向的電視聞人澤穆爾(Éric Zemmour),上文提到的保守思想家芬基爾考特等。
此書再次提出了當今法國知識分子沒落的問題。實際上,此類提問近年來一直不絕於耳。筆者曾經在本欄介紹過英國歷史學者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於2004年出版專著《平淡的思想──法國文化批判》 (La Pensée tiède – Un regard critique sur la culture française),對法國思想界、知識界的總體狀況作出了嚴肅的評判。作者也同樣提出問題:法國號稱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到哪裏去了?一個是英國人,一個是以色列人,二位都是法國思想文化的熱愛者,都對法國干預型的知識分子情有獨鍾,都難以面對法國目前思想界和知識分子的「衰落」現狀,都希望看到法國繼續湧現出一批可以為社會指引方向的思想家和知識分子。然而,在他們看來,現實卻不僅僅不盡如人意,甚至有種每況愈下的感覺。桑德就耿耿於懷地發問:何以現在活躍於法國輿論舞台的都是這種右翼、保守甚至排外的文化人物?

當今法國缺乏思想領袖
知識分子的出現是近代的產物,大致可以上溯至法國革命前的啟蒙時代,隨着近代工業文明的展開,成為普遍的世界現象。一般而言,法國知識分子相對比較典型,影響力也比較大,有一定的代表性,故而觀察法國知識分子的起落具有世界性的意義。東西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退潮,知識分子群體這個意識形態的弄潮兒枝葉飄零,經受重大轉型,時代也相應失去了風向標。這也正是為何眾多的他國學者發問:法國知識分子真的沒落了嗎?從法國國內而言,關於知識分子的詰問不可謂不多,但是,此話題關鍵並非在於提出問題,當今的法國,知識界缺乏眾望所歸的思想領袖乃是不爭的事實,問題是如何解釋這一現象。
早在1977年,法國極權主義研究專家阿蘭·貝桑松(Alain Besançon)在《列寧主義的思想起源》(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u léninisme)一書中就提出一個關於知識階層的悖論:意識形態的在場是知識階層得以降生的決定性條件之一,而意識形態一旦獲得統治地位,也就意味着知識階層的瓦解。將知識分子的興起與沒落同意識形態的興衰聯繫起來,這是十分精到的看法。貝桑松是在論述蘇俄知識分子時提出這一論斷的,如果將這裏的意識形態理解為社會理想的話,從法國啟蒙思想家到現代知識分子都是符合這一特點的。當今歐美社會歷史雖然沒有終結,但意識形態的衰落則無疑義,知識分子失去了藉以定位的歷史路標。
同時,今天的社會難以產生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的重要原因也是社會本身的變化。《法國知識生態史》一書就此給我們提出了不少令人信服的解答。
首先是社會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大學的普及,教師數量的增長,知識分科的細密,社會知識生產成倍增長。
同時,隨着信息工具的衝擊,代際鴻溝加深,一方面信息傳播迅速,一方面社會又面對新的區隔。這種狀況不僅使一呼百應的知識分子很難脫穎而出,更重要的是知識生產的機制發生了變化,知識更新日益加速,知識人賴以生存的傳統社會基礎已不復存在。
另一重要因素顯然是媒體作用的突顯。如果說傳統傳媒更加依賴權威知識分子的話,當代的傳媒對知識人說來,則愈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網絡媒體時代,不僅傳媒人日益有取代知識分子的趨勢,專業傳媒人也受到來自自媒體的嚴峻挑戰。
最後,從社會良心、社會批判的角度看,當代知識群體隱退的一個決定性的原因是社會整體公民意識的加強,公民組織的加強和擴展,分工日細,專業性也大大提高,成為各自專業領域的社會代言人。即是說,公民社會的壯大在很大意義上已經取代了當年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