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 起
在大學時,念的是中文,可是經常流連的地方,卻是藝術系。我修讀過藝術概論、中國美術史、西方美術史……還不時旁聽丁公──丁衍庸老師的課。
香港藝術館的展覽,不分古今中外,我總不會錯過。
因為「虛白齋」,對司徒元傑館長名字,當然不會感到陌生。
一直以來,他策畫的展覽,從展品的選取,到展覽的布局、安排、部署……都給我們帶來驚喜。
2001年《氣宇軒宏──李可染的藝術》,展覽以牛的意象,透顯中國人勤勞苦幹的精神面貌,令人低迴不已。
2007年《國之重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展出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哄動一時。
2011年《墨韻國風──潘天壽藝術回顧展》,亦教人印象難忘。
正式認識館長,已是2012年。那年5月,藝術館舉辦《有情世界──豐子愷的藝術》展覽,而且分為「人間情味」及「護生護心」兩個專題,在文化界引起極大迴響。我還就「護生護心」展覽,寫了一篇觀畫後記。
猶記得2013年2月,他到屯門天主教中學演講,題目就是「德藝雙馨──吳冠中」,他說得精彩而動聽,藝術家背後的故事,令人下淚……
然後,是2014《巴黎.丹青──二十世紀中國畫家展》。巴黎,前衛浪漫之地;丹青,傳統古老的書畫代名詞,二者並列,從作品到展覽的布局,處處可見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
早就想約司徒館長做專訪,可是他真的太忙,直到前一陣子,他才抽出時間,接受訪問,地點就在觀塘香港藝術館的臨時辦公室。
訪談的內容,當然離不開「至樂樓」的書畫藏品、吳冠中的畫作,在短短約一個月內,藝術館先後獲得一古一今的捐贈……
話匣子打開,却從他小學時代說起。
邂逅《芥子園畫譜》
司徒館長自少喜歡藝術,源於小學時代。
就在小學三、四年級,他已開始將人家在大廈後樓梯拋棄的舊雜誌,如《大成》、《大人》拾回家去,雖然不大了解雜誌的內容,但封面的中國畫對他來說,卻極為吸引──「如齊白石的畫,我很喜歡,但當時我根本不認識他是誰……」他往往撕下封面,收藏起來;課餘翻閱《華僑日報》,亦會將文化版介紹畫展的文章剪下來,貼在簿上,製成私人「剪貼冊」。
在學校有美術課,他很喜歡繪畫,老師稱讚他畫得不錯,經常獲得「貼堂」的機會,也曾參加繪畫比賽獲獎。
他猶記得,有一次放學後,在觀塘逛書店,偶然發現書架的高層有一本《芥子園畫譜》,他隨手拿下來翻閱,覺得這本「古書」很有趣。
當時,他只是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學生而已,果真「別有根芽」!
「這年暑假,哥哥做暑期工,賺了點工資,要送份禮物給我。」──他選的正是《芥子園畫譜》,收到禮物後,便開始用打字紙臨摹「畫譜」。傳統畫譜只有線條,他便自行加上水墨,從此,愛上中國畫。
「眼見人家的畫蓋上圖章,自己沒有。當時不懂什麼是印章?也不懂什麼是篆刻?只知『紅色』的東西是父親在手冊上蓋圖章時的『印泥』……」館長很聰明,他學過用「薯仔」刻字,便用「擦字膠」刻上「司徒」兩字,用作自己的印章,又從圖書館借來參考書,得知「印泥由阿麻仁油加艾草加硃砂製成」,於是用「生油」加上「紅粉」*,製成自家「印泥」……
「藝術教育有提及『遺傳與環境』,小孩在成長過程中,一定有不同的天份。男孩子喜歡畫大砲、鐵甲人之類的漫畫,自己畫得好似,想不到後來走上『中國山水畫』之路……」談起往事,他邊笑邊說:「藝術有『直覺』成份,有人視之為『幼稚』,齊白石在畫中展現的童真、直率,便教人着迷不已,無論是畫一隻蝦、一個枇杷果,都很好看。」
回想當時,他不知什麼是宣紙,也不懂什麼叫「水墨淋漓」,將《大成》中的封面仔細觀察,不曉得何以「蝦」的墨色會化開。
直到上中學,他才知道世上有「月宮殿」的存在,偶然有一次上美術課,無意中將畫紙弄濕了,抹乾後落墨,才發現「墨化」的效果。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齊白石的處理方法。
「兒童的好奇心,引發兒童的探索力,這種嘗試的動力,純粹來自興趣,是自發的行為,也是一種生活上的偶得。」念藝術教育的館長,分享了他的看法。
*紅粉:染料店所棄的紅色顏料,他拾回取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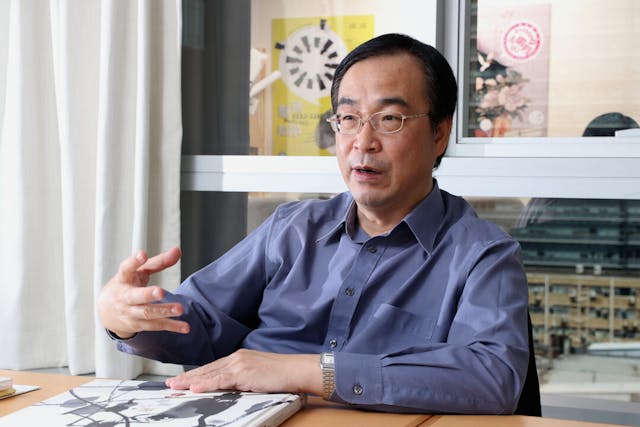
讓孩子發揮創意
司徒館長於英國念「藝術教育」時,曾研究過香港的美術教育,他發現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扼殺孩子的藝術成長──「例如在中秋節,老師派發畫紙後,便吩咐學生畫『中秋節』,完全沒有引導;或是將一份『教材包』派給學生,着學生做一個燈籠,作業完全一模一樣的,一點創意都沒有……」他愈說愈激動。
「這種教法完全無助於引導孩子發揮藝術潛質,最『弊』是用『似』與『不似』去評定學生的作品。學生畫得不似,便好有挫敗感……」而藝術不是以「似」為標準,而且一似便「死」,正如齊白石所說,藝術的最高境界是「似不似」。
他舉出另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國書法如此優秀,為何小孩子會『憎』寫書法?」學校以『默書、騰文、罰抄』三座大山,將優秀的書法藝術轉化成最具懲罰性的行為,帶給學生最不愉快經驗……而且當年的墨盒會『好臭』,寫毛筆字的集體回憶,就是給老師『懲罰』,而且『好臭』,多可怖的聯想!」與館長年齡相若的我,大有同感,未知年輕的讀者,可有共鳴?
「香港的書法教育徹底失敗,藝術教育亦失敗。」館長一邊說,一邊搖頭太息。
西方的藝術教育又如何?在英國念大學時,他曾往學校觀課,觀察學生上課的真實情況,跟香港的完全不一樣,「首先,他們不會以『似』作為評賞標準,教師會引導學生去探討、去發掘,刺激學生創意,不會隨便作出評價,也不是要學生當藝術家。」這種教學方向,對他的影響很大。

從「拆解」到「策展」
「展覽的目的就要將藝術作品介紹出去,讓大眾了解、欣賞……藝術家很偉大,他們透過慧眼,將紛紜世事,加以組織、沉殿、昇華,創作成藝術品。策展人就是要將作品『拆解』,用深入淺出的手法、立體的角度去展現作品的特色……」他回港後當策展人,信念亦植根於此。
「例如豐子愷的作品,可用文學的角度,亦可歷史角度去了解。藝術家的思想、生平經歷,其實都很精彩……」館長策展經驗豐富,順手拈來,例子比比皆是。
「又如吳冠中,他在50年代選擇回國。40年後重返巴黎,與老同學熊秉明見面,熊問他『你有無後悔?』他堅決地說『我不後悔!』對於自己的遭遇,他也沒有控訴。如果他選擇留在巴黎,反而會有失落感,民族感情的失落感……」回顧吳冠中的遭遇,以及他的藝術,再探索何謂「民族感情」,可以重新作出理解。
2010年,因為《獨立風骨──吳冠中捐贈展》,館長到北京訪問吳冠中,再問他「你後悔嗎?」他亦答曰「不後悔!」。不過,重提舊事,令吳老很激動,還為展覽寫了一篇題辭:
獨木橋頭一背影,過橋遠去,不知走向何方。
60年歲月流逝,他又回到了獨木橋,
老了,傷了,走上橋,面向眾生。
「『傷了』是什麼意思,他在講自己的『苦難』……」館長補上一句。

吳冠中另有一篇文章,是在1995年研討會上演講稿,他提到「苦難對藝術家來說,是一種『恩賜』,沒有這些苦難,藝術家就成不了藝術家,如果梵高的命運不坎坷,就沒有梵高……」
事實上,20世紀不少學者、藝術家、文學家都面對這些境況,如季羨林、老舍……還有石魯、李可染、黃永玉、潘天壽──「2010年,我去杭州,路過潘天壽教授紀念館,他的兒子告訴我,門前那條西湖邊上的南山路,當年就幾乎寫滿了批鬥潘教授的大字報。我走在那裏,那種感覺又來了……」
「又如豐一吟大姐,眼見父親豐子愷捱批,她說『不要批他,批我吧!』,甚有木蘭『代父從軍』的氣慨,但木蘭是帶着為國犧牲的精神,而在中國那個時期,中國人鬥中國人,令人多悲難受!」司徒館長曾為多個藝術家策畫展覽,說到這裏,感慨不已。
「做展覽其實不止書畫咁簡單!」溫文爾雅的館長,淡淡道來,卻擲地有聲。
「藝術透顯人性、性靈,與性情有關,是屬於精神性的東西,亦與道德有關。欣賞一張畫,是視覺藝術,看到美好的、愉悅的東西,但對創作背後的理念,以及藝術家創作的過程,多加了解,會產生不一樣的觀感。」作品的背後,其實可以滲出很多觸動心弦的小故事。
話說有一次,為了做李可染的展覽,到北京去看真跡,他還記得與李老的後人聊天的情景,了解到了大師背後「實實在在的東西」,當中也有不少感人的故事。由於當年缺乏紙張,李可染只好在一張紙上,不斷地寫字,乾了再寫,久而久之,於是將這張紙填黑了,於是產生了一張「全黑」的畫紙,不單突顯出其境況之艱苦,亦反映了其不屈不僥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
為何20世紀中國偉大的藝術家的遭遇總是如此坎坷?這實在是時代的悲哀──「捱過了,死不去,便可留下來。」這些藝術家還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在惡劣的環境中還能堅持藝術。
所謂「行為藝術」,是通過一些裝置去作出嘗試,純粹表達一種概念,亦可視之為一種實驗。可是,李可染那張「黑畫」,是發自內心的行為,並不是無病呻吟、刻意經營之作。他做的時候,當然並沒有界定這是「行為藝術」。
館長突然想起了一件「裝置藝術」,安放在「猶太博物館」內──兩大塊玻璃中間,夾着很多猶太人的頭髮,那正是他們被迫進入毒氣室之前,被剪去的頭髮。這件作品的震憾力相當驚人,對人類的悲慘命運,對於大屠殺,提出一種有力的控訴,教人禁不住掉眼淚。
由此可知,現代藝術,可以用歷史角度去看,透過藝術品,可以引發感情,帶出思考──「以前看藝術品,藝術就是藝術,但現時策展,可將這個元素加入展覽中,在視覺藝術以外,多說些精神性的東西。實驗證明,一直以來,做得頗成功,效果亦不錯。事實上,藝術最高的境界就是「感情」方面的東西,引導人家看多些、了解多些,也是好事。」館長如是說。
每次北上探訪回來後,他與助手便會將大師背後的故事整理出來,發給藝術館的導賞員,讓他們在現場與觀眾分享。近年,他還留意到視像媒體的作用,把策展的過程變成影像記憶,送到學校播出。「自己先要將感情投入,效果才會有很大的差異。」
藝術感染力可與歷史、時代掛鈎。如《獨立風骨》展出吳冠中的作品《拋了年華》,所謂「寧折毋屈、不惜年華」,引發了多少人的共鳴、反思?!
據說,吳冠中很喜歡悲劇,「從感情壓抑着,由熱淚盈眶,到迸發出眼淚,是一種感情的洗滌激發。」這就是藝術的力量!

對中國文化要有信心
談到現今社會年輕人的精神面貌,司徒館長指出「愈來愈少學生選擇去唸文學、藝術,年輕人急於求成,只選擇一些刺激感官的東西,而那些要浸淫、要讀書的學問總會被忽視。研究藝術,一定要念書,因為要研究作品背後的文化底蘊,例如文學、歷史,這種求知的精神,似乎已敵不過目前的潮流。」
人們追求快速、易得的東西,幾句看完的短篇,最受歡迎,大部分人不喜歡閱讀長篇大論的東西,這是惡性循環,歷史發展到這裏,好像是到了一個必然階段。雖然如此,但館長引用萬青屴教授曾說過的話:「我們對中國文化要有信心。」輸出正能量。
萬教授曾有一段頗不愉快的經歷,他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當年被打成「壞分子」,進了牛棚,認識了很多大畫家,如李可染、陸儼少等。後來他去美國念書,然後回到香港,在香港大學任教多年。當年籌畫「存念」展覽時,他談到自己在「牛棚」時的經歷,說起一件往事──
「有一次,他去到一個很偏僻的農村,看到幾個孩子在村口『玩』寫詩,他很驚訝,也很感動。你想像不到,詩還是押韻的,像『打油詩』。」
看到這個情境,萬教授領悟到「中國文化優秀之處,是不會失去的,會慢慢滲透,遇上合適的土壤,便會開花結果。我們要接受、面對這個時代,在腐敗中求進步。」
「我們要化消極為積極,腐敗出現了,便要面對,在腐敗中求進步,當然難度高些,所用的時間也要多些。」館長一語中的,他曾到中學演講,從藝術談到德育,引起了不少學生的反響,亦播下種子。
什麼人遇上什麼人
司徒館長一再強調,2019年藝術館重開,一定要做「藝術教育」。他想與香港教育大學合作,研發教案,教具……「世代在變,正因如此,要多做一點功夫,藝術要從教育入手,尤其是『準』教師,一定向他們入手。」
館長想起當年投考助理館長時,遇上的考官──譚志成、曾柱昭和丁新豹三位先生。「我在面試過程中曾說過一句話,令他們覺得很impressive!」
他們的問題是「如何推廣博物館的展覽?」你道館長如何的回應?
「擒賊先擒王」──他主張要向教師「埋手」,讓他們明白,並產生共鳴,如此發揮出來的效果,至少可以影響一班學生,甚至更多人,收效極高。
故此,藝術館出版了很多教育小冊子,例如做《獨立風骨》展覽時,為了推廣藝術教育,他們編製了《小畫簿速寫大世界》,介紹吳冠中的速寫藝術,對象以香港的年輕人、學生為主。編製團隊緊密合作,館長表明「自己很肉緊」,不時找教師提意見,常問「這樣寫,學生明白嗎?用字、用詞如何?」小冊子的設計模式貼近「漫畫」,用“Speech bubbles”展示,連字體亦考究,採用「小朋友」樂見的字體。
吳冠中看到小冊子後感到很滿意,亦感到開心。因成本昂貴,政府資源有限,故印量不多,有見及此,吳老一聲「我給!」,便捐出6萬元,結果加印了2000本。他們自行貼上郵票,寄到學校圖書館去,「雖然做得很辛苦,做完之後,同事很有成功感,也感到很滿足。」館長一邊翻閱這本小書,邊說起往事,笑瞇瞇的,喜形於色。
藝術館做小冊子甚多,「李少染、潘天壽……都有!」
帶着手卷去旅行
吳冠中經常在江南一帶寫生,柯橋、甪直、朱家角、周莊、西塘、南潯……全是蘇浙一帶的水鄉,司徒館長全都去過了。未做吳冠中展覽之前,他對這些地方已深感興趣,覺得這些地方,黑瓦白牆,很有味道,亦富詩意。
以實景對比作品的畫面,是館長最愛做的事情,
例如《姑蘇繁華圖》,是清代宮廷畫家徐揚創作的一幅長卷,比《清明上河圖》還長一倍多。展出之前,從蘇州到木瀆,他沿着乾隆下江南的路程走了一趟,還拍攝了很多照片,「可以感覺一下,為何畫家會如此繪畫,他一定按照皇帝的意思去畫,如何取捨?畫什麼,不畫什麼,都反映了皇帝的心意。」
如此去欣賞一幅作品,他覺得很有意思,當時有一本旅遊雜誌U Magazine訪問了他,標題就喚作《帶着手卷去旅行》。
「其實,我是受日本旅遊書影響,日本人很厲害,他們設計了不少很有意思的旅遊路線,如『梵高之路』。」受到啟發,「我們也可設計『吳冠中之路』,他去過那麼多的地方,我們拿着他的畫作,沿途觀察『似』或『不似』的地方,一定很有趣……」館長愈談愈興奮,彷彿已身處江南,走在水鄉。
藝術的「知者、好者、樂者」──香港藝術館館長司徒元傑專訪(二之一)






































